电影英雄以造梦之心,点亮中国银幕
作者: 何焜 吴纯

黄建新:电影跟我的生命已经分不开了
作为《长津湖》的监制和编剧,黄建新对于自己如何爱上电影的记忆带着年月漫漶后的色彩。17岁时,他在部队当兵。彼时,部队会放一些反对军国主义的国外电影。作为士兵并不被允许观看,于是,他从暖气管道里头爬进去看,电影带来的冲击力是非常直接有力的,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太神奇了”。在人们迷上电影的那一刻,往往会发出这样一声喟叹。
兴趣一夕之间落地生根,急需攀附着更多的阳光和水分继续滋长。与黄建新同期当兵的一个人正好在第五航空学院的校部图书馆工作,黄建新周末放假就去那玩,翻看前苏联学派的电影书籍。自己私下里画蒙太奇草图,组合变换,琢磨其中的意味。上大学后,他的老师同为电影迷,一聊起来,为黄建新对电影的涉猎之深感到惊奇,毕业后就将他介绍到了西安电影制片厂。“我做这些事没有规划,都是偶然”。在文学部的黄建新有一天被一位导演相中,叫去了导演组,从场记,助理导演,再到副导演,最后被厂里推荐到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回来之后,他拍摄了自己的导演处女作《黑炮事件》,正式标记了自己电影生涯的开端。
如今,他以监制、制片人、编剧的身份游走于电影幕后。他口中的自己是个好奇心强的人,“啥都想试一下”,从警匪、传奇到历史,他的创作兼容并包。他说,自己的理想是做个职业人,拍别人的剧本,也拍自己的作品,用作品提升自己生命的延展度,“体会更多的东西,那不就等于活了的时间相对变长了吗”?
Q:本次评选中,哪部作品让你印象深刻?
A:其实入围的都不错,都不一样,风格不同,每个技术部门都很好地完成了艺术想象。所以全世界有两种情况,有一种是电影节认为电影是不可比的,还有一种认为是可比的,可以互相激励。我们现在把它列在可比的范围里,其实是一个更大的交流碰撞,我觉得这个对中国电影的幕后工作者是有激励的,因为很少有这样的评选,我们选的都是横跨着技术跟艺术重叠的一些部门,不光是技术好,还得有艺术感受力,还得有艺术想象,才能完成电影那个虚拟空间所做的一切。
Q:你觉得要拍出一部好电影,“时代”会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吗?
A:一个是大的时代给予的一个前提,因为你都是生活在现在时,每一个生命都在现在时,但是这个生命可以回到过去,也可以穿越现在到未来,这就是想象力,所以想象力是艺术最根本的动力。接下来就是表现力,我们今天其实都在表彰优秀的表现力的代表。所以就是要把这两种情况复合在一起看。而且通过这些电影在技术上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到它对艺术想象力的扩展。
Q:你心目中对于好电影的标准是什么样的?
A:它能够让你的精神有所依托,有良好艺术的表现,让你觉得或美好或高深或独特。
Q:与好莱坞跟其他电影工业体制相比,可否描述一下你觉得中国电影制作处于什么样的阶段?
A:没法比,就像印度宝莱坞跟好莱坞怎么比,每个国家的文化本质不同,它的艺术方法也不同,工业是保证独特的艺术扩大的方法。文化母本不同,看到最后还是要看自己的故事,中国几千年文化基因,都不是后天教的,是先天遗传的,你生出来天然就有的文化,美国会有吗?你也不会有人家的。文化部分决定了你的取舍。
Q:你觉得电影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A:做的时间长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了,它已经不是工作了,跟你的生命分不开,都搅在一起,变成你生命的一部分,它赋予生命一些意义,你拍电影就会兴奋,就会在想象的空间里驰骋,会有多元的理解或者不同角度的感受,让你的思维变得活跃,让你的感触变得灵敏,让你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所以觉得看电影好玩有意思。
Q:基于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你认为一个优秀的监制或者制片人,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A:复合型人才,管理的能力,人格魅力,以及对于艺术深刻的理解,才能做好。

秦海璐:人的多面性,吸引我为电影创作
这几年,从《河山》到《悬崖之上》,秦海璐仍然以她细腻独特的表演活跃于银幕,不断斩获从影视剧到电影的大小奖项。然而,她的触角早已延伸至许多不同的方向。
从2011年的《到阜阳六百里》,甚至更早之前,秦海璐就已经开始尝试编剧工作。人性、幽默、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牵绊,这些都是触动她进行编剧工作的肇因。而在宁浩的牵线下,她也为新人导演曾赠的影片《云水》担任了监制和主演的工作。她喜欢《云水》中对人性的调整与反思。那种平静,在她看来,有很强的内心力量。
而在导演了自己的首部电影《拂乡心》之后,秦海璐对于电影制作的理解也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在她眼中,商业片与文艺片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野,只要是动人的作品,都可以是一部好作品,采取什么样的讲述方式,则取决于导演自身的美学决定。
“电影是造梦工厂,电影里的光影太有魅力。”打从拍摄第一部电影起,秦海璐就对这一艺术形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她也期待着未来的中国电影能够更加多元化,“如果每年我们可以产出四百部、四千部、四万部电影的时候,它真的会有四百、四千和四万个不同的样子”。
Q:你是如何理解电影的幕后工作的?
A:我觉得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对艺术的追求和创作的权威,他们的能力高低代表着在一部电影里他们呈现出来的水平,诸多种类掺杂在一起的时候,大家都在创作,创作之后是通过演员这一载体,通过摄影这一记录方式把它呈现在一起,我觉得他们是相辅相成、互相依赖的。
Q:你认为如今的年轻导演与所谓的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相比,有什么优势和限制?
A:我觉得现在新导演是很困难的,他们的困难在于我们小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信息,没有那么多资源,所以当有一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全国人民都在看,信息量匮乏的时候,选择性也会很少。现在年轻导演所面对的大多数观众是在互联网时代长大的,大家就算不在互联网时代长大,也在互联网影响下生活,所以接触到的信息、作品、对生活的认知都太丰富,观众的要求变得很高,他们生活的条件允许他们有更高的审美,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讲,其实是很难的。那如何打破这种限制?他们的优势是什么?我觉得是他们可以利用我们现在有的这一些信息、资源,比如大家都在讨论一些事情,那我们也可以拍一个不被讨论的,撇开拍冷门的,这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同时,有很多技术手段可以帮助到你,这是第五代、第六代导演可望而不可即的。
Q:拍摄过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拂乡心》之后,你对于电影制作的理解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A:我觉得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你作为一个导演,从开始的剧本酝酿,到编剧,到拍摄时各个部门的要求的释放,再到后期的一些流程上的事情,我们首先是全方位对接的,且不断提出你的要求。作为演员时,我们可以有建议权,但一定是服从导演想要的。所以从前期到后期一些制作的技术流程和标准,整个一套体系走下来之后,我才觉得电影真的是蛮复杂的一个工艺,它可以简单到你想象不到,也可以复杂到你无法想象。
Q:作为导演,你自己最看重电影幕后制作的哪个环节?
A:每一个环节都很重要,如果电影中间缺一个环节,它就注定是一个不完美的样子。不能忽略任何一个部门。不要觉得音乐轻松,也不要觉得拟音可有可无,不要觉得录音随便,嘈杂的背景都可以做。甚至是推摄像机轨道车的那个人都很重要,因为他可以推出你的感情,推出你的焦躁,推出你的恐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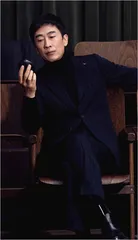
陈同勋:为电影做服装,需要穿越历史和未来
在部队大院成长起来的小孩,往往会储存着这样一幅集体记忆的画面:部队放露天电影,整个营区的小孩提早去划圈占地,等待眼前那块白色幕布上演超越自己想象的异彩纷呈的人生——而这,也是陈同勋关于电影的记忆画卷中一个重要的场景,尽管那时,他对于未来电影会与自己发生的关系还懵然不知,他只是怀揣着好奇,同大家一起,候在那块白色幕布前。
多年后,陈同勋无意间考上了上海戏剧学院的舞台美术系。每周五,学校都会放映一些参考片,正是在大量阅片的过程中,陈同勋了解了电影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毕业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陈同勋都在设计歌剧、话剧等舞台类的东西。直到参与了第一部电影《相伴永远》的制作,有机会去了俄罗斯、法国等地,陈同勋对于电影和世界的认知和想象才一同被打开了。
从《梅兰芳》《太平轮》到《妖猫传》,陈同勋都留下了令人赞叹的服装设计。在他眼中,服装设计没有简化为设计,在新的电影工业体系之下也不再只是一个从属于美术的传统概念,它能帮助演员深化角色,同时,由于服装所具有的强烈独立性而自然而然带来的话题度,都对如今电影推广具有很大的帮助。可宏观,可微观,挥挥手十万八千里,静下来细致到分毫,正是在这样的穿插与交织中,陈同勋用服装为角色赋予了个性和生命,完成了自己的艺术表达。
Q:在今年你看过的电影当中,哪部作品的服装设计让你印象深刻?
A:其实我觉得电影进入一个新工业时代之后,特别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一直在表达很多现实主义的东西,于是所有的设计点、原则、概念、材质,所有这些都来自特别生活的一些细节,这触动我去反思,在思想、制造工艺等很多地方,我们还是有欠缺的。回到今年令我印象深刻的电影,《长津湖》确实是一部具有标杆意义的电影。
Q:你自己是很拥抱技术上的变化的?
A:对,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工作室里琢磨一些新质感的东西,这个质感当中,可能不代表未来,也未必见得过去,但恰恰是在处理一个概念的过程中,我处于一种新鲜和兴奋的状态,其实就是你不愿意受过去方式的束缚,想在设计上追求解放。
Q:看一部电影时,除了服装外,你自己会首先关注的是什么?
A:首先肯定是跟我的专业有关系,最关键的是我可能会从这个点出发,看到更大的一个面,即这部影片的气质。我不太会从一个人物上去看电影,更喜欢从导演、摄影、环境与人物之间的关系上去看。比如我们每次试完妆拍剧照的时候,觉得这件衣服特别好看;可进入拍摄阶段,这件衣服反而变得难看,这就是环境和衣服对撞,它不能够成为一体,比如我们的衣服是偏冷色调的一个红,然后摄影走了一个绿颜色的光,这个红就会变得很脏。所以未来怎么能够让摄影、美术、造型走到一个审美情绪里面,这个是很重要的。
Q:从当下的中国电影市场来说,一个优秀的服装设计师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
A:作为一个造型设计师,他一定是穿越型的。对所有文化都要有尽可能深的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吸收更新的一种时代信息,如果只是处理到这样一个程度,还是个匠人,设计师好的状态是在历史和未来当中,穿越之后,重新提炼出一种新的构成方式,这才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我觉得设计师在电影里面起到的作用会越来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