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树的悼词
作者: 伍泽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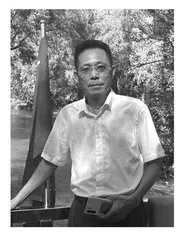
伍泽生,湖南衡阳人,现居广州番禺。著有长篇小说《雄性的土地》《都市外乡人》《地厚天高》等,在《广州文艺》《湖南文学》等刊发表过作品。曾获“浩然文学奖”、“冯梦龙杯”短篇小说奖、“古今传奇杯”中篇小说奖、衡阳市“文学艺术奖”长篇小说奖等奖项。
1
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是先有莲花村,还是先有村东头那棵大槐树。
每个村庄,都有其悠久且尘封的历史,就算出过名人或伟人,也不可能有完整的历史记载。莲花村的历史已无从考证,但从家家户户先祖的灵牌上,和想象发挥中,略可以猜到,在不知朝代的近代甚至远古时期,一个或两三个同姓氏的先人,不知道是为了逃避战火还是为了奔波活命,不得已人海泛舟、搏风打浪,最终流落于此。以此类推,几乎所有古村庄的形成,大抵如此。至于为什么叫莲花村,村里的长辈便会复制祖辈的形态,瞪眼往一脸疑惑的晚辈脑门上一戳:莲花山下莲花村嘛。
莲花山并不是莲花村的标志,山不伟岸,且石层厚,生长不出大的树木,更没有各路大仙驻足过的古迹。按照无树不成村的说法,村东头矗立的那棵大槐树,才是莲花村的唯一标志。大槐树的历史更加无从考证,它就是一棵普普通通的树,或许它根本就没有历史,就算有,那也是一个谜。村里人对大槐树的身世无从知晓也不想知晓,就如同面对寺庙里高高在上的泥菩萨,有关它的一切,只能从村里老年人对它尊崇的行为和一辈辈口口相传中寻找答案。
村里人不叫村东头,而是叫槐树头。
最开始或许只有一间或两三间泥墙茅屋,经过岁月更替和时空翻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次改朝换代,才演变成了一排排五十多间墙靠墙、门对门的砖瓦房。当初不知道从哪里流落到此的一个或许两三个为了活命的人,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不但刨出了活命的食物,还刨出了一辈接一辈的子孙后代。村里的人已经无法追溯到自己的祖宗,年轻一代只知道爷爷的爷爷那一辈大家都是堂兄堂弟,就如同一年年留下的稻谷种子,无法说清楚这稻谷种子的来历一般。在家族不能联姻的规矩下,当初的一个或者两三个靠着土地刨活的技能,用智慧、善良和淳朴传承了人类本能,繁衍发展到了后来的两百多号人,也可以算是一种奇迹了。现在村里七十岁以上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四世同堂了,他们正站在祖辈的坟前,感受着新时代的繁华,享受着先祖们从未享受过的幸福、快乐和美好的现代生活。
一个普通的村庄,一群普通的村民,一片贫沃不均的土地,加上村东头那棵标志性的不知道年轮的葳蕤大槐树,在光秃秃的莲花山下开阔的空地上,经过岁月的洗礼和沉淀,构成了一幅优美的湘南乡村画卷——这就是我魂牵梦萦的村庄,生我养我的故土。
每个人对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都记忆深刻,童年的懵懂和少年的无知就像历经岁月而褪色的黑白照片,年龄越大越喜欢寻找和追念,特别是历经磨难在困苦中长大的人。我是父亲用锄头刨出来的,然后放在苦罐里泡大的,同时也是莲花村这片土地上结出的果实。虽然离开它快四十年了,但我的骨子里依然是农民的儿子,每年都会从五百千米外的大都市乘坐各种交通工具来这里三两次,小憩三两天,目睹它的变化,聆听它的鸟鸣。
2
限于环境的闭塞、交通的阻碍以及知识的匮乏,乡村的孩童时代大多是懵懂无知的,特别是在偏僻贫穷的乡下,一学会走路便开始了放羊放牛,从记事开始存储于内心的自卑,像烙下的印章或被下了诅咒似的无法抹去。在我的记忆中,村东头那棵大槐树,便是我对害怕和畏惧的启蒙,从而让我对所有带有神秘的人和物都感到好奇和敬畏。
大槐树离村约二百米,一条沙石路像一根纽带,一头连着村庄,一头连着大树,那是村民们进出村庄唯一的通道。大树旁边是村集体用石灰铺就的晒谷坪,树下便是村里人濯衣洗足赖以生息的渔塘,一条穿晒谷坪而过的石板小径,是附近几个村的人去到十里以外乡镇集市的必经之路。大槐树就扎根在石板路旁的塘堤高处,塘堤下裸露的大大小小的树根虎爪般扎根于泥土和石缝中,像男人脚上凸起的青筋饱满坚韧且充满活力。大树高约三丈,下面的主干虽不是很大,但也要两个成人合围才能把它抱住,从一丈多高的地方开始分枝,枝又分枝,枝繁叶茂,就像一把撑开的巨伞。远远看去,犹如一位高大威猛的城门卫士,守护着村庄的安宁。
无论是在县志上,还是在县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莲花村的名字。莲花村地处偏僻,信息闭塞,村里人去一回乡里的集市,往往要谋划和准备好些天。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莲花村村民一代代传承的生活全部。
还没进入学堂的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从早到晚我就像她身后摆动着的尾巴,父亲、母亲和哥哥随着生产队一天三次催命似的出工哨声进出于村前那条泥沙小路,根本没有闲暇顾我。每天黎明时分,七十岁的奶奶就像墙角鸡笼里负责打鸣的公鸡一样,她起床的同时就会把我踢起来,在还是一片朦胧的晨色中,她躬着身子拖着那双被裹脚布束缚了几十年的三寸小脚,高一脚低一脚带着我这只摆动的尾巴来到大槐树下。只见她蹲在地上划亮火柴,把三片黄色的纸钱点燃放在地上,暗淡的火光把奶奶的脸照得和大树的树皮一样,苍老、黝黑且粗糙。然后把三支香放在燃烧的纸钱上引燃,站起身,双手捧香躬身对着大槐树,嘴巴一张一合说着只有她自己才能听到的话。
奶奶的世界,对我而言是一片茫然,但那虔诚的模样,却凿子一样刻在我幼小的心里,同时萌生的还有对大槐树的无限畏惧和神秘。
奶奶律定的仪式完成后,我便摆动身子随着奶奶往回走,这时候村口就会出现女人或者老人,各自手里拿着同样的东西去到槐树下做同样的事。此时的奶奶总会重复地告诫我,这大树不是一般的树,是神,神是无所不能的,是不可以冒犯和亵渎的……看到声保伯伯那条一拐一拐的跛腿了吗?就是小时候爬上大槐树去掏鸟窝摔断的,快四十岁了还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嫁给他,这辈子怕是要单身终老了,这就是对神不敬的惩罚……每听一次,我心里对大槐树的神秘和畏惧就增加一分,神奇的大槐树让我的好奇心与日俱增。
村里以持家主妇或者老人为代表,逢年过节、初一十五、生日喜庆、红白喜事的早晚,都会去到大槐树下祭祀、祈祷。我奶奶不一样,每天一早一晚都要去,雷打不动风雨无阻。一天不去,她就好像做了一件对不起神的事,家里有人生病或者出现什么不顺心的事,奶奶就会不停地怪罪于自己没有诚心诚意,到树下时便会低下头一边祈祷一边忏悔。
日复一日,村东头的大槐树在我幼小的心里成了无比畏惧的神,也成了缠绕在我心里难以解开的谜。
3
民国三十四年(公元1945年)腊月的一个早上,天还没吐白,莲花村一个二十八岁的年轻寡妇带着香和纸钱在凛冽的寒风中踩着积雪走向大槐树,她的身后尾巴一样跟着一个四岁的小男孩,那是她四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走近树下时,她朦胧中发现一只箩筐,小心翼翼地走到近前,掏出火柴点燃三片黄色的纸钱仔细察看,一件破棉衣里竟然躺着一个面呈紫色奄奄一息的女孩。年轻寡妇心想,估计是后半夜送来的吧,单薄的小身板怎么能够持久抗寒?如果不是大槐树粗大的树干多少挡住了一些直面吹来的刺骨寒风,不是一树绿黄绿黄的树叶张开怀抱接受凌乱飞舞的雪花,人怕早就没了。积德行善是莲花村人自觉的习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年轻寡妇没有多想,三支香往地下一丢,一手抱着箩筐一手拉着儿子就往家里赶……
在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的年代,没人能猜透一个刚死了丈夫带着四个年幼儿子的年轻寡妇当时的想法,也猜不透一家人本来就吃不饱穿不暖而她为什么又让家里添一张口的做法,但类似辛酸的故事在大槐树下时不时就有发生。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身份,大槐树给附近村庄那些无路可走的人带来了选择和希望,因为那是神的辖区,相信万能的神会在冥冥之中安排心存善念的有缘人,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并拯救他们。
村庄可以追溯一个个家族的历史,而大槐树却无法查到它的年轮,千百年来,从村里一辈辈人的口口相传中得知,凡是被送到大槐树下的小孩没有一个夭折的,其顽强的生命力像路边的野草。也许,这就是大槐树无以言表的神秘和神圣,是被尊为神的法力无边和伟大所在。到底是巧合还是神的庇佑起了作用,始终没人能说清楚,但它实实在在让村里一辈辈人有了可坚持的信仰和寄托的希望。在那暗无天日饿殍遍野的年代,事实上没有什么可以保佑他们,也没什么可以让他们相信,对他们来说,世界上只有两样东西是不可缺的,一是脚下的土地,二是村头的大槐树。
是什么时候大槐树成了神的化身?又是什么让大槐树成了村民心中唯一的信仰?大槐树是否真的附有神的法力?它是否真的能感知到膜拜者的诉求并能提供庇护?对我当时这样一个小学生来说,它是一个难以解开的谜。
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偶然的,当年那个把小女孩抱回家的年轻寡妇就是我奶奶。二十年后,当年那个奄奄一息的小女孩成了我的母亲,那个尾巴一样跟在我奶奶年轻时身后的四岁小男孩就是我的父亲。村里类似于我母亲命运的童养媳有很多,只是大家都不愿提及,那是一块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一旦触碰不是流血便是落泪。
一个女人就是一颗种子,她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只要扔进土里便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承担起一个家族子孙后代的兴旺发达。
4
莲花村的黎明不是被大槐树下村民们燃烧的纸钱烧亮,就是被一阵沉闷的鞭炮声唤醒。
大槐树下,每天都有人去烧纸钱,但鞭炮声不是每天都会响起,当鞭炮声一响,就如同吹响的唢呐,不是悲就是喜,不是生便是死。所有听到的人心里基本有数,谁家添新丁了,谁家老人走了,谁家佳偶天成了,谁家惬意祝寿了,一切明了。无论是来还是走,是喜还是悲,当家的老人或主妇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雷打不动地来到大槐树下虔诚祷告。
三片黄色糙纸打上了月牙状孔印,就像钱币上的专属印章,这是用智慧流传的一种文化象征,也是神世界的通关文牒。地上被焚烧后的纸钱灰烬,被晨风一吹便狂乱翻滚,变成了另一个世界的通用货币,虽然不多,但诚心苍天可鉴;三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纤香气息袅袅,一缕缕飘散在空气中缠绕着大槐树不愿离去,让人感受到宁静和祥和,蕴含着香主的诉求、祈祷或是忏悔,希望唤来神的谅解和庇护;一挂鞭炮惊天动地,肃穆且庄重,空气和树叶都一起颤动,连同三个摆在地上装有祭供的小碗,是向神报到或者与神告别,来者不问出处,去者不问归期,来,是莲花村的人,去,是莲花村的魂。
对刨地讨生活的村民来说,要想避凶趋吉平安和顺,实现心中向往和未来愿景,认为只有神才能做到,只有神才能洞察到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只有神才能听懂、理解并感受他们的期盼、苦痛和祝愿。
莲花村方圆几十里没有寺庙,没有寺庙就没有神,没有神就没有信仰,没有信仰就没有寄托,没有寄托就没有希望,没有希望就如同失去魂魄的人。在莲花村,大槐树是村民心里的神,是无所不能的神。面对大槐树不怒自威却又宽厚包容的模样,看似冷漠却一视同仁、神情自若,从来不为你的悲喜而影响从容淡定,对村民的诉求、祷告和忏悔,总是表现出一律接纳倾听的神态,有时候如同一尊微闭双眼、表情冷漠的泥菩萨。对此,祈求的村民我行我素心怀敬意表情肃穆坚守着心中的信仰,他们觉得这才是神该有的样子。
香气袅袅日复日,炮竹声声年复年,莲花村一代又一代的人每天都是在这种状态下拉开了新一天的序幕,在大槐树无声地承诺下,开始了一天的劳作。
5
村里人对大槐树的依赖,不仅仅是将其视作神的化身,它还依靠自己天然的优势,尽着给村民提供庇护和福利的责任。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一年四季树枝上都挂满了树叶,树下方圆成为村民遮阴避暑之所;秋冬时节,你看到的是由绿转黄,在黄色的树叶还未落下之前,冬末春初时绿色又替代了黄色。特别是炎热的夏季,它的生命力更加的旺盛,不知疲倦的知了趴在树枝上此起彼伏欢歌吟唱,绣眼鸟、柳莺、鹊鸲等各种鸟儿在浓密的树叶中叽叽喳喳甜言蜜语,好客的喜鹊一大早就向村民们传递亲戚来了的喜讯,昼伏的猫头鹰趴在窝里闭着眼睛听着热闹,负责任的黄雀专心致志寻找着树枝上的小虫,唯有灵巧的麻雀来去自由无拘无束,蜻蜓点水般跳来跳去展示自由者的快乐……
中午时分,头顶火辣的太阳把村里低矮的砖瓦房变成了一个个蒸笼,劳作半天的男人便会搬一条板凳来到大槐树下,在一片荫凉下享受从田野吹来的阵阵凉风。特别是槐花盛开的时候,凉风中夹带着浓浓的花香直浸心田,可以让人顿时忘了一身的劳累瞬间进入梦乡。这大槐树下,是村里男人们整个夏天最惬意的去处,枝繁叶茂的大槐树此时就像一只带着一群小鸡在野外觅食的母鸡,在火辣的日光下,随时随地张开翅膀护卫着小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