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克松时代看美国的当代挑战
作者: 亨利·基辛格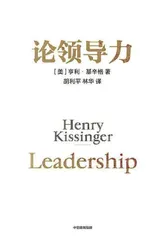
《论领导力》
[ 美] 亨利·基辛格 著
胡利平 / 林华 译
中信出版社
2024年3月
理查德·尼克松是美国历史上争议最大的总统之一,也是唯一一位被迫辞职的总统。同时,作为一位在冷战高峰时期重塑了已呈败象的世界秩序的总统,尼克松还深深影响了他任职期间的外交政策及其后果。
尼克松总统在5 年半的任期内结束了美国对越南的入侵,奠定了美国作为一个域外国家在中东的霸主地位,借打开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将两极化冷战置入一种三角动态格局,最终使苏联陷入战略被动。
从1968 年12 月尼克松邀请我出任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到1974 年8 月他离开总统职位,我始终是他的亲密助手,在他领导下参与了他的决策。在尼克松余生的20 余年里,我俩始终来往不断。
尼克松的挑战
我年逾99 岁,重提尼克松不是要炒半个世纪前是是非非的冷饭(我在3 卷本回忆录中已经写过了),而是为了分析一位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性格。尼克松就职总统时,美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文化政治动荡中。他毅然采纳了关于国家利益的地缘政治概念,从而变革了美国的对外政策。
1969 年1 月20 日尼克松宣誓就职总统时正值冷战高峰。在战后年代里,美国似乎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国力,在海外四处承担义务。如今美国无论在物质能力上还是情感上都开始对以往做出的承诺感到力不从心。
美国国内在越南问题上爆发的冲突已呈白热化。美国国内一些人士于是呼吁军事上从越南撤军,政治上收缩。当时美国和苏联正在部署有效载荷更重、更精确、具有洲际射程的导弹。苏联在远程战略核武器数量上与美国不分伯仲。一些分析家认为,苏联甚至有可能正在获得对美国的战略优势。美国人不禁忧心忡忡,担心会突然遭到末日袭击和长期政治讹诈。
1968 年11 月尼克松赢得大选前几个月,他出任总统后即将面临的挑战开始在三个重大战略地区显现:欧洲、中东和东亚。
1968 年8 月,苏联联合几个东欧国家出兵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此前捷克斯洛伐克试图在不脱离苏联轨道的前提下推行经济改革,结果成了它的一大罪状。在联邦德国,苏联对西柏林的威胁依然存在。莫斯科时不时发出威胁,要封锁处境艰难的西柏林。
对西柏林的威胁始于赫鲁晓夫。1958 年,赫鲁晓夫对几个西方占领国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它们6 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军。饱受战火创伤的欧洲和日本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伞下实现了复苏,开始与美国展开经济竞争。同时,欧日还对演变中的世界秩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观点,有时还是与美国相左的观点。
1964 年10 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后第5 个拥有世界上最具毁灭力武器的国家。北京在参与还是远离国际体系之间摇摆不定。
在中东,尼克松面对的是一个在冲突中挣扎的地区。1916 年,英国和法国缔结了《赛克斯-皮科协议》,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的部分领土被划分为英法势力范围。这一协议出台后,产生了一批阿拉伯穆斯林政权。这些政权看上去类似《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创造的那种国家体系的成员,其实这只是表面现象。20 世纪中叶的中东国家与依然处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之下的欧洲领土不同,既没有共同的民族身份认同,又没有共同的历史。
历史上法国和英国曾称霸中东。两次世界大战后英法元气大伤,势力日衰,无力向中东投射自己的力量。当地起于反殖民运动的动荡不断蔓延,演变成为阿拉伯世界内部以及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国之间的冲突。1948 年以色列独立后,两年内就得到了大部分西方国家的承认,现在正争取周边邻国的承认。而邻国认为以色列侵占了本应属于它们的领土,因此根本就是非法的。
孤立主义的流行
尼克松就任总统之前的10 年间,苏联开始趁中东走向大动荡之际与当地的专制军人政权搭上了线,中东更是乱上加乱。这些军人政权取代了奥斯曼帝国覆灭后留下的封建色彩浓厚的统治体制。由苏联武器装备的阿拉伯军队把冷战引入此前西方称霸的中东,导致该地区矛盾日益尖锐,有可能引发一场全球大灾难的风险随之上升。
尼克松就任总统之时,血腥的越南战争泥潭已是头等大事,以上关切均退居其后。前一届约翰逊政府向这一地区派遣了多达50 余万美军,这是一个无论地理上还是文化和心理上都与美国风马牛不相及的地区。尼克松宣誓就职时,超过5 万美军正在奔赴越南途中。
让美国从一场没有结果的战争中脱身的担子落到了尼克松肩上,而且是自美国内战以来国内局势最动荡之时接过的这副担子。
尼克松当选总统前5 年,美国国内政治分歧之剧烈,为美国内战以来所未见。约翰·肯尼迪总统、他弟弟(当时是呼声最高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和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先后遇刺身亡。美国各地城市街头爆发了激烈的反战示威,抗议马丁·路德·金遇害的示威游行遍及全国,华盛顿常常一连数日陷入瘫痪状态。
在美国历史上,国内因尖锐分歧吵成一团屡见不鲜,然而尼克松面对的局面前所未有。一个新兴的美国精英阶层坚信,战败不仅在战略上不可避免,在道义上也不失为一件好事。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信念意味着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一项共识—国家利益代表了合法目标,甚至可以说代表了合乎道义的目标—破裂了。
在一定程度上,这类观点标志着昔日孤立主义的冲动再次冒头。孤立主义者认为,美国“卷入”海外麻烦不仅丝毫无益于国家福祉,还腐蚀了它的性质。然而今天与昔日孤立主义的区别是,这股新孤立主义思潮提出的理由不是美国的崇高价值观不允许它卷入遥远地区的冲突,而是美国自身已腐败至极,没资格在海外充当道德榜样。
宣扬这一观点的人在高等学府先站稳了脚跟,之后影响越来越大,几乎左右了大学师生的思想。他们既没有从地缘政治角度审视越南悲剧,也没有把它视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而是把越南悲剧看作全民情绪宣泄的先兆,激发美国做早就该做的事—自扫门前雪。
(本文获出版社授权,标题为编者所加)
责任编辑董可馨 [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