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礼议”的政治面相
作者: 叶克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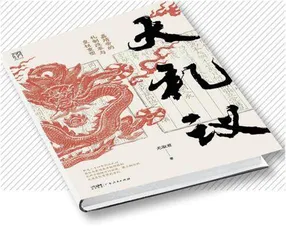
“大礼议”是明朝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震动整个朝堂,催生了180多位文臣被打伤、17人被打死的左顺门血案,严嵩、夏言、杨廷和和张璁等人相互倾轧。
现代人看起来似乎寻常无奇甚至有些无聊的“大礼议”,实际上关乎权力、制度和文化的角力,也是明朝中晚期政治衰败的标志性事件。
大礼议的背景和事件本身都相当简单,正德帝身后无子,由朱厚熜继位,也就是嘉靖帝。文官系统想干一件事,就是请嘉靖帝入继大宗,作为嗣子,改认堂伯弘治帝为父,而称生父朱祐杬为叔。嘉靖帝不愿听从百官,一心追尊其生父母,自此引发“大礼议”。朝中形成两大阵营,“人情论”强调人伦亲情,主张“继统不继嗣”,“濮议论”坚持宗法正统。
除了不惜以武力制造左顺门惨案之外,嘉靖在法理和言路上进行了一系列动作,包括编纂《明伦大典》,构建皇权正当性的理论文本;编造罪名以阻塞言路,扼杀士人“为王者师”的政治理想;不断变更国家礼法,名为“恢复祖制”,实为提高生父的政治地位,巩固自身皇权。
最终,嘉靖帝成为胜利者,博弈多年后,他如愿将生父称宗祔庙,也达成了皇权重塑、小宗变大宗的目的。但与此同时,以“礼”为主的政治文化体系被破坏,皇权私化,名分礼秩混乱。影响最为深远的是,他为操控群臣,大张阁权,几易首辅,朝廷政治风气日下,为党争愈演愈烈创造了条件。
大礼议并不仅仅是表面上的是否入继大宗问题,它有着更深层的角力:皇权与士大夫之争,皇权与礼法之争。群臣希望“法在君上”,嘉靖希望“君在法上”,嘉靖希望的是通过这件事告诉群臣,自己的权力大于礼法、大于群臣。
能够在这场长时间的政治角力中夺得胜利,嘉靖帝的精明和韧性一样都不会缺。在传统认知中,嘉靖帝是典型的昏君,多年不上朝,将政务弄得乱七八糟。
但实际上,嘉靖帝智商极高,只是高开低走:15岁时只身从湖北入主紫禁城,年幼时并未有过耳濡目染和太子式的政治训练,但却能迅速适应自己的新位置。在大礼议之争中,他一步步突破老臣的管控,达到自己的目的,继而又对朱元璋创建的礼制进行大改革。
他将朱元璋独创的天地合祀改回天坛、地坛分祀,将朱棣升格为“成祖”,降低孔子与孔庙的道统地位,将孔夫子兼具道统与政统地位的“文宣王”称号去掉,改为只是“至圣先师”的道统地位。尤其是在国子监增建敬一亭,为嘉靖帝对经书批注的圣训树碑,确认了皇权的诠释经典权,这一步在现代人眼中可能不算什么,但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却影响极大。
可以说,正是嘉靖帝的一系列动作,使得明代皇权达到高峰,专制程度尤胜酷烈的朱元璋时期。
在《大礼议:嘉靖帝的礼制改革与皇权重塑》一书中,尤淑君探讨了大礼议的政治面相。推动大礼议,是为了皇权的加强,而嘉靖帝之所以要加强皇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一种合法性辩护。正如尤淑君所言:“嘉靖皇帝之所以屡屡宣传自己继承君统的正当性,正因为其政权正当性不足以让士人信服……”
基于这一出发点,嘉靖帝的每一步都有确定目的。《大礼议》提及嘉靖帝将朱棣尊为成祖一事时,就这样写道:“为了避免众臣批评自己过于尊父的行径,嘉靖皇帝改永乐皇帝的庙号“太宗”为“成祖”,让朱棣的政治地位大幅跃升,成为名副其实的创亚之主,得到与太祖相等的尊荣,也强化了朱棣在君统上的正统性。”
嘉靖皇帝命人编纂《明伦大典》,仿效永乐皇帝命人制定《永乐大典》。而《明伦大典》对于嘉靖乃至明廷来说都影响巨大,它“让嘉靖皇帝间接剥夺了士人的话语权力,得控制解释权,让天下之是非皆出于朝廷,朝廷之是非皆出于皇帝”。
对于明廷士大夫而言,嘉靖帝的表现超出了他们的预计。谁也不会想到,以外藩入主帝位的年轻人,竟然会如此强硬。当年的朱棣,兴兵“靖难”,清洗建文朝旧臣,但那是立朝之初的动荡。可嘉靖帝即位后,大明立国百年,皇权稳固,强藩不再,大家都不会认为这次皇权交接有什么大问题,可嘉靖帝却给了他们一个大意外。
“礼”在古代王朝的统治中极其重要,它的范式可以帮助人们建立共同遵循的认知框架,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历朝历代都有许多君主借礼制的维系或变化,来实现一些不愿宣之于口的隐秘目的。嘉靖就是如此,他挑战传统礼法,实际上是为了打破旧框架,重新分配权力。
明代政治架构原本就相当特殊,书中写道:“明太祖废中书省,代表宰相制废除,中央政制为之一变,六部尚书是官僚体系的最高长官。内阁大学士本是皇帝处理政事的私人顾问,秩位不高,仅正五品,却有票拟诏书之权,得出纳王命、审查奏章、决定政策。积时既久,渐成皇帝与众臣沟通的枢纽,同时分侵六部尚书的议事权,六部仅负行政责任。然而,首辅之秩位甚卑,必须兼尚书衔,方能提升威望,从来不是真正的宰相。一旦内阁与六部发生争执,六部可站在法理的角度,批评首辅越级揽权,是为权臣,无大臣之体。首辅的执政地位,难获朝野一致的承认。首辅的职位与职权既不相符,职权与职责又无直接关系,却成为政事的总枢纽。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实难得到合理的结果。”
从武宗驾崩到朱厚熜即位的39天内,杨廷和等阁臣凭着《武宗遗诏》赋予的权力,又获得昭圣皇太后的支持,因而能打破惯例,独断朝政,有效防止叛乱,剪除了江彬、钱宁等人,士气为之大振。内阁权势的扩大,让原本是政府首脑的吏部尚书权力大为削弱,反而得听命内阁,造成权力中枢转移,甚至在决定嗣君人选时,杨廷和等人唯恐泄漏消息,竟违反廷议的常规,坚持不让吏部尚书王琼等官员参与其事。
可在大礼议一事中,皇权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杨廷和这种见惯风浪的名臣,在这场角力中也无法占得上风。当嘉靖帝欲在兴献帝、兴献后的尊号上加称“皇”字,命礼部商议时,杨廷和极力反对,援引汉宣帝、光武帝二例,说明“统嗣”必须合一,不容分离。一旦为兴献帝后加尊“皇”字,其身份便等同孝宗皇帝、昭圣皇太后,“是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
最后,杨廷和还扬言说,若欲加“皇”字,便要辞官回乡,不再接受挽留。支持“濮议论”的官员们为支持杨廷和,纷纷上疏反驳《大礼或问》,阁臣蒋冕也著《上嘉靖皇帝为后疏》,试图打消嘉靖皇帝的念头,却无法全盘反驳“人情论”,也无法让嘉靖皇帝回心转意。
同时,张璁等朝中新贵从礼法、皇权两个层面强调“人情论”,并催生了《明伦大典》,让杨廷和等老臣黯然退场。但即使是张璁等人,也有自己的立场,不会无底线附和皇帝。嘉靖提议北迁显陵,就遭到两派大臣的一致反对。
想要控制朝臣,就得另想办法。嘉靖的办法是提高内阁首辅的权力,以其作为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的缓冲。可与此同时,又不能违背明朝不立宰相的祖训,对内阁首辅又要予以限制。这种身份上的模糊,使得嘉靖时期的内阁首辅一方面权力极大,但另一方面又极其高危,很容易成为文官系统的眼中钉。
正如《大礼议》中所写:“当首辅失宠时,久受压抑的言路随即反扑,攻击首辅。六部部臣也会附和言官,暗中支持。首辅只能依靠皇帝出面,平息舆论,或指使另一批附己言官,代为辩驳,否则就得上疏乞休,告老还乡。皇帝是否愿意代为平息,端视皇帝与首辅之间的君臣关系。若双方的信任基础稳固,皇帝便保全首辅,严惩攻击首辅的言官,容易造成政局紧张;反之,若双方猜忌不已,皇帝乐见言官攻击首辅,好安排亲信入阁。”
所以,嘉靖朝历任首辅,除张璁“平安着陆”之外,其他人多半不得善终,比如在菜市口被杀的夏言。
可以说,在大礼议之后,嘉靖是唯一赢家。内阁首辅的首要任务就是取得皇帝的信任,不可能出于公心处理事务,官员出于对皇权为所欲为的恐惧,也会结成各种小团体,一方面针对首辅,一方面抵御皇权,党争倾轧之祸也由此而生。
至于嘉靖,他确实得到了远超此前的皇权,但对既有原则和政治体系的破坏,造成了君臣冲突,也造成了社会失序。明朝的命运,此时已经注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