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恨水戏曲改编的小说
作者: 方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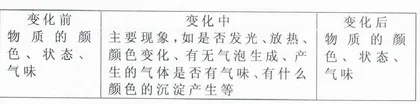
摘 要: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原本擅长写作世态言情小说的张恨水转而将目光投向了以四大传说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民间戏曲,并通过对它们加以改编而创作出了一系列的同名小说。本文试图透过这一现象探寻其背后的本质。
关键词:戏曲; 改旧编新; 改编原因; 如何改编; 改编条件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315(2013)10-022-002
《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作为我国的四大民间传说,历来便是以传统戏曲为代表的民间文艺的取材源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张恨水通过对四大传说为主的民间戏曲的改编和再创造,创作了一系列的同名小说。本文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揭示作家创作转向的原因,具体分析这批作品的改编状况及其实绩,并进一步论述作家改编所具备的条件。
一
极其善于写世态言情小说的张恨水,转而去从事民间戏曲的改旧编新工作,这一现象背后的含义是多样化的。从文学的大环境来讲,在五十年代高度政治化的语境下,“通俗小说”作为“革命大众文艺”的对立面,属于非主流且被压抑的一支,通俗小说作者对题材把握稍有“不当”,便会受到批评,因而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也是不难理解的。[1]包括张恨水在内的一些著名的通俗小说作家基本停止了这一类型的小说创作,转而将目光投向了较为“稳妥”的中国古代戏曲和民间故事,这也就有了《梁祝》等小说的诞生。从张恨水个人来讲,作者的健康状况是无法忽视的因素。张恨水由于脑溢血半身不遂,记忆力遭到很大破坏,几乎丧失语言能力。在此之后,虽然他奇迹般地康复并逐渐恢复了写作能力,但不得不承认其才情的锐减,正如作者自己所言:“以前语言词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2]以上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也迫使作者对自己的文学创作策略作出一定的调整:变长篇为中篇,变创作为再创作。
张恨水有着报人和通俗小说家的双重身份,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里有其独特性。张恨水通过改编《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白蛇传》《牛郎织女》等传统民间戏曲而创作出的通俗小说,也确实表现了古代人民的美好品德,陶冶了当代人的情操。从以上普及性与教谕性两方面来考察,张恨水对传统民间戏曲的改旧编新,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成与其办报纸、写小说的初衷殊途同归。
“我做小说……当然距离党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写工农兵生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方针差太远了。几年来在病中眼看着文艺界的蓬勃气象,只有欣羡。老骆驼固然赶不上飞机,但是也极愿作一个文艺界的老兵,达到沙漠彼岸草木茂盛的绿洲。”[3]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张恨水作为一个通俗小说家在当时谨小慎微的心态。正如作者自己所言,对民间戏曲的改编,既是出于当时文艺政治化和健康状况恶化的无奈之举,更是出于对祖国和人民的挚爱而让自己文学生命的变相延长。
二
张恨水通过改编戏曲得来的这一批通俗小说文本,不应忽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的成功。
1.思想内容上的革新
五十年代之初,新中国加强了对戏曲艺术的重视,加大了对传统戏曲改革的力度。部分剧目中落后的思想内容是改造的重点之一。张恨水对传统戏曲的改旧编新便发生在这样的背景之中,其对落后思想内容的改造又体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戏曲是在封建社会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艺术形式,其虽然取材于民间,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但又经过了封建文人的雅化,带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情况便导致了传统戏曲内部矛盾的产生:在体现出一定的人民性、革命性的同时,却又显得极不彻底。张恨水在把戏曲改编成小说的过程中对传统戏曲里损害思想意义的部分作了有效的修改。如《白蛇传》结尾由原来的许士林拆塔救白蛇改为由同属被压迫阶级的小青练成技艺后打败守塔天将而救出白蛇。张恨水作出的这些修改,不但很好地解决了传统戏曲中的思想含混问题,而且对戏曲中原先便存在着的反封建思想作了加强,增加了作品革命性和人民性的内容,提高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另一方面,传统戏曲虽然经过了一个文人雅化的过程,但它毕竟取材于民间,在传承了民间文学清新质朴、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等特色的同时,也沾染了一些不良的习气,即民间文学自身不可避免的藏污纳垢的内容。张恨水在把戏曲改编成小说的过程中较好地克服了上述缺点:他的这批小说内容精致,文辞优美,对于传统戏曲中的色情内容予以删除或者加以另一种形式的含蓄表现,并在不妨害原有情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的除去了封建迷信的内容。
综上所述,张恨水通过改编传统戏曲创作出的这批小说,不但超越了封建思想的局限性,而且克服了民间文学自身的一些弱点,极大地提高了作品的思想价值,这与五十年代戏曲改革的主潮也是完全相符的。
2.文体形式上的探索
戏曲与小说都具备极强的叙事功能,两者都善于情节的建构,但也都有各自的特点。如何充分地利用有限的情节来极大地发掘出其中的审美价值就成为戏曲面临的重大课题,经由这一课题催生出来的是一套“戏曲式”的情节建构原则。张恨水在这一批小说创作里对它们就有所借鉴:
1.无奇不传
戏曲剧本曾经被称为“传奇”,这说明了戏曲中叙写的事件都是奇特的,非同寻常的,而不是人们生活中习以为常的普通事物,只有保证了事件的“非常”性质,才能使戏曲里有限的情节在观众的内心留下深刻印象。小说《梁山伯与祝英台》里第七章“疾病相扶持”中有这样一段情节:祝英台得了急病,梁山伯(此时尚不知英台为女性)为了方便夜间照顾屡次提出要与之同床,祝实在无法回绝,只得编造谎言说自己有个习惯:“凡是与弟同床的,弄个纸盒子,里面装满了灰,放在外边锦被之间,睡觉的时候,谁要不留神,打泼纸盒子里一点灰土,那就明天受罚了。”梁竟然相信并照办。这段情节的功能除了在于表现梁的忠厚老实之外,很大程度上在于事件本身──读者在阅读这件“奇”事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其中的趣味,这件“奇”事在被阅读的过程中也在读者内心打上深厚的烙印。
2.误会
包括戏曲在内的舞台艺术经常会通过设置误会来吸引观众,活跃舞台的气氛。小说《秋江》第十章,潘必正从土地庙回来,正因未能见到妙常而失望,书童却告知“她”已经来过,潘十分兴奋,一连串问了关于“她”的好多问题,在得知“她”说以后天天要来时更是欢喜异常。
在那段对话里,老尼(姑母)并不是潘必正话语信息的真正受体,所以对他说出的每一句话都产生了误会。这样的误会设置,极大的增添了小说的趣味性,使得文中戏味十足。
3.悲喜交错
中国戏曲历来讲究悲喜交错,究其原因至少有三点:中国古典文论推崇一种“哀而不伤,乐而不淫”的中庸美学;戏曲作为一门舞台艺术,气氛的过冷或过热都会令观众反感;悲喜相间往往能够相互映衬而起到一种悲后更喜、喜后更悲的演出效果。张恨水通过改编戏曲得来的这批小说,在情节的建构方面对传统戏曲借鉴的地方还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但它们存在这样的共性:注重对情节的精雕细刻。这与戏曲“有戏则长,无戏则短”的精神也是相符的。
小说这一体裁相对于戏曲的最大优势在于它较少受时空等因素的限制,以极大的容量来编织复杂的情节,张恨水便充分利用了这一点:
首先,这批作品在传统戏曲原有情节的基础上作出了巨大的变更。这种变更是从戏曲到小说的情节完善工作,是在戏曲主体结构不变的前提下对原有情节的重新编织,这其中既有充实,又有调整。其次,这批作品展示了小说叙事灵活多变的特点。最后,这批作品充分发挥了小说善于写实的长处。
综合上述两段,张恨水通过改编中国传统戏曲而创作的这一批小说,在情节的建构上对戏曲与小说两种体裁都有所借鉴,以上论述只能说是挂一漏万,但这些借鉴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它们兼得了戏曲情节的精致与小说情节的容量,汲两者之所长,无疑是非常成功的。
3.人物刻画上的兼容
戏曲与小说作为叙事型的体裁,都十分注重对人物形象的刻画,但是两者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从戏曲方面看,中国传统戏曲以唱、念、做、打为表现手段,这就决定了剧本主要是通过对语言、动作的刻画来塑造人物。戏曲作为一门舞台表演型艺术,剧作家无法跳上舞台直接向观众描述人物的性格特点,只能以舞台为中介,隐藏在幕后,让人物通过台词、动作来体现自己的个性特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传统戏曲在心理刻画方面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障碍。从小说方面看,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正是其所长。小说相对于戏曲是更具私人化的文学样式,作者往往以全知视角来编织情节、刻画人物,这无疑为展示人物的内心提供了巨大便利。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的是,一部分小说(主要是指中、长篇小说,但不包括中国古代章回小说,它们由民间说书人的脚本发展而来)由于具备了较大的容量,往往只注重通过情节的安插来刻画人物而忽视了对语言、动作的描写,这在一定程度上就使得人物形象显得不够具体,有时候甚至是只见事不见人。张恨水通过改编戏曲创作出的这一批小说,在人物形象的刻画方面汲取两种文体的优点,较好地融合了语言、动作和心理描写。
三
文学史上经由小说改编成剧本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但把戏曲(戏曲文本也是一种戏剧脚本)改编成小说的情况却极其少见,张恨水能在对传统民间戏曲的改旧编新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方面,深厚的戏曲底蕴为他的改编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张恨水可以说与戏曲有着不解之缘。而作为一名报人,他以报刊为园地,联系当时的演出现状,针对包括京戏、川戏、黄梅戏、昆曲等多种样式的中国传统戏曲发表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小说家,他在自己的通俗小说里塑造了包括名角、歌女在内的许多戏剧人物形象,以京剧曲牌给小说命名(《夜深沉》),以自作的南曲散套作为小说的楔子(《斯人记》)。作为一名父亲,他带家人出去看戏,并向子女传授有关京剧的历史知识。另一方面,一些事实也不应该被忽视。张恨水以善于写作世态言情小说而著称,其之前的小说创作(作为一种“前结构”)无疑对他的戏曲改编工作有所裨益。从内容方面看,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主要涉及两种题材:男女爱情故事是他善于表现的,《啼笑因缘》中的樊家树与沈凤喜,《金粉世家》中的金燕西与冷清秋,他们之间的爱情或因为军阀霸占,或因为世俗偏见,都不得善终;对于黑暗强暴的揭露他也得心应手,《春明外史》《八十一梦》等小说表现得都较为突出。值得一提的是,以上两种题材在张恨水的同一部小说中往往是相互融合的。张恨水改编的戏曲就是如此:有的侧重于反映青年男女反抗封建礼教,力争自由民主爱情(如《梁祝》《凤求凰》《牛郎织女》《秋江》),有的侧重于反映劳动人民不畏强暴,坚持抗争(如《孟姜女》《白蛇传》),这些都是张恨水熟谙的题材。张恨水针对这些传统戏曲所进行的改编,自然是如鱼得水。从形式方面看,张恨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便存在着一种类似戏曲式的思维方式。在人物刻画的技巧方面,张恨水有自己独特的一套“表演法”:每当对某个人物的动作、神态拿捏不准时,他便会面对镜子表演那个人物,“那不容易着笔的地方就写出来了”。在处理情节与节奏的关系方面,张恨水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传统戏曲有所借鉴。中国传统戏曲为了加强悬念,增强紧张感,在处理演唱时常用紧拉慢唱的方式,通过节奏的快慢对比来增强演出效果。这对张恨水在情节与节奏的把握方面有所启发。一般来讲,以冲突激烈为特征的情节,节奏通常较快,而以冲突缓和为特征的情节,节奏往往趋缓。张恨水在其小说创作中有时候会反其道而行之。如《啼笑因缘》第十九回“山寺除奸”这一段文字,明明将要写到关氏父女上山刺杀刘德柱,作者却将笔锋一转,转而去叙述樊家树的胆怯心理,吊足了读者的胃口。总之,张恨水小说创作中的戏曲式思维方式,对其之后改编中国传统戏曲的工作无疑是有益的。
综上所述,张恨水深厚的戏曲底蕴以及他之前的小说创作,为他在五十年代将传统戏曲改编成小说的成功做了重要的铺垫。
总之,在漫长的戏曲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传统戏曲取材于人民大众口耳相传的生动故事,另一方面,这些来自民间的题材不断被文人所雅化,提升了戏曲的艺术品质,而它被搬上戏台后,其成功的舞台演出也反过来促进了其在民间的传播。这种活动是双向的,互动互补的。张恨水的价值在于他打破了这种封闭自足的结构,在改编传统戏曲的基础上构建了一批具备较高质量的通俗小说文本,它们在文学作品较少、文学质量普遍不高、文学题材又相对单调化的五十年代显得格外宝贵,它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小说的题材领域,丰富了小说的审美表现,为戏曲在普通百姓中的普及与提高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张友鸾.《对〈神龛记〉的初步检讨》,文艺报1952年第9期
[2]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10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3]《文史资料》,1980年第70期
[4]张恨水.《序〈秋江〉》,《〈秋江〉〈凤求凰〉》,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3月朝阳第1版
[5]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6月北京第1版
[6][7]张恨水.《写作生涯回忆》,第340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第1版
[8].张正.《张恨水记传》,第136页,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