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飞腾:我愿做一辈子“冰川医生”
作者: 雪舟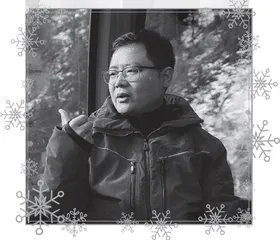
“你们知道吗,我国西部地区的生产生活用水多数来自冰川消融。保护冰川,就是保护人类自己……”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的一所中学里,“冰川医生”王飞腾正在为学生科普冰雪知识。
2004年,王飞腾考上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误打误撞进入冰川学方向学习。刚入学不久,导师就带着王飞腾直奔新疆天山1号冰川观测站。沿途山高谷深,地势落差极大,冰川融水源源不绝。越接近冰川,气温越低,他竟在一天内感受到了四季的温度变化。经过半天的高山跋涉,登上位于海拔4000多米的观测站时,入目的是瑰丽又壮观的冰塔林、冰茸、冰桥……巨大的震撼之下,他久久不能言语。自此,王飞腾开启了一段与冰川的不解之缘。
王飞腾最先研究的是成冰过程。他在冰川上挖一个雪坑,并在每层积雪上做标志,每周上一趟冰川进行观察、记录。在山地冰川,成冰过程是缓慢的,500克的新雪往往只有约20克到30克能保留在冰川中。不知不觉,王飞腾观察了三年。此后多年,他坚持在不同的冰川高海拔区域进行野外观测。科研之余,他还前往小学、中学、高校,开展冰川知识科普讲座。
2016年,作为中国科学院的研究员,王飞腾接到了为北京冬奥会滑雪场进行雪务保障的工作。“什么是冰状雪赛道?为什么要制作冰状雪赛道?”尽管从事冰川研究和保护工作多年,但他仍对冰雪赛事的很多概念未曾耳闻。原来,冰状雪赛道是指滑雪场表面有一层薄的硬冰壳,可以减小赛道表面和滑雪板之间的摩擦力,且不易损伤滑雪板。但是,制作冰状雪的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想要制作一条高质量的冰状雪赛道,着实不易。作为领头人,王飞腾带着团队奔波于全国各地的滑雪场,不断进行冰状雪赛道制作实验。他们每天忍耐着低温、寒气,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铺雪、注水、压实、测量、分析……在成百上千次的试验后,他们研究出在冬天下的新雪上覆盖隔热反光布料的方法来储雪,终于攻克了冰状雪赛道制作的关键问题。
制作冰状雪的经历给了王飞腾灵感:能不能把这个办法用在冰川保护上?他想起自己第一次去四川达古冰川时,景区的人急切地找到他说道:“王老师,我们这个冰川过几年就要消失了,到时候景区名字都要改了!”过去50年来,达古冰川的面积缩减了70%,王飞腾认识到保护它已经迫在眉睫。北京冬奥会的工作完成后,他马上行动起来,带着团队登上达古冰川,准备开展减缓冰川消融的试验。
王飞腾到达达古冰川时是2021年8月5日,正是达古冰川消融季。王飞腾不敢停歇,用最快的速度选取了500平方米的试验场,随后在冰川表面铺设隔热反光布料。他形象地将这称为“盖被子”试验。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他才将所有材料都覆盖在了试验场的冰川上。等终于直起腰时,他才发现双手早已冻得又红又肿。
之后,王飞腾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观测和记录数据,默默期望着“盖被子”真能保护达古冰川。两个月后,他小心地从试验场的冰川表面移开隔热反光布料。他用肉眼就已经看出,“盖被子”的冰川与没“盖被子”的冰川相比,消融的部分更少、更薄,差不多有1米厚。记录的数据也证实了这一点:消融速率明显变低,总消融量减少了34%。看到这个结果,王飞腾欣喜若狂地说道:“这说明‘盖被子’对减缓冰川消融是行之有效的!”
但王飞腾也深知,我国的48571条冰川中,仅有四五十条是人类足迹可以到达的,连千分之一都不到。“对于无法到达的冰川,该如何保护呢?”这是一直萦绕在王飞腾心头的担忧。在他看来,做冰川保护研究,更像是医生面对一位癌症患者:“我们给冰川开了药方,但阻断不了它消亡,只能减缓。比如,这个病人原来能活到80岁,经过我们的治疗后,现在能活到85岁或90岁。”
这些年,王飞腾不断寻找着新办法,想延续冰川的“寿命”。他曾在天山1号冰川做过人工降雨增雪减缓冰川消融试验,最新的设想则是把造雪机放到冰川上,尝试将冰川融化形成的湖水直接造雪,反过来再保护冰川。
如今,王飞腾已经与冰川结缘近20年,仍然初心不改,他说:“这是一门‘冷’学科,所以需要付出更多的热情,而我愿意做一辈子的‘冰川医生’。保护冰川,我们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