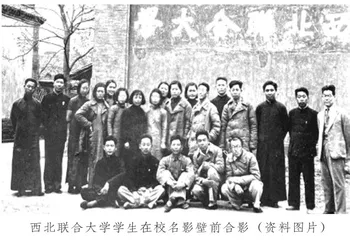教育救国的践行者陈剑修
作者: 齐悦陈剑修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后投身教育界,在教育实践中勇于革新,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武汉大学教授及浙江大学系主任、中央大学教务长、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广西大学校长等职。
陈剑修,原名陈宝锷,又名陈剑翛,出生于赣西遂川县泉江镇,青年时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传到东方,引起北京青年和学术思想界的震动,革命思潮在中国汹涌澎湃。北京大学在校长蔡元培“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下,学术气氛空前浓厚,各种思潮异常活跃。在北大求学的陈剑修积极投身爱国运动,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骨干。陈剑修和同学段锡朋、许德珩、周炳琳等人创办了《国民》杂志,他把强烈的爱国热情凝聚笔端,发表文章,撰写社论,批判北洋当局政治腐败,发表及编辑的文章深受读者喜爱,获得校长蔡元培和教授鲁迅、李大钊的赞赏。《国民》杂志刊载了北大经济系学生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前半部分,这是《共产党宣言》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个译本,有力推动了当时青年的思想解放。
1920年,陈剑修从北京大学毕业后,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潜心于教育理论研究。他认为“教育的力量就是要把社会上的人,造成有相当的技能、知识与品性的方法和态度,然后方能参加并适应各种社会组织的共同生活”,并提出“在教育思想上便是要注意个性的发展”。这时的陈剑修已在学界崭露头角,1925年受派赴爱丁堡出席世界教育会议。
倡导普及教育之由
1927年,陈剑修留学归国后便被委以重任,出任南京市政府教育局局长,这个职位为他提供了施展抱负的舞台,他为革命功勋子女申请免费就学机会,普及中小学教育。为掌握学龄儿童数量,确定未来教育经费分配及学校开设,教育局委托警察局调查南京户口、登记南京市6—12岁学龄儿童情况,不料此事将他卷入一场风波。
1928年开春,陈剑修倡导开展学龄信息普查,引起南京城内流言纷纷,城里10岁左右的孩子胸前都悬挂着一块红布条,上面写着“石叫石和尚,自叫自承当;快快回家转,自己背石板”“你造中山墓,与我不相干,一叫你魂去,再叫你去当”等避邪歌诀。原因是教育局调查户口和学龄前儿童数量情况涉及孩童生辰,这与当时流传孙中山陵墓即将完工、石匠需要各160个童男童女生魂以合龙口的谣言赶巧碰在一起。彼时,传言南京东门一带已有多个孩童被摄魂而亡,市民只有在孩子身上佩戴符咒红布才能避免被摄走魂魄。中山陵摄魂的谣言逐渐在全城蔓延,到处弥漫着恐慌的气氛。
南京市教育局处于风口浪尖之中,陈剑修主持教育局召开扩大会议,会上提议印发广告,解释调查户口和学龄儿童是为办理市政、兴办教育,以此来消除市民的误解。很快,教育局就发布公告辟谣,向学生家长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意义以打消他们的疑虑。陈剑修向公众解释调查学龄儿童的良好初衷,他指出,“如果我们不晓得学龄儿童是多少,我们如何知道要办多少学校,要请多少教师,以及需要多少经费……不料正在实施当中,竟发生许多笑话出来”,并对中山陵摄魂谣言进行反驳:“如果世界上真有妖邪恶劣的当道,要着你们的小孩子的命或灵魂,还来公开地调查么,早就秘密的捉将去了。”
陈剑修及教育局的举措未能阻止谣言传播。随后,《京报》发表《摄魂把戏》一文,描绘南京可能出现的可怕局面:“商旅裹足、家家闭户,柴米油盐,无人挑卖,几十万市民坐而待死而已。”《京报》记者推测,孩童的离奇死亡可能是因节气引发的某一种流行传染病所致。教育局、公安局等部门联合农、工、商、妇女团体的专业人士召开研讨会探讨辟谣之法。经医生诊断,孩童死亡原因实际上是一种脑膜炎的流行病所致。查明了事实真相,陈剑修便安排教育局所有人员到学校辟谣,并向百姓解释摄魂纯属荒诞不经的谣言,谣言实际上是反动分子刻意散布和时疫流行所导致。陈剑修还亲自撰写五条辟谣标语“莫信妖人摄魂的谣言”“严防反动分子鼓动邪说”“邪说是煽惑人心的”“只有疾病能死人,邪术是不能死人的”“破除迷信,消灭邪说”,广为宣扬,呼吁市民不要轻信谣言,应当注意自家孩童的卫生健康。

在陈剑修的推动下,整个南京被动员起来,各界自发组织废除迷信宣传队,公开辟谣,以正视听。南京市市长向公安局下达政令,要求扩大民众知情权,把涉及谣言的几十起案件审讯详情公开。市政府发布布告,解释摄魂谣言,公布谣言的审讯结果,证明摄魂之事皆为子虚乌有。这场闹得沸沸扬扬的妖术摄魂谣言逐渐平息。经此风波,陈剑修认为普及教育、提高民众素质、培养公民科学素养迫在眉睫。
担任边疆教育机构首任司长
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我国的民族危机和边疆危机加深,严峻的情势促使南京国民政府将注意力投向边疆地区,有识之士也纷纷认识到要开发边疆就必须发展边疆教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藏等边陲之地教育极为落后,除寺院教育、少量官方贵族教育和民间私塾教育,无严格意义上的近代教育。这种教育状况使得西藏民众的思想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和保守倾向,制约着边疆的发展,也为帝国主义的入侵提供便利。
1929年,教育部部长蒋梦麟委任社会教育司司长陈剑修筹备设立蒙藏教育司。1930年,蒙藏教育司正式成立,陈剑修成为首任司长,主持擘画蒙藏地区的教育发展,主管业务包括:调查蒙藏地区教育状况,兴办蒙藏地区各级各类教育,培养蒙藏教育师资,奖励蒙藏子弟入学读书,筹集蒙藏教育经费,筹办蒙藏教育事业。
蒙藏教育司创立伊始,仅下辖一科,科室只有科长、科员、书记员三人,科室业务有限,人力财力紧缺。作为中国第一个管理少数民族教育的中央机构首任司长,陈剑修深感任务艰巨,他对边疆现状进行深入调研,认为蒙藏分处西北,因其气候、地势相似,人民生活方法及社会状态、礼节仪式,亦大略相同;一般民众,以游牧为业,不事生产。所谓教育,除了休息时唱歌、讲述故事及神话,仅贵族仕宦子弟或喇嘛信徒浏览一些宗教图书与圣书。因此,蒙藏教育司拟于最短时间内,在南京创立蒙藏中学,分设两种班级,授课对象分别为蒙藏升学青年和内地愿赴蒙藏的工作人员,培养向蒙藏人民宣传新式教育理念和国家有关边疆教育的政策法规的宣教人员,让蒙藏边疆民众充分了解和认识发展边疆教育的重要性。
鉴于边疆与内地教育实际情况的不同,内地各级学校教科书无法在边疆学校统一使用,尤以中小学校为甚,陈剑修因地制宜开展蒙藏边疆教育:教材使用方面,参酌现行中小学教科书,依照蒙藏特殊情形编订蒙藏中小学校课程标准及教材或民众用书;教育行政方面,在蒙藏各盟旗各宗设立教育行政委员会,主持所有教育事宜,并进行一般学务调查;普通教育方面,将东蒙海拉尔蒙藏中学、辽宁蒙旗师范、西蒙土默特旗初级中学、太原蒙藏特班进行整改,再定其他地方中学的设立标准;高等教育方面,饬令北平、中央两所大学设立蒙藏班,并规定蒙藏学生出洋留学名额及办法,以资鼓励。
陈剑修在短短一年任期内,促成蒙藏教育司与蒙藏委员会共同制定了蒙藏教育的发展规划,调查了蒙藏地区教育现状,研究了边疆教育方法,督促蒙古地区兴办教育,整顿蒙藏学校并筹建了几所蒙藏专门学校,保送了大量蒙藏籍学生入读专科学校和大学,编写了蒙语、藏语与汉语合璧的双语教科书及短期小学与民众学校的课本,促进了蒙藏地区教育的发展,推动了边疆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事业的协调发展。
振兴乡梓教育
1932年,陈剑修调任江西省教育厅厅长,这是他北上求学、教学、从政十余年后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任期内,陈剑修勇于改革,敢于创新,使江西教育面貌焕然一新。
到任后,陈剑修发现江西一些教育官员和中学校长很不称职,其中不少人是他的北大校友,有的还有私交。陈剑修为人耿介,任人唯贤,为学认真负责,不徇私情,他大刀阔斧进行人事改革,撤换北大出身的一中校长,改派北师大教授曾仲鲁继任,改变了江西教育系统的不正之风;改变长期以来北大一派独霸江西教育的不合理局面;废除文牍主义,简化办事手续,提高行政工作效率,要求各学校对上的请示报告等办文,一律不用烦琐公文,改用便条或口头报告。
陈剑修到任伊始,发现南昌很大一部分中小学生患有瘌痢、沙眼及蛔虫病,严重影响身体健康和正常发育成长。针对以上情况,江西省教育厅设立了健康教育委员会,切实加强对中小学生卫生保健和疾病防治工作的管理,提高学生身体素质,贯彻德智体并重的教育方针。健康教育委员会会同医疗卫生、保健部门开展瘌痢、沙眼及蛔虫疾病的治疗防护,仅一学期即收立竿见影之效,经复查,学生中基本消灭了瘌痢和蛔虫病,沙眼重则减轻、轻则痊愈。学生恢复健康,精神饱满,学习热情高涨,校园里一片蓬勃向上的朝气。
1932年1月,南昌国民政府借口经费支绌,迫使38所公立小学全部停办,失学儿童除小部分转入20余所私立学校就读,大部分闲散在外。陈剑修为解决学生失学和教职员工失业问题,亲自出面与省市财政部门协商解决经费问题以恢复停办小学复学复教,省教育厅成立省会小学管理委员会专司其事。省会小学管理委员会将督学改为视导员,陈剑修任主任委员,下有视导员3人,常到各校协助校长做好行政工作,辅导教员课堂教学,改进教学工作方法,开展学生课外活动。从此,检查、指导、改进小学教育工作逐渐走上规范化、制度化轨道。
在陈剑修的努力下,教职工按月领取工资,生活无忧,安心教学,各学校很快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一个学期之后,陈剑修把停办的38所小学交归南昌市教育局接办。
参与主持高校西迁
陈剑修不仅有在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机关主管教育的资历,也有在大学从教和管理教务的履历。他先后在浙江大学、武汉大学、中央大学、国立广西大学等校任教,爱护培植青年学子是他的一贯作风。1934年,陈剑修应北大同学罗家伦之邀,担任中央大学教务长,“三顾茅庐”从上海请来国画大师徐悲鸿,让徐担任中央大学美术系主任,一时传为佳话。陈剑修慧眼识英才,只要发现可造之材,就加意培养。饮誉世界的吴健雄博士在中央大学求学时,身材瘦小貌不惊人的她对理科有一股异乎常人的“钻劲”,为弄通一个学术问题,常常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在实验室里研究,陈剑修对她这种孜孜不倦的刻苦钻研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和鼓励,多次帮助她申请甲等奖学金。吴健雄成名后写信给陈剑修说道:“学生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恩师当年对我的关怀、培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天津相继失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机,高等教育也面临国破校亡、根基沦丧的空前灾难。1937年9月10日,国民政府教育部紧急颁布第16696号令:“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师资为基干,成立长沙临时大学;以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和北平研究院等院校为基干,设立西安临时大学。”由此,形成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最大的两个大学联合体。
1937年10月11日,教育部、北平研究院、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洋工学院、东北大学、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陕西省教育厅等代表组成西安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教育部部长王世杰担任主席,聘任陈剑修、徐诵明、李蒸、李书田、童冠贤等9人为委员,随后指定陈剑修、徐诵明、李蒸、李书田4人为校务常委,不设校长,由常委商决校务。
陈剑修临危受命,他和其他常委同舟共济,带领合并学校的师生一路向西,徒步近千里来到西安,完成联合大学的组建。1937年11月1日,西安临时大学开学,15日正式上课,设立文理、法商、教育、工、农、医6个学院24个系,全校学生共计2472人。在战况频发的艰难条件下,学校不但坚持正常授课,还特别设置与抗战有关的课外训练,如军事、政治、救护、技术等,每周邀请各界知名人士给学生演讲,介绍抗战形势,鼓舞学生斗志。
1938年3月,日军打到风陵渡,潼关告急,西安震动。敌机空袭频繁,西安居民外出逃难。此时,教育部命令西安临时大学迁往汉中,更名为国立西北联合大学(简称“西北联大”)。陈剑修等校务常委带领教职员包括眷属共300余人、学生千余人从西安坐火车到宝鸡,然后用20余天徒步250多公里安全到达汉中,实为中国教育史上可歌可泣的壮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