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与侯官文化
作者: 任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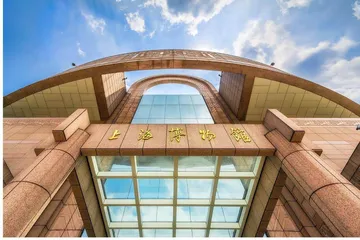
“侯官文化”是福建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在中国近代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作为“侯官文化”代表人物之一的严复是中国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和翻译家。他的八大译著,尤其是《天演论》,对中国近代社会思潮起到了巨大影响,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西学东渐”这股洪流中不可撼动的地位。他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题为“侯官严复学”,并在译著和文章署名时皆在名字前加上“侯官”二字,使得“侯官”这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县名从19世纪末起就成为文化的代名词。
2023年4月8日,福建省委宣传部部长张彦在《瞭望》杂志上发表论文《推动“闽派”特色文艺蓬勃发展》,这是“侯官文化”首次作为福建地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被提出来,并上升到福建省规划纲要的地位。
侯官文化
侯官原为汉代冶县之地,从东汉到晚清,在福建地域文化之中,形成了一个具有其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方特色的侯官文化。作为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历经宋明以来闽文化的发展变迁,在晚清福州地区中西文化碰撞交流中,形成了一支具有福建文化标识意义的地域文化。
“侯官文化”,指的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曾出现过一个奇异现象:地处东南之隅,远离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弹丸之地侯官,在极短的时间内崛起了包括林则徐、沈葆桢、严复、林纾、林觉民、萨镇冰这些特殊时空的人物群体。更为令人惊叹的是这些杰出人物门类齐全,有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文学家、外交家、思想家、翻译家,几乎囊括了各个领域。这么多著名人物集中出现在一个不大的区域,“晚清风流数侯官”,体现了所谓“地灵人杰”,或谓“天时、地利、人和”。正是这些风流人物,在各自的领域对中国近代史起到或大或小的推动作用。
早在19世纪末开始至20世纪上半叶,“侯官”虽然只是一个县域地名,却频繁出现在《申报》《新民丛报》等各大全国发行的报刊版面,且一度成为知识分子交谈和笔墨触及的“热词”。这一现象的出现同“侯官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严复及其译作《天演论》的流行密不可分。
求学之路
严复(1854—1921),福建侯官县人,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中医世家,从七岁起上私塾,从小便打下了坚实的文字功底。1866年,是严复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这年春天,14岁的严复成婚,6月,福州瘟疫,家中经济的顶梁柱父亲在救治病人时不幸染病过世。这彻底改变了严复的命运,中断了严复的科举之路。家道中落,全家不得不搬回城郊的阳崎老家。不要说继续读书,就是家中生计都要靠母亲和妻子做针线活来艰难维系。就在严复急于寻找出路、谋求摆脱困境时,恰好年末福州船政学堂开始招收第一届学生,不仅食宿、学费和医药费全免,而且每月还有四两银子补贴。巧的是,那年的考题是与父母孝道有关的“为大孝终身慕父母论”。刚经历了丧父之痛的严复,触题生情,挥笔成章。声情并茂的文章打动了也刚经历了丧母之痛的主考官沈葆桢,因此严复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
在晚清海军人才的摇篮——福州马尾船政学堂,严复上的是以英文教学为主的后学堂,并接受了几何、代数、光学、天文学、航海术等现代科学课程。因此,严复从14岁到18岁期间,不但接受了系统的英文教育,还接受了远远先进于同时代国人的基础科学教育,这两者都为严复日后的“严译名著”打下了坚实的语言基础和知识基础。
1877年,23岁的严复作为清政府派遣赴欧的第一批留学生,前往英国留学。他先是就读于普茨茅斯海军学院,后考入伦敦的格林威治海军学院(即现在的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1879年,26岁的严复回到母校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习。从此,教育成了他毕生的事业。
教育事业
严复作为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不仅提出了丰富的教育理论,而且在多所名校主持教育。1880年,他于马尾船政学堂任教一年后,经陈宝琛举荐,被召去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十年后,被提升为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第二年又被提升为总办(校长),并在此执教二十年。
除了北洋水师学堂,严复还先后担任过安庆高等师范学堂和上海复旦公学校长。1912年5月,他出任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他执掌北大之际,北大正处于艰苦创业的阶段。为创建、保全和发展北京大学,他经历了一生办学实践中最艰难的阶段,为此倾注了无数心血。无论是为筹措北大办学经费呕心沥血,或是两上“说帖”请求保留北大,拯救将遭停办厄运的新生学府:还是改良教学,提出“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的办学主张,使之成为后来北大办学思想的主流和传统。严复为北大,为这所中国最高学府,为艰难前行的中国现代教育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家李志伟在《北大百年(1898-1998)》一书中称赞严复为“第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北大校长”,感叹严复留下了一个“具备了一流精神底蕴和办学思路的北大”。在一百多年前的民国元年,在一个动荡不安、官僚军阀们都忙着争权夺利的社会大环境下,竟还有这样一个头脑在思考着中国高等教育制度的未来,这不仅是北大之幸事,中国现代教育之幸事,更是中国之幸事!
翻译事业
从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的十余年间,是严复一生中精力最旺盛、学问造诣最深厚、思想认识最成熟的时期。他主要致力于翻译西方十八、十九世纪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逻辑学、哲学、法学等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向中国知识分子系统介绍了“西学”的精华。他的译作,不仅使当时的中国人耳目为之一新;而且为中国学术的更新,为中国近代社会科学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
严复于西学的接触始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发展于英伦留学期间,真正让他从教育事业跨界到翻译事业的导火索是1894年的中国甲午海战的惨败。他为了唤醒国人、救亡图存,开始选择用笔和文字作为战斗工具。甲午战争前,人们普遍关注西方的“坚固的船只和猛烈的大炮”,而洋务运动也主要是学习西方精巧的机器,以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严复批评这些肤浅的认识,认为学习“技艺器物”等有形文化只是学习西方的皮毛;主张更需要学习的是西方的思想、观念等无形文化。为了让中国知识分子全面、系统地认识西学的精髓,他从1896年到1905年的十年间,慧眼独具地选择翻译了一批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原著,后来史称八部“严译名著”。这八部“严译名著”,详见表1。
八部“严译名著”中最重要、影响力最大最深远的当属1896年翻译出版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严复成为第一个将达尔文进化论全面系统介绍到中国来的学者。在《天演论》自序中,严复明确表示,他翻译此书的目的,是因为此书的主题是阐述“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可以号召国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要发愤图强,急起直追,而不应坐以待毙。这不但与严复“维新图治、救亡保种”的思想非常合拍,而且与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想主流是十分吻合的。严复在翻译此书时,并非字字直译,全盘照搬,而是在翻译过程中,加了大量按语、解释或评价,在阐述自己的社会政治见解的同时,引导读者的思路。他甚至在文本翻译中,也根据自己的思想观点对原文进行了改造和发挥。
这部译作不但使他成为“向中国介绍西方先进思想的第一人”,而且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词成为人们的口头禅。时至今日,哪怕这本译作面世已百余年,现代人一提起严复,除了《天演论》,下一个脱口而出的关键词必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该书190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到1921年就印行了20版。该书对社会影响之广,由此可见一斑。正是因为严复翻译《天演论》,康有为称赞他是“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称赞他为“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鲁迅热情地称道他“是一个19世纪末年中国感觉敏锐的人”,胡适称赞“严复是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综观严复的译著,涉及政治学、经济学、哲学,逻辑学、法学等众多学科,形成了相对完整的西学体系。具体而言,《天演论》为近代中国敲响了亡国灭种的警钟,为救亡运动作了总动员,并且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通诠》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由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军国社会阶段的完整社会进化过程;《原富》为中国人民自强求富贡献了“自由平通”的方略;《群学肄言》则强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对国家政治的指导作用;《穆勒名学》与《名学浅说》介绍了近代西方格物穷理的治学方法;《法意》宣传自由民权学说、三权分立学说及君主立宪的好处。严复以一己之力,率先独立翻译出横跨如此众多学科的西学名著,在中国近代史上绝无仅有。
更为重要的是,严复的译著在介绍西方学术思想时,不是一味吹捧、盲从或是全盘接受。而是结合中国国情,或借用原著阐发自己的观点,或介绍对中国人可资利用的新思想、新方法、新知识,或对原著加以评析。严复在每本译作中都针对性地加上按语和序言,鲜明地阐述自己的观点。他不是以西学排斥中学,而是融中学和西学为一体,既传播了西学,又能切中时弊。他的翻译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移植过程,而是一个文化再创造的过程,因而产生了较强的社会效果,因此每次译书出版之际,便得到社会各界读书之人的争相购买,产生了深远的社会影响。
严复对中国近现代的影响除了“严译名著”外,他还在自己的翻译实践中结合翻译的心得体会,首次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并指出这三个标准是翻译中最难达到的三件事。严复所说的“信”就是尽可能地忠于原文,使译文意义不违背原文;“达”就是在“信”的基础上准确充分地表达出原文的内涵,当“信”和“达”发生冲突时,“信”是第一位的。严复主张,为了做到“达”,在具体翻译过程中不能硬译死译,只要能准确表达出原文意旨,不必斤斤计较文字和句次。严复提出的“雅”,本意是强调译文必须正确规范,符合正道与正统。所以“雅”泛指译文的文字水平,而非单纯指译文的文学价值,也不是要求译文要一味追求所谓的“高雅”。近代中国首次提出将“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并论述三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使之成为一种较为完整的理论,则始自严复。“信、达、雅”是中国近代翻译理论的起点,在中国翻译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我国翻译理论中至今仍占据主流地位。
侯官严复学
严复和侯官文化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严复曾将自己的学术思想题为“侯官严复学”,而当代学者汪征鲁教授则称之为“侯官新学”,并认为“侯官新学”的内涵主要表现在:以社会进化论为核心的世界观与方法论。社会历史观与以“三民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为核心的救国方略。“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价值取向。严复学术思想的最大特色还在于,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思维、以儒家传统中的基本价值理念为基点来介绍和宣传西方的价值观,努力寻求中西思想的一致性。因此,严复的“侯官新学”无疑是侯官文化的核心。“严译名著”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产物,严复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吸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及对构建中国近代新型的文化体系的不懈努力,堪称“侯官文化”最具代表性人物。
另一方面,纵观当时各个版本的《天演论》,严复的署名都冠以“侯官严复”。在《天演论》成名之后,严复经常在当时流传甚广的报纸,诸如《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撰文发表政见,皆署名“侯官严复”。《天演论》发表之后,严复陆续翻译的其他西方名著都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当时影响力较大的报刊——《新民丛报》《东方杂志》《教育杂志》《鹭江报》等,都以“侯官严复”译或译著为名进行了宣传报道。这样一来,“侯官”也就和“天演”一样成为严复的标签。
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因《天演论》获得了一大批粉丝,他们也都喜欢用侯官严复来称呼他。比如他重量级的粉丝之一梁启超就常以“严君”“侯官严复几道”等称呼严复。而当时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如蔡元培、钱穆、鲁迅等盛赞《天演论》时都冠以“侯官严复”的标签。“侯官”本仅为一县名,跟随着当时社会的“严复热”和严复粉丝的二次传播再度成为当时中国报刊及文人争相传播的“热词”。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教授认为,“侯官文化”虽然是地域文化,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中华优秀文化在华夏大地开枝散叶结出的果实。“侯官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受人敬仰的文化现象,最重要的不在于孕育了一批历史名人,而在于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体现了中华文化精髓。其中最鲜明的一点就是将个人之小我同国家、民族之大我统一起来,时时处处以国家为大、以民族为重。
中央党校许耀桐教授认为,以林则徐、严复为代表的侯官先贤爱国主义精神中,蕴涵有崇高的理念宗旨,涵盖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层面。“侯官文化作为地域性文化,能够如此集中、全方位地体现出爱国主义的伟大精神,这是非常独特和难能可贵的现象”。“严复八大译著”蕴藏着同一个指向:如何让中国人凝聚并团结起来。
概言之,侯官文化具有爱国自强、开放包容、敦厚务实的精神特质,在中国近代史乃至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因此,侯官文化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福建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