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仕女纹样的研究
作者: 李晶津 王志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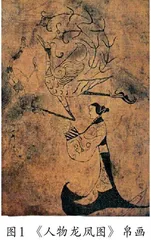
对仕女画的历史进行梳理,选取仕女图中变化明显的面部特征展开分析,并比较现代女性的审美风格;通过列举现代活化仕女纹的案例,总结出将传统仕女纹应用到现代设计中的方法;此外,结合当下时政、社会背景,从不同维度分析将传统纹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要求,引发读者对时下热点词汇的审美思考。
在古代,官宦人家的女子是“仕女”一词的指代,也作“士女”。仕女画一般指以封建社会中上层妇女为题材的国画[1]。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概念越来越广义,凡是表现以女性为主的美人画都可以称之为“仕女画”。仕女画作为中国传统人物画中的一个分支,迄今发现最早的实体仕女画,可以追溯到战国的《人物龙凤帛画》,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2]。前人将中国仕女画的风格概括为一种平缓柔顺的整体静态之美。我们不难发现,仕女图中的女子大多笑不露齿,仪态往往没有一丝动态感,这和汉代的儒学、宋明理学下的封建礼制思想息息相关。现将对仕女画的历史进行梳理,并对其展开分析,从不同的维度上提出将传统纹样运用到现代设计中的应用要求。
不同时代仕女纹体现的特征
仕女画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两汉时期,这个时期在许多绘画当中出现了女性的形象,可以说是仕女画的萌芽时期。我国现存最早的仕女画实物是战国时期的《人物龙凤帛画》(如图1),同时期还有《人物御龙图》,这两幅帛画虽然在技法上都比较稚拙,但其单线墨笔勾勒的画法为后世的绘画形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秦汉时期,绘画中的女性形象逐渐丰富,出现了仕女、农妇、歌舞伎等形象;应用场景也很丰富,例如在墓室壁画、画像石、画像砖中都有所应用;画面场景丰富,出现了宴会、杂技表演等场景。到了六朝时,前人在人物画的画法和技巧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一阶段可以称之为成熟期。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形容此时的仕女画是“历观古名士画……有妇人形相者,貌虽端严,神必清古,自有威重俨然之色”[3],由此可见此时的仕女形象典雅端庄,当时的绘画技法已经能够成功地表现出人物的情感和气质。
到了隋唐五代时期,仕女画已经历经了近千年的沉淀,此时仕女画的绘画技艺有了新的突破。具有代表性的画作有周昉的《簪花仕女图》、张萱的《捣练图》等,其中唐代的仕女以雍容华贵为特点,面部丰腴、柳眉星眼、直鼻小嘴、披帛绕胸,神情泰然自得,色彩浓艳雄厚,整体画面十分生动。五代时期的仕女画是一个转折点,此时的风格有些保留了唐代浓丽丰肥的形象,而有些人物身材则变得更加修长,衣着的线条纹样也更加简洁,与唐朝的风格有着明显的差异,比如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如图2),显然已经接近宋代仕女修长秀美的风格。
唐五代之后一直到两宋时期,仕女画比前几代更加丰富,不再局限于对封建社会上层贵族女性的描绘,也出现了表现社会中下层女性真实生活的画作,画师们把题材扩大至平民妇女,突破了贵族范围“仕”的羁绊[4]。仕女形象由丰腴变为修长,整体风格由华丽奢靡变为清秀文雅。元代以后,文人画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仕女画,这个时期可称之为徘徊期。
明代开始,由于社会文化艺术发展的繁荣,画家在审美取向上多以商人和市民阶层的需求为主,以仇英、唐寅等人为代表的明代画家创造了“世俗美”的仕女形象[5]。代表作品有唐寅的《秋风纨扇图》、仇英的《修竹仕女图》和陈洪绶的《女仙图》等[6]。然而,明中期以后,仕女形象过于千篇一律,弱不胜衣,了无生气。清代仕女画从故事、诗词、民间传奇、戏曲小说等题材中取材,仕女造型蕴藉委婉,多是尖脸、削肩、柳腰、莲步的病态形象[7]。彼时,中国封建社会即将走向没落和衰亡,仕女“病态美”的形象也是画家对时代不满的写照,例如费丹旭的《金陵十二钗》、改琦的《红楼梦图咏》等。同时将这种孱弱的特征不断强化,暗示了当时女性极低的社会地位和不自主性。
不同时代下,仕女纹样中表现出的审美特征也在不断发展和变化,通常与当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对文化艺术作品的解读,也是对社会历史发展的透析,比如唐代的富饶表现在仕女丰腴奢华,清朝的社会风气糜烂表现为女性的病态之美,这些不同的时代背景造就了不同的纹样表达方式和造型特点。
从汉代的儒家思想再到宋明理学,封建礼教思想对女性的种种禁锢和束缚导致当时的女子不能抛头露面。纵观仕女图纹,在一幅幅优美的画面中,女子很少有手舞足蹈、眉开眼笑的动感表情,往往只是在花园或庭院中赏花、吟诗、作画、教子。仕女图中的仕女多笑不露齿、行无大步,体态和神情几乎没有什么动感和节奏感[8]。笔者将重点从变化较多的容貌特征着手,探讨传统视域下对女性审美趋向的变化,将其和现代女性审美作比较。
传统视域下仕女纹容貌审美变革的规律
脸型指面部的轮廓,也代表了一个人的容貌,其中“容”指仪容、仪表,是人的神韵和气质所在,“貌”指外貌,也就是指五官大形,如瓜子脸、柳眉、杏眼、樱桃小嘴、粉面朱唇等可视的外表[9]。中国古代仕女的面部妆容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秦汉女子流行画广眉,面部妆容以浓艳为美,面部已经开始用铅粉涂面[10],并且当时的绘画以神仙形象为主,因此发型主要以飞天髻为主。
唐代民风自由开放,女子妆容多姿多彩,就以眉形为例,从唐玄宗命画工绘制的《十眉图》可见一斑,当时流行的眉形有鸳鸯眉、八字眉、远山眉、三峰眉、垂珠眉、月棱眉、分梢眉等,在盛唐时期光唇式就出现了17种。并且彼时出现了贴花钿、描斜红的女子妆容,影响了今天许多影视作品的妆容创作。据《中华古今注》载:“长安妇人好为盘桓髻,到于今其法不绝。”由此可见,这种盘桓髻在长安风靡一时[11]。
宋代时期女子以高髻为尚,有代表性的为朝天髻。仕女妆容也与唐朝有着很明显的区别,女子摒弃了浓妆,偏爱淡抹[12]。
明朝开始,女子以细眉为美,发髻以低为主,很少梳高髻,女子妆容上也非常有特点,通常采用“三白法”——即在额、鼻和下颚三个部分晕上夸张的白粉,表现面部层次。
清代仕女画的层次更多,大体上可以分两部分来研究,一部分为康乾盛世时期,另一部分为清末晚期。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跨越百年,反映到艺术当中,其变化更是显而易见。以彩瓷仕女为例,康熙时期的仕女高髻素衣,细眼弯眉,脸呈杏核形;雍正时期仕女脸施薄粉,吊眉细眼,脸呈鹅蛋形;乾隆时期仕女松髻华衣,额宽颊窄,五官紧凑[13]。仕女妆容素雅,往往上唇不涂唇妆,只在下唇内侧略施唇脂,有点类似今天流行的“咬唇妆”。在发式方面,满族女子多梳“两把头”,到了清末,这种发式越来越高,渐渐变成了“大拉翅”,与此同时还兴起另一种“后垂髻”与“盘髻”的发式。
将以上变化精简地概括为图3,使读者可以更好地掌握仕女纹容貌。
现代视域下仕女纹“活化”的应用
“活化”这个词语原本是化学和物理范畴内的专用词语,但现代视域下“活化”被赋予了新的语境,即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供新的用途,使其获得了新的生命,服务于当今的经济和文化发展。
现代女性审美风格
近年来,女性的审美风格产生了极大的变化。如仕女纹样作为当时应用广泛的形式,就其形象而言,《诗经》中就有对其的描述,“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如今,随着偶像文化的引入,“白、幼、瘦”成为如今大火的审美标准之一。而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审美逐渐走向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提出女性美不应该再被传统局限,不应该再被定义。正如艺术家Hanna Lee Joshi用鲜艳的渐变色调,表现真正的女性之美是不受限制,她们突破了现有社会对女人的局限,其作品优美而富有象征意义。
仕女纹活化的运用
2021年河南省春晚节目《唐宫夜宴》的播出,在网络中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热度持续不下。其中穿插了水墨画、贾湖骨笛、簪花仕女图等环节,不仅体现了艺术创作的价值,还体现了非遗文化唐代仕女图的“活化”运用,有助于提高国人的文化自信,有助于文化传播。
仕女纹活化的方式
对非遗文化的活化,我们首先要充分了解民族文化,了解我国历史的发展,以文化的内核作为传播的基础;同时要深入了解人们的内心,激发民族认同感。其次,现代信息技术已经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将现代技术与文化充分结合,使文化的内核更广泛地传播。例如,虚拟现实技术、微信表情包的运用、交互设计等。最后,活化离不开经济、政策的支持,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运用多元化的活化方式,说好中国故事,推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现当代对于仕女纹的总结及反思
当今时代的背景
面对当前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创新,继承传统文化,提升文化自信,是我们国家提升软实力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也需要深厚的历史底蕴与传统传承。很多传统元素被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而其“活化”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体现,也为世界人们多角度、多方位地了解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实际而有效的平台。
如何避免活化争议
出于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尊重,要合理运用活化手段。首先,在创作前要充分了解不同时代的物质文化,根据文化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如在设计前我们要考虑四个方面:区域、民族、国家、时代以及它们之间的不同,同时还要考虑到文化的排他性。其次,在创作中充分尊重受众才会赢得市场,要考虑作品的普适性和大众性。最后,在创作后针对同时期不同的社会形态和文化产品要具备不同的适应性,例如在欧洲文化当中,欧洲女性用中国的仕女纹饰表现当时的审美状态。而在中国,其本身就符合历史和国人的审美状态,实现了社会文化体系的适应性发展。
综上所述,历史文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中国价值的核心。通过对传统仕女纹样的了解研究,提出了非遗文化的“活化”传播,需要将中国的传统艺术与现代技术进行结合并继承发展,同时注意避免活化争议,实现必要的社会适应性发展,传达出中国哲学“和而不同”的中和之美、以人为本的人性化之美、自然和谐之美以及对于整体意境的重视与把控。
建立由内而外的文化自信,在有文化自觉的前提下,我们也不应该对一些艺术创作过于敏感,过度的敏感反而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比如稍有异动就去批判和否定。我们不仅要重视发扬传统文化,更要警惕借“传统”话题扰乱国内舆论的行为,避免在没有充分了解传统文化和设计动机的前提下展开争论,从而陷入话语的陷阱。我们要做到尊重审美的多元化,提倡文化自信,不断发扬和传承非遗文化,因此,我们还有很长的文化发展之路要走。
参考文献
[1]夏征农,陈至立.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2]杨冬,徐泽.从明清文人仕女画看“才子”的“佳人”梦[J].台州学院学报,2005(02):17-19+27.
[3][6][7][9][11][12]徐丽慧.中国传统仕女艺术[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4.
[4]吕建昌.含蓄逸雅和浮华媚艳——中国仕女画与日本美人画散论[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01):53-59.
[5]沈辉凌.浅析釉上彩仕女图的艺术特色[J].景德镇陶瓷,2014(01):92-93.
[8]张小萍.从陶瓷仕女图纹看古代女性文化[J].中国陶瓷,2006(02):64-65+68.
[10]贾瑶.从古代女性面部妆容看中西方审美文化的差异[J].青年文学家,2020(06):170-171.
[13]马未都.马未都谈瓷之纹 天时人事日相催——人物纹(下)[J].紫禁城,2012(06):66-91.
【作者简介】李晶津(1996—),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艺术设计、视觉传达。
【通讯作者】王志强(1970—),男,硕士,教授,研究方向:艺术设计与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