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美科技界加速主义新思潮
1美科技界加速主义新思潮
丁明磊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瞭望》2025年第7期
近几年,有效加速主义在硅谷精英中快速兴起,认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应该设法加速技术奇点的到来。技术加速主义是加速主义的一个分支,认为技术进步是推动社会变革的核心动力,主张加速技术发展来推动社会变革,认为唯有主动加速技术(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进步,才能突破现有社会结构的局限,甚至可能通过技术引发的系统性崩溃或重构,催生更理想的社会形态。技术加速主义相信随着技术的加速发展,可以自动解决当前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任何试图阻碍技术发展的障碍必须全部取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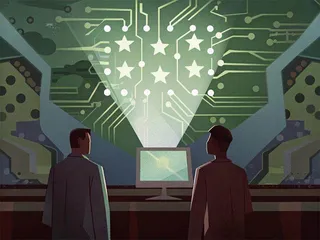
技术加速主义在推动技术创新加速、经济增长提速、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同时,其缺陷和消极影响也不容忽视。一是技术加速主义放大了技术发展带来的正面效应,忽视了其负面效应,试图通过加速技术发展来改变社会历史发展方向,有将社会历史发展置于唯心主义的风险,而且暗含了精英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内容。二是技术加速主义以对技术的关注取代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性批判。其强调对控制论、平台、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把握,忽视了背后更为关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统治性地位。三是按照西方科技精英的观念,未来的技术奇点很可能会由少数科技资本家和工程师掌控,其基本逻辑是精英主义或是超人主义,参与这种游戏的是少数精英,而不是广泛的社会大众。正因此,美国才产生了不惜代价独占技术奇点及其生产力爆发的幻想,并掀起对华脱钩断链、“小院高墙”式的科技打压与封锁。四是一些批评者也认为,加速主义太过于决定论,甚至陷入乌托邦式的空想,其承诺的美好未来生活也许并不会如期到来,人类社会在技术加速下有可能变得更糟,弱势群体反而会受到技术加速的伤害。
事实是,当美国愈加投入“小院高墙”的俱乐部体制怀抱,其便丧失了与外界进行大量信息交流和资源交换的机会,反而加速了全球技术的多极化分布和技术力量的重新洗牌,招致全球技术生态的“去美国化”反噬,最终只会加速其自身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孤立。历史已经反复证明,技术封锁总是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的规律,尤其是在全球产业链不断深度融合的今天,美国无法有效控制全球技术的流动,正如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所言:“全球化不是可逆的,每一个封锁的行为都会激发出技术新生力量。”
2“虎扑”平台城市男性生育话题中的“钱与能力”
申琦 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教授
本文节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1期

在生育相关话题的探讨中,城市男性对彩礼问题表现出极高的关注度,尤其在谈及彩礼与生育补偿时,负面情绪常常溢于言表。这一现象深刻反映出,他们在考量生育问题时深入权衡经济因素,其核心在于围绕“钱”这一关键元素,谨慎处理“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微妙平衡。对于城市男性而言,在购房、育儿等重大经济事项上,来自大家庭的隔代帮扶是小家庭有效抵御风险、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保障。他们既不希望因为组建小家庭而过度透支大家庭的资源与活力,又不愿因过度依仗大家庭的帮扶而削弱小家庭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事实上,城市男性在组建小家庭后,与原生大家庭在经济、情感、育儿及日常生活等多个维度仍保持紧密的联系,呈现出鲜明的双向互动特征。因此,若彩礼等经济问题处理不当,易引发家庭内部矛盾,破坏大家庭与小家庭之间的情感纽带;而处理得当,则能够强化代际互助与支持。
“虎扑”平台上城市男性深陷生育年龄焦虑的漩涡,其背后潜藏着当代青年新型生活方式与传统优生优育观之间的激烈碰撞。社会建构论指出,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与感知是社会建构的结果。在传统的家庭与社会价值体系中,早生早育往往因能为家族注入新鲜血液、促进代际传承而被赋予诸多积极意义,并在近代的科普宣导中不断得到强化。在公众的潜意识里,女性生育年龄与生育质量紧密关联,35 岁以后生育的女性往往被界定为高龄产妇。这种观念在文化传承中逐渐演变成一种潜在的社会心理共识,致使男性在面临生育决策时,不自觉地将早生和优生画上等号,形成一种思维定势。事实上,生育质量是一个复杂概念,心理因素、生活环境、孕期保健等在生育结果中所起的作用与生理年龄同等重要,甚至更为关键。相比生理条件,心理与物质层面的充分准备,能让夫妻双方在面对生育过程中的各种挑战与压力时更有底气,情绪也更加稳定。同时,生育年龄的宣传引导必须考虑当前时代的特点。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引发了生活方式和家庭结构的全面变革,晚婚晚育成为许多青年在现实压力下的无奈选择。传统的“早生等于优生”观念,已不符合当下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
3进城还是留守
贺雪峰 武汉大学教授
本文节选自公众号《新乡土》
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体制性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出现了越来越多务工经商的获利机会,农村男性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经商,而老人、妇女和儿童留守农村,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三留守”问题。留守会产生各种问题,缓解并解决留守人员问题应成为“三农”政策的重要目标。
不过,特定历史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留守人员问题,解决起来也要考虑历史社会条件。当前留守人员问题的成因,源自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寻找获利机会,这些青壮年劳动力无力携全家老少到城市居住,有两个原因:一是城市生活成本远高于农村,二是中老年父母进城,家庭会丧失农业收入。全家进城,农民家庭收入减少,支出大幅度增加,生活会更加贫困。这是当前中国绝大多数农民家庭没有全家进城,而是青壮年劳动力进城、中老年父母和年幼儿童留村的原因。留守是农民家庭应对城市有限收入机会的主动选择。城市收入有限的原因又是由中国当前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决定的。与中国同处发展中国家的大国,举家进城的农民家庭很少可以在城市体面安居,结果很快就落入城市贫民窟。中国农民进城而不愿落入贫民窟,他们因而保留了在农村获得农业收入及在农村生活的机会。农民是在落入城市贫民窟与留守农村之间做出选择,相对来说,留守是次优选择。或者说,留守以及从农业中获取收入是农民的权利。
中国当前发展阶段决定了留守人员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留守其实也是农民的选择与权利。若农民进城失败,或中老年父母不愿与年轻子女住在局促的城市空间,他们还可以退回农村,留守成为了弱势农民的基本保障与社会保险,是他们可以获得的底线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