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药片与它倡导的生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陈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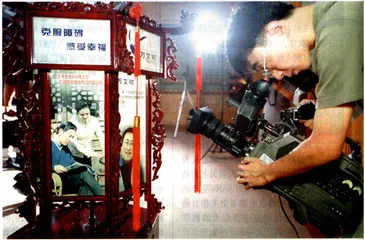
“伟哥”已成为成人保健品商店的金字招牌(马罗 摄)
一片给老人的药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
7月3日,正版“伟哥”进入中国。辉瑞公司在北京、上海和广州三地同时举办新闻发布会,新闻记者没有看到意想中成盒成盒的“伟哥”派发,只不过得到了一个内镶一粒“伟哥”的水晶座。“这是不是真正的伟哥?”窃窃私语的记者们,对这个蓝色菱形颗粒的兴趣当然超过他们手中的新闻稿和采访提纲。
尽管此前久闻大名的“伟哥”已经从各种渠道流入了内地,但已经更名为“万艾可”的这种药片第一天在国内正式上市还是异常惹眼,北京市医药公司当天仅向北大医院和同仁医院两家就发售了400盒。而在此前不久,国内多家保健品商纷纷祭起法宝,大把免费送出各类号称“功效超过或等于美国伟哥”的“土伟哥”,成都、南宁、南京等地数以千计的男女老少顶风冒雨声势浩大地排队领取。
“伟哥”在中国的声势还算不上浩大。在美国,1998年3月27日“伟哥”通过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的批准,第一周,每天即开出1.5万张处方,第二周2.5万张/天,到第七周,达到27万张/天,创下了全球药物史的纪录。“伟哥”第一年全世界的销售额即达到10亿美元。从1998年3月“伟哥”正式上市到2000年4月的时间里,世界上有800万人接受了“伟哥”的治疗,用药2.5亿粒,平均每一秒钟就有4粒售出。
在观念相对自由和开放的欧美社会,“伟哥”引起的反响状况就好像是历史的再现——像“伟哥”这样,作为一种药而受到如此关注,上一次是在40年前——1960年口服避孕药通过美国“联邦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的鉴定。这种药片“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消除了人们对怀孕的恐惧,使人们能够放松地去追求性爱的乐趣。”记者、作家阿斯贝尔在他的《The Pill》一书中这样写道。
现在“伟哥”又来了。《时代周刊》说:“世界等待这种药已经4000年了!”“伟哥”(VIAGRA)的意思是“精力旺盛如澎湃的瀑布”。在中国,人们还是更愿意把辉瑞公司注册的“万艾可”叫作“伟哥”——这可能是近年来香港翻译的西文里最漂亮、地道的一个,让人觉得有那么一点亲切和权威感:做个威猛男人,这回真的简单了。
“你真的需要它”或“你真的不需要它”?
“我用得着用‘伟哥’么?”北京一位不愿暴露姓名的IT业公司副总经理自信地反问,“网络这行儿压力是不小,我闯荡了3年,可回家还是个男人嘛!”这样的回答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男性受访者的态度。但有意思的是,在对这位副总的妻子的采访中,却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有留学背景,这位妻子谈及性的问题时落落大方:“和现在相比,我认为‘伟哥’会重新带给我和我的家庭快乐。当然我理解我丈夫,现在社会给男人的压力越来越大,男人之间互相比较的东西也越来‘物化’:房子大小、汽车牌子、职务高低……也只有性还能算是纯个人的,但好像也得证明一番吧。其实‘伟哥’可以成为男人的一种希望,只要你抛开一些面子问题。”
“你真的需要它?”或者“你真的不需要它?”不管你的女伴问你上面的哪一个问题,结果都会让你发窘;如果是后一个,可能会更糟。男人可以忍受妻子、恋人的唠叨,但很难接受对方质疑自己的性能力。最近见到的一个承认自己性功能不佳的例子是在网上,关于“伟哥”的热闹讨论中,一家BBS上有一张帖子这样说:“这回麻烦了:以前我出差,遇见问‘要不要小姐?’我就说‘我阳痿’,省了不少事儿;现在我再这么说,他们就会问:‘先生要不要伟哥?’”
这不过是调侃。从北京、沈阳、杭州、成都、广州等大城市的“伟哥”上市情况看,南方的反响似乎更“热烈”一些。购买“伟哥”的男性表现不一。在以“补”出名的广州,第一位得到“伟哥”处方的男士对记者解释说.自己其实没有功能障碍,就是喜欢试不同的壮阳药。药到手后,他把药盒、说明书全扔了,只留下蓝色的药片揣进兜里,接着对药房里面嘱咐,以后给病人拿这个药,不要把药名说得那么大声,“别人听到了会不好意思的”。
“你不好意思问我会不会吃‘伟哥’吧?我当然可以告诉你,如果我真的需要它,为什么不呢?”供职于一家瑞典公司的驻京代表安德森告诉记者,在瑞典,患者可以根据自已的意愿到医院领取‘伟哥’,他用北欧人特有的直率和认真说:“也许中国的历史太伟大,让人太沉重了。生活的本身是快乐的,我们为什么不把它看得很轻松呢?既然‘伟哥’是科学的,健康的,我看不出有理由要反对它。”
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我们听到了另一种声音。尽管对中国男人来讲,承认自已性方面的小足仍然可能比承认无知更需要勇气。但毕竟,在性和面子的选择中,一粒蓝色的药片终于可以把问题解决了。
虽然医生们一再强调“伟哥”是针对男性勃起功能障碍症状的治疗药,而不是春药,然而不少人还是相信“伟哥”能够助他们大显身手。在一些成人保健品商店,店主也纷纷把“伟哥”作为金字招牌,只不过,这“伟哥”不是那“伟哥”,大多是国内厂商冠以“××伟哥”的性保健品。有人称随着“伟哥”登陆中国,中国保健品也进入了“壮阳时代”
“这当然是企业和媒体的炒作,但也可以看出人们对于性的观念的变化”,北京社会科学研究院的俞长江教授在评论国内各大城市的“伟哥现象”时说,长期压抑的心理一旦释放,它的能量会超出常规的想象,“这肯定是一个会不断引起关注的事情。不论美国的“伟哥”、法国的虎哥,还是国产的形形色色的‘哥’,究竟是所罗门的瓶子,还是技术对人们生活观念的又一次革命,我们还得等待。”
“其实‘伟哥’就是一种药,一种目前世界上可能最有疗效但并不是最完美的药,它会帮助我们获得快乐和健康的机会,但它不是快乐和健康本身,就像它也不是道德本身一样。”北京一位在某大公司工作,同样不愿透露姓名的30岁的女性则认为,既然和谐的性生活可以让婚姻更加完美,如果“伟哥”真的可以让这种和谐成为可能,“男人为什么不理直气壮地选择它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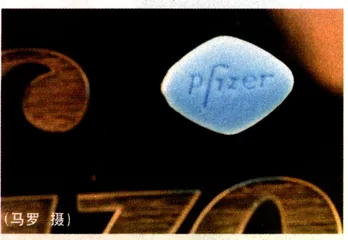
(马罗 摄)
40年前的药片和它倡导的生活
美国“计划生育委员会”主席戴丽丝·科斯依这样描述口服避孕药发明40 年来亲眼目睹的变化,50年代她在伦敦一家生育控制组织担任秘书。
“这种药片带来了一场革命。似乎是在一夜之间,女人们也能谈论她们所喜好的性生活方式了,女人的生活和生命都已发生了变革。或者在女权主义者们看来,正是这种药使男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得到女人,‘只要他愿意’。
“其实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恰恰没想到的是,避孕药使女人能够爱其所爱,自由选择,她们永远可以说不。”
1965年,芝加哥市一位20多岁的年轻母亲告诉《星期六邮报》的撰稿者,说:“我服用避孕药以后稍稍长胖了点。不过,我想可能使我在精神上更加放松了。以前我总担心会再怀上一个孩子,这让我变得越来越瘦,而现在我不必担心了……我想等到这个孩子两岁多的时候再要第二个。我可以等到那个时候的。”
1990年6月,《妇女生活》杂志为了纪念避孕药问世30周年,发表了一则宣言说:“避孕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鼓励了性开放和试婚,它使得妇女们歼始认真考虑事业问题,因为她们可以推迟生儿育女……”
男人最喜欢女人说“我要”,最怕女人说“我还要”
“性能力=强壮”的意识氛围和现代人的焦虑加在一起,使得男人更加看重也更加担心自已的性能力,有一个时候关于“美女作家”和她们的书引起好大一片争议,其中一个声音就典型地体现了这个担心:“我同古往今来的男人一样并不在意把男性设定为性狂欢的主角,但我们内心有一个绝对的恐惧,就是害怕女性对自已的性器官的觉醒。因为女性的性能力是无限的,而男人则有限。”
“伟哥”真有效果也好,仅仅是暗示也好,男人对自已身体的怀疑和恐慌确实存在,这种恐慌甚至可以超过对死亡的顾虑。在泰国,香烟盒子上的警告是“吸烟导致阳痿”,可能这要比“致癌”、“致命”更有劝戒的说服力。面对这种怀疑和恐慌,李宗盛也只好自嘲着絮絮叨叨地唱着:“餐厅的灯光有些昏暗,我遍寻不着那蓝色的小药丸”也许正是这种怀疑、恐慌、自嘲的存在,“伟哥”才会如此风光。
英国研究人员指出,男人25岁之后,男性荷尔蒙即开始发生大变化,睾丸激素逐步减少50%,随之出现的现象包括出汗、抑郁、神经紧张、疲劳、体内脂肪增加以及总体上能量的损失。“20岁时你每天可以跑10公里,一口气能做30个俯卧撑;到了30岁,身体功能超越了顶峰,对耐力非常重要的摄氧量逐渐下降,身体的关节开始发出咔咔的响声;等过了40岁,肌肉的可锻炼性已下降25%,体力下降,肌肉逐年萎缩,身体开始发福。”对一天天在“老化”的路上往前走的男人来说,中国先生网上这样的描述简直是一场灾难。
男人的力量需要鼓动,比如不停地运动。自“伟哥”出现后,许多已婚男人表示,他们虽不需要“伟哥”,却开始格外注意起自已的身体和健康。32岁的M保持着每天游泳一小时、健身一小时的习惯,而他的几位同龄同事差不多也每天安排类似跑步、游泳、打网球这样的一小时运动。他们几乎共同认为,运动的目的是“感到自己已经老了”。M说这个年龄的人已开始有了一种“无法克服的对青春的迷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