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梦想和合奏
作者:王珲
冲突
这个家,潜藏着一场巨大的风暴。
6月7日,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的全校大会上,本年度第一学期18名甲等奖学金获得者中,王天阳以专业、文化考试第一的成绩位列初一年级学生之首。这份高达4000元的奖金,足以抵消王天阳一学期的学费。
妈妈的兴奋与喜悦只是听到此消息时的短暂笑容,眼看第二个学年临近,她一直试图说服儿子退学,转入自己任教的101中学读初二。
“再不转,文化课就跟不上了,王天阳以前的数学优势也就没了。”刘旭说。
1998年到1999年6月之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刘旭都在为面临小学毕业的儿子上什么学的问题与丈夫争论不休。王骐一意孤行、快刀斩乱麻地安排了儿子的道路,王天阳果然以钢琴、视唱练耳、作曲、文化四项第一的成绩无可争议地考入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作曲系。
但夫妻间的争吵仍在继续。发展到2000年的6月,已是转不转学的论战,而问题的实质,直指以音乐为生有没有前途?
在做音乐教研员的王骐看来,儿子迈进附中的门槛,是父子俩的殊荣。他常教诲儿子,“全中国就这么一个音乐学院附中,这个专业培养的人才就二三个,我们一层层考试跟着看着,担惊受怕、心惊肉跳得来的非常珍贵的机会,怎么可能就把它丢掉?你已经提前进入专业了,这就等于进入了科学少年班一样,不能把自己等同于普通的中学生!”
刘旭希望儿子走一条普通人的道路,“他行。以我们家孩子的素质,他上普通的中学将来也能特别优秀。”但对儿子的音乐生涯,她就远没有这份乐观,“当音乐家,不是什么人都行。音乐学院培养了那么多学生,还不是一多半都转行了。搞音乐不是说刻苦就行,除了技巧,还得有灵气,有创造力。再说,如果是音乐世家,孩子从小的氛围就不一样。我们是平民。他的压力太大了……”
普通人的理想
刘旭不认为儿子学音乐特有天赋。王天阳因为手小,考音乐学院附小被教授们以弹钢琴没有前途拒收的挫折还历历在目。刘旭还记得,作为最小参赛选手,5岁的王天阳在北京市星海杯钢琴大赛上的紧张——他坐在椅子上,双拳紧握,头仰向天,眉眼紧皱,她心疼地哭着叫儿子不要参赛。
刘旭甚至觉得,儿子走上这条道路是生生让丈夫给逼出来的,这不是他的本意,“在这条路上,王天阳付出太多了。为了学音乐,父子俩老起冲突,他忍受不了时,王骐就急。我记得特别清楚,学视唱练耳,他爸让他听《白毛女》,只放一遍就让他唱,那哪复述得出来啊?唱不出,就一遍遍地放,弄了半宿,这孩子就是一边哭,一边唱,他爸起码让他唱了得有100遍!太残酷了,我在旁边根本就受不了。我觉得如果不是这孩子心理承受力好,都得给逼疯了。”
与此同时,周边环境发生着的一切事情也让刘旭对儿子的出路充满焦虑。身处中关村,IT、网络的热潮,不仅使许许多多的理工科人才炙手可热,也让很多家长重新修订着孩子的未来。多数孩子学艺的局面到了初中戛然而止,把艺术特长当作避开电脑派位的敲门砖,进一所重点中学,考一个重点大学,进一家大公司,做一名收入不菲的软件工程师成为普遍梦想。刘旭听到了太多对考了音乐附中的王天阳的遗憾之声,“在中国搞音乐,哪有前途啊”,“你们家儿子数学那么好,搞音乐,以后什么都不会,跟不上时代了”……
儿子常回会来跟妈妈说学校里的事:今天搭谁家的车回来的,谁谁谁在国外比赛上又获得了大奖。这些无心之语,让妈妈听着却是无形压力,“学音乐那就是靠钱堆出来的。必须得有机会参加国际比赛才能出来啊,可音乐学院现在出国比赛不再公派了,全自费。我们怎么可能负担得起?”细腻的母亲不无苦恼,“现在一个男人压力多大啊,将来他职业不行,养家 口,买房买车都成问题。”
付出
影响也渗透到王骐身边,让他偶然惶惑。
“我是不太过于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再三地问着自己,也问儿子,“你自己说,想怎么着?”
儿子面对父母为他频起的矛盾,要么以沉默回应,要么说“随你们便”,他从不肯说“转学”二字。
10年。4岁半从幼儿园退园,跟着孙虹老师学视唱练耳;5岁学钢琴,并成为星海杯钢琴大赛上最年轻的选手,获少年组第二名;6岁为了练琴,推迟一年上小学;7岁考音乐学院附小,转入徐进行教授门下学难度艰深的视唱练耳;8岁加入杨鸿年的少年合唱团,以“神奇的耳朵”著称;13岁考音乐附中之前,已拿下了钢琴的十级证书。音乐主宰了王天阳的全部生活。通常,周末的日子,一天在合唱团度过,一天在钢琴老师家。去过一次意大利、两次台湾的王天阳说,他逛过的国外公园比北京多。
家里的一面墙上,被打造成玻璃橱窗的架子上摆满了一个个奖杯。这些,和时常浮动在空气里的争吵声,也会让王天阳很困惑,“有时我觉得该听妈妈的,有时又觉得爸爸对”。

除此之外,王天阳的痛苦只关乎音乐。
“四五岁的时候,爸爸总希望每学一次琴就能有进步,就特别怕他,一上课,整个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心里发凉,觉得自己不行。后来爸爸发现我害怕他,就躲出去了。开始我还奇怪,课上看不到他人,下课就溜达出来了。结果,有一天我突然看见窗户外头有张脸。他趴在那看着呢。”王天阳说,他到六七岁才有些不怕父亲了,八九岁以后,就完全不管有没有父亲在场了,“小孩子对痛苦是没有记忆力的,当时害怕,过了就忘,也不会记仇;到了八九岁自己真正喜欢弹琴了,痛苦就有了,有压力,怕被别人超越,发誓要赶上别人。”
说着话的时候,王天阳的手也在不停地飞速弹动着。王骐也许说得对,“他已经学会学习音乐的本事了。他在音乐领域里如鱼得水,你说让他断开再学普通数学、物理?”
梦想
王天阳对王骐意味着什么?
他笃信的天才培养论的验证?23年前自己考音乐学院失败的补偿?抑或是更高的梦想?
王骐是有更高的梦想。他坚信不远的将来,人们对于用丰富的手段提高生活品质的要求会很高,“中国教育现在老谈创新,创新不是光靠科学和教育就可以激发的,必须还得有艺术,艺术是人性的动力,我们早晚要走到这条道路上来。”
一说起他的教育理论,王骐就滔滔不绝:“天才是可以培养出来的,关键要拿住时机。儿童的4到6岁,是建立音乐素养基础的最佳期。幼儿耳朵里的绒毛很长,听力非常敏锐,随着年龄慢慢地长大,听的声音越来越多,它就会呈保护性的萎缩,所以不抓住孩子听力最佳时候训练,以后就得事倍功半。
“大部分中国人对待音乐的态度,就是玩一玩,听一听。中国的音乐教育也不过如此,小学阶段一、二年级以唱游为主,不要求读谱,不要求听音,带歌词的音乐成了当前为主的乐感教育,培养了孩子对音乐的爱好,却建立不了对于音乐本身的理解。这和中国以线条为主、旋律为主的音乐风格有关。西方研究音乐自身的逻辑性,每个独立的音都有它的固定音高,因此教育是以音感为先。德国人汉斯利克在《论音乐的美》中说过,音乐就是音乐,音乐本身的形式就是美,没有技术就进入不了音乐。
“教孩子就像在播种,必须在适当的季节、恰当的地点挖一个洞,让它发芽。小孩的心理特点就是兴趣来得快、消失的也快,学东西一不会就失去兴趣,其实真正入了门,兴趣自然而然就有了,学起来就由被动变主动了。困难的时候就要大人推一把,带强迫性的推动,不让他退缩。小孩的受挫心理都很强,我教孩子,用的是无关系刺激,唱不好,我一板脸,孩子就哭,哭也得唱,唱对了就鼓励,跟你哭不哭完全没有关系。就是要让王天阳不断地接受挑战,不断地面对挫折,他才能在成功中获得极大的喜悦和自信。”
王骐每往前推进儿子一步,这个家庭为此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去年9月,王骐一家才从平房中搬出来。那平房,一面墙挨着大家做饭、烧水的火房,一面墙外堆着煤,冬天下雪,夏天下雨,水淤在煤堆里,渗到地下,人在屋里,脚踩地,一踩就是一洼水。4岁半,那时王骐为了抓住儿子的学琴时机,坚决从对他教育方式无法认同的丈母娘家搬了出来,搬进平房,一住就是9年。“我们大部分时间就只好呆在床上。”王骐说,“为了王天阳,我的腰也不行了,老疼。他妈妈的腿都是黑的。他去台湾访问认识的好朋友来北京,总说想来家里看看,一直不敢叫人来,见不了人。”
为了儿子,父亲创造了一切可能的机会。这个家庭的收入2/3都投在了学琴上,但是为了让儿子出国进行音乐交流,王骐借钱,然后为人无偿打工,或者跑到学校帮人训练合唱挣得一点点额外报偿。带着儿子走道,走得都是节奏,王骐身上带着音哨,嘴里唱一个6/8拍的歌,俩人就走成那种节拍,一直走,遇到台阶也不停,直到一首歌完,再迈脚进行下一个作品;带着的哨音是用来校正王天阳的音准,如此的努力,把儿子的学习紧密地结合在父亲的生活里。
“我只是怕他错过这个时机,我真是知道这时机的重要性。如果他错过了这时机了,不是跟我年轻时在兵团耽误的一样了吗?!”王骐说。
分歧
为了儿子,母亲也在创造一切可能的机会。
曾是朝阳区成人教育局成人中专校长的刘旭,为儿子学琴,把工作调到了地处海淀区的北京101中学。至于损失是什么?也许就是房子、升职,但从成人教育转到普教,从管人变成被管,好几年刘旭都在一种被歧视、难适应的状态。“我忍了好多年,还不是为了孩子有朝一日能上101嘛,托底保险。”刘旭说。为了等这一天,她努力地工作,研究孩子教育心理,以至于每年的优秀班主任奖都给了她。“到头来,没用上!”
一直是刘旭在做着妥协,向王骐的教育方式,向儿子的未来发展做着妥协。经济也许只是一个表面的压力。在内心深处,刘旭还有做母亲的最普通心愿。“我特羡慕人家的孩子,充满童真,跟妈妈撒娇,可我从来没有享受过,王天阳不会,他在同龄的孩子中显得太理智。”刘旭说,“我要有第二个孩子,就不要他非得成为完美的人。我觉得做平平常常的人最幸福,不管干什么,地位有多高,只要心态挺好,生活有滋有味就挺好。”
王骐可能永远无法认同这种幸福观。要做就做最好的。这不仅是对儿子的要求。5月,北京市合唱节上,由王骐训练的三支合唱团,拿了少年组的五金二银——海淀区共获得11枚奖牌,他的占了7枚。在儿子1989年刚学视唱练耳的时候,老师认为他没有音乐的潜能、发木,王骐却偏偏不信。在他的坚持之下,终于有一天王天阳从听出一个音、二个音、三个和弦、四个和弦,到几年后听一把音,音块,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孙虹老师的话,王骐一直记着:“你不是一般的家长,你的孩子也不是一般的孩子。”
这场源于孩子教育方式的争执最终会以什么方式结束呢?
王骐在等待一个让他家人都欣慰的时代——那是王骐坚信不疑的未来,“我认为当我能够生产一个音乐家的时候,我为什么不去做这事呢?是我的孩子,我认为也是我能影响的一个学生,我对其他学生还施加那么大影响让他们接近音乐,在音乐中获得快乐,让他们去音乐中领略整个人类的文明,我对自己的孩子期望值当然更大了。我一直压抑着自己不过分地去干扰他。如果不发生什么大的变化,我想我们家这把舵是我掌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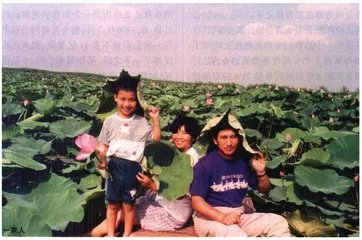
有关音乐教育
有一些数据看来充满矛盾,例如说,一份与素质教育相关的调查问卷说,有82%的学生喜欢音乐,认为一生离不开音乐的学生从8到18岁分别占43%到100%;而另一份针对“中国城市独生子女人格发展状况与教育”调查又说,有52.5%的孩子正在学习或学过钢琴等乐器,他们当中只有11.5%的人表示“非常喜欢”演奏乐器,有30.1%的孩子明确表示“不喜欢”和“一般”。
在双休日,我们的孩子47.8%的人被家长送去“参加特长班培训”。
1997年,中央音乐学院对3295名琴童的调查表明,有11.4%的父母因学琴会打骂孩子,33.3%的家长偶尔打孩子;至少有44%的琴童因“不听话”经常受到家长批评,21%的家长经常威胁孩子;40%的家长在孩子学琴时批评多于鼓励;因为是琴童,其中50%的孩子受到比其他孩子更为严厉的管教。
调查还显示,只有19.7%的琴童每天可得到玩的机会;32.9%的琴童每周有一次以上的机会出去玩会;12.1%的琴童很少有玩的机会,平均每月有一次以上;还有6.2%的琴童则在每月一次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