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性边缘》到《贝奥武甫》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马爱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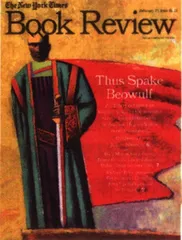
在本期上榜的畅销小说中,我们来看看与我们熟悉的作家的两部作品。
看到海伦·菲尔丁这个名字,读者一定会想起那本在两年多前轰动一时的小说《布里奇特·琼斯的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在那本书的结尾,当我们最后一次看见布里奇特·琼斯,这位开朗奔放、思维活跃的现代女子时,她正和马克·达西同居,在单身公寓里度过一个狂欢和纵欲的圣诞之夜。她对自己的生活现状基本满意,她感到同样满意的还有这一年的减肥效果:增74磅,减72磅。
《理性边缘》作为《布里奇特·琼斯日记》的续集,诚然缺少第一本书的那种独创的魅力和发现的喜悦,但女主人公以其亲切而富有喜剧性的对生活的描述和感悟,仍然使读者产生许多愉悦和共鸣,如同又看到一个你熟悉的身影,又听见一个老朋友在你耳边絮叨一些知心话。
是的,布里奇特的许多方面都没有改变。她的每篇日记仍然包括:体重,每日摄取的卡路里,香烟和酒精。她仍然是个“自信,情感丰富,冲动易感的女性”。她仍然害怕自己会孤苦伶仃地死去,“三星期后才被人发现,尸体已被野狗啃去一半”。每当这种恐惧袭上心头,她便恨自己为什么年过30还是形单影只,巴不得赶快找个人嫁掉。而平静下来之后,她依然不紧不慢地保持现状,冷眼旁观几个女朋友的情感生活,从中阅取一些经验教训,在日记上发一通议论,并经常在微醉的状态下入梦。
岁月不饶人,对于年逾30的单身女子,即使是布里奇特这样一位骨子里透着乐观、幽默的女子来说,时间的流逝也是既快得吓人,又显得沉重迟缓,仿佛永远熬不出头。在第12篇日记中,她已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恐慌,生怕有朝一日会失去马克。布里奇特的担心不幸成为了事实,她输给了情敌丽贝卡,由潜在的新娘沦为现实中的伴娘。于是,她怀着一颗失意沮丧的心去泰国度假,一路思绪翻腾,想入非非。她设想坐牢的种种好处,开列出长长一份清单:可以减肥,节省开支,因少用香波而保持头发的自然油性,等等。布里奇特不愧是个快乐的新女性,连排遣烦恼的方式也是这样幽默有趣。与此同时,她的事业也给她带来不小的安慰,她意外地赢得了采访BBC当红明星柯林·菲斯的机会,这使作为记者的她很是春风得意了一番。
读者也许已经悟出,海伦·菲尔丁的这部续篇的成功之处在于:布里奇特智商不高,有时甚至显得傻乎乎的,犯一些愚蠢的小错误。她的前男友曾说:“我怎么能跟一个连德国在哪里都不知道的人出去呢?”这么说可有点冤枉她。布里奇特当然知道德国是在欧洲,而且,关于怎样对付德国人,她还有自己创造性的见解。看见高速公路上路标林立,她便突发奇想:“如果现在爆发战争,我们就把路标弄乱,让德国人摸不着头脑,这岂不是很妙?”后来,据一个竞争对手透露,布里奇特竟认为兰波(Rimbaud,法国诗人)是史泰龙扮演的一个角色。这些傻乎乎的想法使我们感到多么亲切啊,因为我们在畅销书中看见过太多才貌双全、伶牙俐齿的俊男靓女。
我们怎么能不喜欢布里奇特呢?——尽管她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事实上,正是由于这些缺点,我们才觉得她格外可爱。我们还喜欢她身上那股乐观向上的劲头。她对待生活是努力和认真的。在她的日子里,总是充满了灿烂明艳的希望和憧憬,然而紧跟着便是挫败和失望,许多美好的计划不了了之或草草收场。她对绝望有着深切的认识。当她在一本心理指导书上读到“你感到自己一无是处吗?你认为自己不讨人喜欢吗?”这样的句子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唉,不是认为,是事实如此啊。”但是她的心情恢复得也快。不管怎么说,生活总是往前走的,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日子也就在期盼和等待中一天天地过下去。在小说的最后,我们看到布里奇特在痴迷地端详杂志封面上威廉王子的照片。“多么富有王族气派,”她感叹道,“真像是古代的圆桌骑士。”然而,唉,王子会是个单身汉吗?
《贝奥武甫》这部英雄史诗是古英语文学的最高成就,是最早用古英语(盎格鲁-撒克逊语)写成的史诗,见于大约1000年留存下来的孤本手稿,讲述的是公元7~8世纪开始流传于民间的故事:公元6世纪初瑞典王子贝奥武甫帮助丹麦灭除巨妖和火龙,最后与火龙同归于尽的悲壮经历。
谢默斯·希内(1939~),爱尔兰诗人,生于德里郡,大学毕业后任教,1965年出版第一部诗集《诗十一首》即引起注意,翌年出版的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的死亡》使他一举成名。他的诗作多表现爱尔兰乡村的生活,赞颂劳动人民的辛勤和纯朴,地方色彩浓郁。另一些作品描写政治动乱和宗教纷争,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情绪。因其诗作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他于199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严格地说来,希内对英语诗歌传统始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是英语压制了爱尔兰丰富的诗歌遗产。因此,当80年代中期《诺顿英国文学选读》的编辑约请希内将古英语的《贝奥武甫》翻译成现代英语时,他的兴趣并不强烈。而在编辑们看来,史诗的内容与希内作为诗人的才情和他所关注的主题十分吻合:一位英雄如何战胜野蛮威胁家园和祖国的敌人,以及在一个被暴力蹂躏的世界上社会关系变得何其脆弱。事实证明编辑们的眼光是准确的。
法国畅销书评
《薇罗尼卡决定去死》
大家熟悉的巴西作家保罗·柯埃略曾以《炼金术士》风靡全球,他新近又出版了《薇罗尼卡决定去死》,连续7周登上法国畅销小说排行榜,如今名列第四。
《炼金术士》译成44种语言,销到近百个国家,总计售出2600万册。《快报》书评说这本书的成功就在于“个人传奇”,书中说每个人都有一个使命,既符合他最隐秘的愿望,又能给他以最大的幸福,有些人之所以没有完成,就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自己能完成。柯埃略所言之事有亲身经历的成分。他从小就想当作家,遭到了父母非常粗暴的阻拦,直到40多岁才开始自由地写作。
《薇罗尼卡决定去死》涉及的是同样的主题,决定去死就是决定拒绝被强加的生活,患有抑郁症的年轻女孩薇罗尼卡自杀不成,被送进精神病院,只好通过掩饰和伪装,让别人相信自己跟大家是一样的人,以求宽大处理。这也出自亲身经历,1966年柯埃略被父母送进精神病院,唯一的罪过就是他要当作家,他回忆说:“那个时候的中产阶级家庭根本不让子女从事艺术工作,万一谁把这个词跟现实的人生联系起来,大家对他就会像对同性恋者、赤色分子和吸毒者一样。”遭受多次电击治疗之后,柯埃略回了家,但他还是坚持写作,结果又被多次送进精神病院。后来终于有位医生费尽口舌,说服他父母“不一样”不等于“不正常”,才让柯埃略彻底摆脱了被治疗的生涯。在薇罗尼卡的故事当中,柯埃略同样借一位医生之口说出了这番话:“每个人都是唯一的,有自己的本能和追求的方式,而社会却有强加的共同方式,很多人习惯以后,甚至不再追究自己为什么非得跟所有人一样不可。这时候,假如冒出一个就是要跟其他人不一样的人,非常遗憾,他就只能被认作病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