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她俩把“问题”解决了
作者:王珲吵架
你得承认,仗在虚拟空间和真实生活里打来打去,已经波及好多人。
好多人是无辜的。他们或是看到网上的叫骂,或是从熟悉的报纸上不断看到“卫慧”、“棉棉”这几个字,于是冲到书店。
北京风入松书店里,卫慧与棉棉的书摆在一起。收款台的女孩子们说,《上海宝贝》已是第二次进货;而棉棉的《糖》在它的对面,深陷在周围高起的书中间,也不存几本。
有人把书店里她们的书的脱销——一厢情愿地想成是“书店禁卖”及“读者有意识抵制”。
买了书的人多是大呼上当。尽管《上海宝贝》不过16元,《糖》比它便宜2块。
更多人返回网上加入谩骂。
到4月19日时,网易的“卫慧和棉棉谁惹了谁”专题论坛里,帖子已逼近5000条。黄金书屋那边也是如火如荼,有4000多条帖子,点击率达到150000人次。
有几件事和几个人直接推动了此事。
首先当属3月13日李方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文章,《你是美女吗?当作家去吧》。此文一出,即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弄得3月23日李方赶快在网上补充一文,说明自己是害怕女性性意识过强男人招架不住而为《上海宝贝》呕吐的“阴暗心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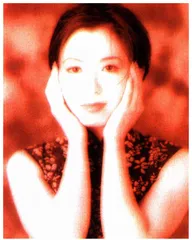
棉棉的《啦啦啦》
对骂
4月8日,发表在《阅读导刊》的封面报道——“卫慧抄袭棉棉”,挑起了两个人对骂的开始。
网易把“卫慧的姿态”和“棉棉的声明”摆在一起。你点击卫慧的笑脸,那里写着“我有严重的学历歧视”。
近3000字的《卫慧没有抄我》和写于1998年只有500字的《棉棉厌恶》摆在一起,可见作为《上海宝贝》的读者,棉棉的厌恶情绪几倍增长。
4月13日,卫慧和棉棉先后在论坛出现,卫慧干脆直言对方“有着太多在深圳做妈咪时留下的凶狠和脆弱气质”。棉棉回应说,“卫慧,做你自己爱你自己”。
两个人的对打——被人形容为“两个女流氓的叫骂”,激起的热闹和愤怒超出了最初的范围。
为了弄清谁真谁假、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或者谁坏谁更坏,好事者做了许多事:提供登有卫慧、棉棉照片的网址——用以彻底毁灭许多人对于“美女作家”的幻想;四处收集卫慧的一切,包括她来自浙江,她个子不高,她的着装品味,她的复旦情结,她变换着的外籍男友;自觉译出德国《明星》采访棉棉的全文——在那本通常惊世骇俗的精彩杂志里,棉棉对国内媒体一直不加细述的18岁至25岁之间的放浪生活被描述成这样,“18岁时,她辍学,……跑到毗邻香港的深圳,……在那儿她有了第一个男人。……之后,她经营一家妓院,爱上了一个摇滚歌手,可是这个男人却和她的女朋友上床。于是她沉溺于海洛因。”
有了这些,人们的同情心、辨别力更趋复杂,但好奇心日重。
网易的作风显得飘忽不定。4月16日“假道学”写出《真实?做秀?》一文,大意是说卫慧抄袭棉棉的思想、行为方式,棉棉则抄袭了一帮朋克乐队。
17日,卫慧抗议删除,否则诉诸法律。
网易对此举不屑一顾。
已完全不再是卫慧和棉棉在吵。网友中混杂着自发的及有预谋的倒卫派、倒棉派,更多的人双管齐下。仔细看看,顶着“王安忆”、“苏童”、“王朔”之名的人也在讲话,有些人还讲得特别好,文章一次一次被热心网友从淹没状态拎到前方。
难怪有人会叹:“怎么对卫慧的口诛笔伐比抗议美国鬼子轰炸我驻南大使馆还要厉害啊。”
网络是个让人疯癫的地方。
明星
阴谋论者坚持认为,无论是两个人的对骂,以及蔓延在网上、纸媒体的吵闹,都是商业炒作行为。“因为这些炒作,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了她们,这就是所谓的‘注意力经济,”。
但令很多人痛心疾首的是,为什么是她们——充斥着吸毒、同性恋、乱交、地下摇滚的写作——而不是别的什么,被抬高到“新生代”的隆重地位,被传媒竞相吹捧。
一家时尚类刊物的编辑一语道破其中机密:“你可以说,卫慧和棉棉们就是被我们这类杂志捧出来的。”
1999年,棉棉下午4点起床,晚上组织主题派对的生活开始被倡导时髦生活的杂志捕捉。她在杂志上的语言惊世骇俗——“用身体检阅男人,用皮肤思考”。国外媒体也纷纷报道。他们把她的写作视为“这个新的、狂野中国里肮脏地下生活的见证人”,称她作“亚洲的凶猛动物”。
与此同时,卫慧的“出位”写作正与尾页缀着“小小说”或“都市情感”之类栏目的女性刊物的需要不谋而合。她也被国外媒体形容为“小说雅皮”。
那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编辑告诉记者,“我们这圈子包装了四大美女作家,她们风格类似,大多打扮各色——穿艳俗的中式服装,抽烟,以自己的情感经历为写作内容,不是写麦当劳或地铁里偶遇的爱情,就是写写坐台小姐的情感惨剧,再就是露骨的、总是无疾而终、被爱情摧残的故事。”
网上的一则评论语言尖刻:“在今天,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她写的东西远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一、她会不会炒作自己;二、她漂不漂亮;三、她敢不敢写揭露自己的隐私;四、她是不是著名文化人的老婆(或情人)。”
IKEA、“卡布基诺”、“可可·夏奈尔”、毒液香水……这些出现在卫慧文中的语汇,不正是时尚生活的倡导?卫慧们如此写作,怎么不落入“新新人类”的时髦?
面具
卫慧、棉棉们写作自己的欲望,生存状态,趣味——无论高级低级。当赤裸裸的欲望从一个女子笔下滑出、还被争相阅读的时候,人们就被激怒了。
“现在的卫慧们居然认为性权利是男女平等的,怎么不让我们为自己的妻女担心!”
“一流的教育、良好出身、漂亮的外表却演绎着娼妓的生活。”
“难道还嫌我们的国家不够乱吗?”
“那些忙着挣钱的编辑,敢拿这样一本书给自己的孩子看吗?”
“文化上的亡国奴心态被粉饰成时尚招摇过市。”
“为什么她的性高潮一定要来自异国男子呢?”
“越来越多的人自傲于某种‘高人一等’的生活方式,他们已经不再骂别人农民,而是矜持地不屑一顾所谓‘平民的’一切。”
中国人用传统的思维定势对作品加诸沉重意义。对社会的失望,对教育的失望,对道德的失望,甚至包括对两性关系的失望像臭鸡蛋一样被投掷到作者头上。
还好,网上有些尽管势单力薄却较清醒的声音:
“不分析《上海宝贝》产生的历史背景,一味用传统说教民族主义阿Q心理甚至流氓眼光来评价卫慧及其作品,是文化的阳痿加之太监的恶毒。连个卫慧都容不下的中国,徒有其大徒有其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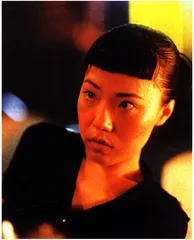
棉棉(胡渝江 摄/《时尚》供图)
“即便你不承认,你也一样是一个对异性的性行为有强烈反应的女人,而且这没有什么不道德的,这才是最正常的,那些被旧观念压抑的“性冷淡”可怜虫,才是不正常的。”……
在商业社会里,一切都可真可假。80年代中期,麦当娜唱《宛若处女》,唱《像个祈祷者》,她是如此反叛。到了90年代中期,麦当娜开始从良做好母亲。早先美国公众们的举国哗然,除了把她的专辑送上了销售排行榜的第一之外,事到今天,一切都趋于平静。
一位同样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杂志编辑说:“在商品社会中,性当然是有卖点的。早年间,就有人写文章预言,下一代中国电影明星将是‘脱星’,可惜我们到现在也没见识大陆的脱星。歌坛上不会出现麦当娜,电影中也不会有《本能》里的莎朗·斯通,相对自由相对沉寂的文学倒因卫慧和棉棉热闹起来,这事儿无奈、无聊,土得掉渣儿。”
卫慧和棉棉之争,为社会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