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蹒跚神童的一部令人心碎的作品》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马爱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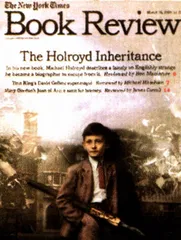
在本期上榜的几部新书中,最值得介绍的恐怕要算戴夫·埃格斯的《蹒跚神童的一部令人心碎的作品》这部充满人情味的“令人心碎的”自传。
这本书实际上是作者戴夫·埃格斯为接受电视台“真实的世界”栏目的采访而写的回忆录。书中叙述,在埃格斯21岁那年,父母身患癌症,在短短32天内双双撒手人寰,留下他独自抚养8岁的弟弟托弗。正在读大学的埃格斯辍学回家,卖掉了位于伊利诺斯州湖畔森林的老房子,带着弟弟迁往加利福尼亚。他们一路放声高歌,风驰电掣般地驾车驶往旧金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家。埃格斯一方面有意识地使自己的形象与同龄人相吻合:作为一个20来岁的小伙子,他懒懒散散地住在一间肮脏邋遢的公寓里,并开办了一种讽刺杂志,在上面发泄青春的躁动和叛逆。另一方面,他又表现出一种与之完全对立的形象:父母双亡,长兄如父,他像50年代的一个有责任心的成年人一样,恪尽父亲职责,定期参加家长-教师联谊会,为托弗安排一日三餐,在睡觉前给他讲故事,关心他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发展。“我24岁,”他在书中说,“却感到自己很老很老,简直有一万岁了。”
埃格斯的阅历和责任使他与大多数同伴有些格格不入,他显得既桀骜洒脱,又老成持重。在他看来,任何无法想象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因为命运已经向他展示过这一点。他写道:“在我的生活里什么都可能出现,我不会感到半点惊讶。地震、蝗灾、毒雨都不会使我吃惊。天使降临人间,独角兽,举着火炬和权杖的蝙蝠人——所有这些都是可信的。”死亡的噩梦仍然把他纠缠,他经常莫名其妙地担心死神会把托弗夺走。但他认为,这种担心同时也给他带来刺激,使他振奋、紧张,使他感到生命的每一分钟都弥足珍贵。
埃格斯觉得,他有责任给托弗创造一种轻松的气氛。他和托弗的生活就像一部名为“听哥哥的没错”的系列情景喜剧。他们做各种游戏,在房间里互相追逐、打闹,嘴里含着水,随时准备喷向对方。他们坐在餐桌旁吃饭,试图体会家庭的温馨,“但是不太容易,”埃格斯写道,“桌子上横着乒乓球网呢。”他们的生活,正如书里写的那样,“充满五彩缤纷的乐趣,烟花爆竹,杂耍舞蹈,魔术把戏。猜猜这是什么!快看这儿!是不是够棒?”
大多数时候,他们的房间里都是又脏又乱——到处堆放着变质的食物,用过的碗碟,待洗的衣服。托弗的一位朋友感叹道:“天哪,你们怎么能这样过日子?”对此,埃格斯承认自己时常感到“沮丧和内疚”,他甚至担心,会不会因为自己没有准备好早饭,没有督促弟弟去上学,而导致弟弟心理变态呢。
埃格斯的这种顽强适应性恐怕与他们原先贫苦的家境有关。在平静的湖畔森林,埃格斯一家没有地位,属于贫苦的白人。父亲是个烟鬼,母亲大量地被动吸烟,这恐怕就是他们双双早逝的原因。“镇上就数我们家最穷,”他写道,“衣食住行全成问题。我们的老爷车破旧不堪,墙纸还是70年代的,日常用品都是廉价而简陋。”在埃格斯看来,是悲剧把他造就成了一个“超级英雄”,这多少有些黑色幽默的色彩。“突如其来的灾难使一个好脾气的人产生了突变。麻烦接踵而来,人就只好在变异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怀着一种绝望和希望混杂的心情,做出许多古怪而愚蠢的事情。”
埃格斯抚养弟弟的方式带有戏剧性和试验性,他的写作也同样如此。这部“以亲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录,充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力和创新。长长的书名带着浓重的自嘲和夸张,它的语言,它的篇章结构和宣传文字,许多地方都与众不同,有一种俏皮和跳跃的风格。乍一看,读者或许以为这是一位玩世不恭的弄潮儿的探索新作,仔细读进去以后,才发现这是一部扣人心弦,充满真情实感的作品。对于表面上的这些并不高明的小花招,他自己承认道:“这只是一种策略,一种保护措施,为了掩盖整个故事核心部分的那种刻骨铭心、痛彻肺腑的悲伤和失落。”
总的来说,《蹒跚神童的一部令人心碎的作品》是一本诙谐而不失真诚,轻松中蕴含深情的好书,这实际上也是它成功的秘诀。埃格斯的语言十分生动,但他并不做无病呻吟或感情泛滥式的渲染,只让读者自己去体会深层次的情绪和蕴意。书中有一个场景既滑稽,又感人,同时又触目惊心:埃格斯在父母去世后第一次回到湖畔森林,把母亲的骨灰撒进密歇根湖。他原以为骨灰是细密的粉末,却吃惊地发现它乱糟糟的活像一窝猫崽。他很不顺利,骨灰总是沾在他汗湿的手掌上。他不小心把一些骨灰洒在了地上,弯腰去捡时,又弄洒了更多。慌乱中,他居然一脚踩在了骨灰上。他吓坏了:“我真是个孽子。可怜的妈妈,她准要怪我了。”
书中还写到另外几例死亡。一位朋友自杀;一位同事的女朋友自以为食物中毒进了医院,几天后不治身亡。两个人都不满20岁。所有这些,作者都用平淡的、就事论事的口吻讲述着,没有作很多无病呻吟或感情泛滥式的渲染,似乎他只是一个旁观者。但是不知怎地,在直白的文字背后,始终有一种灰暗的底色提醒读者:这是一个经历过痛苦的人,这是一颗受过伤的心灵。当一个朋友昏迷不醒、生命垂危时,他到医院里去看她。“我知道这种事的规矩,”书中写道,“我们不能笑,不管怎样都不能笑,除非他们家里的人先笑了。我们必须穿得整整齐齐,准时到达那里。”
法国畅销书评
日记的供应和需求
日记是作者与本人的日常对话,他们通过这种形式检查自身的存在,满足认识自我的需要,也因此更好地接受自我。这种文学形式历来有多少供应就有多少需求。安德列·纪德坚持记日记半个多世纪,“我发疯时写,清醒时做修改”,这就是他呈现内心的无序状态并使之合理化的最好途径。保罗·勒奥多说自己写日记就像“一个门房不停地说房客的坏话”,他的《文学日记》赢得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的喜爱。
日记的创作和出版在当代作家之中依然常见,最近在巴黎书架同时出现的就有多米尼克·罗兰的《恋爱日记》,米歇尔·戴勒·卡斯迪罗的《向世纪告别》,让·夏龙的《巴黎日记》和安妮·艾尔诺的《外面的生活》。书评家认为写得最好的是多米尼克·罗兰,这是一个女人与一个名叫吉姆的男人持续40年的顽强的爱情故事,吉姆比她小22岁,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小说家菲利普·索雷尔,但是对相爱的人来说,数字没有意义,他们拒绝政治上正确的爱情观念,完全听从内心的需要,时空被他们超越了。《巴黎日记》有点普鲁斯特风格,它记录了1963年至1983年作者与可可·夏奈尔、尤瑟纳尔等人的对话。《向世纪告别》是启蒙出版社给卡斯迪罗布置的作业,连续6年来,启蒙社每年出版一套日记系列,此前应邀出版日记的多是媒体名人,如《新观察家》专栏女作家弗朗斯瓦·吉胡,有些书评家指责他们的日记不像私人物品,更像工作日志。相比之下,卡斯迪罗比较谨慎和骄傲,他把自己关注过的事和人,连同其中的秘密,告诉了大家——以他特有的有所保留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