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寻求自我的戴安娜》到《科索沃十字路口》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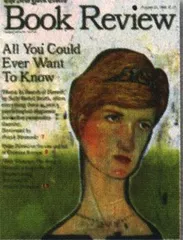
《寻求自我的戴安娜》一书出版于她去世一周年之际,这是出版家善于抓季节的招数。但无论如何,这部书比起一年前戴安娜突然死于非命时临时拼凑出来的东西要认真和深入得多。该书作者萨莉·比代尔·史密斯是一位传记作家,此次她把兴趣转向戴安娜是有相当准备的:她在戴安娜生前曾采访过她,后来又做了大量调查,再经过筛选、对比和参照,因此材料翔实而可靠。在她的笔下,戴安娜简直是个疯子,甚至比疯子的生活还要多一道阴影。
作者曾与查尔斯王子(顺便讲一下,按英国惯例,王储都要封为“威尔士亲王”,故戴安娜可以称作王妃)和戴安娜谋过面,她把这一段写在全书的开篇,或是以此表示该书的可信性吧。当时查尔斯在温莎参加一场马球赛,正在聚精会神地倾听他祖母的一位老朋友的谈话,而戴安娜则在玛莎葡萄园中和一些巴西朋友待在一起。戴安娜“美得迷人”,却拒绝谈话:“这是我们这颗星球上最富慈悲心肠的一位女性,但似乎不动感情。”因为戴安娜怀疑作者在“密切观察她”,戴安娜可能是对的,因为她是个能一眼望穿那些密切观察者的人。接下来的叙述便让读者体会到,查尔斯比戴安娜更能殷勤待人,虽说他的教养和王室传统使他不善驾驭这位乖戾异常的妻子,但他在那种场合下仍显得关心备至,而王妃则喜怒无常,十分任性。
这部诚挚的作品提出了一些普通经历的人所无法回答的问题。因为一般人难以想象整天受到无孔不入的记者和偷拍镜头的摄影师的骚扰的苦恼。对于戴安娜,有时人们认为她很容易和记者合作,但也有人说她很善于回避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这些名人的私生活很难不成为公共表演;当然,从小约翰·肯尼迪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些名人处理得还是比较巧妙。
戴安娜本来就是大家闺秀,所以她对王室批评起来并不外行,比如她觉得丈夫的乡间别墅还不如她娘家的房子。倒是报刊的披露和饶舌,把她抬到一种莫测高深的童话中的公主般的地位,千百万读者再随声附和,于是她的美貌、她的服饰,以及她的一举一动,都见诸报端了。
王室原本就惯于受人敬仰,这就进一步鼓励了骄纵任性。书中所写的戴安娜,是一个难以捉摸、自我中心、咄咄逼人、坐卧不宁、自作主张、患妄想狂、有占有欲、易于厌烦、未受教育、惯于撒谎的人,是个可怕的情绪摇摆的牺牲品。她偷听别人说话,私拆他人信件。总之,她的一生是“通奸、精神病、背叛、多疑和报复的一个悲伤故事”。
一个位高言重的女性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多麻烦的困扰呢?传记作者开出了令人折服的诊断:戴安娜患有“边缘性的个性紊乱”,所谓边缘,就是介于精神病和心理失调之间。作者认为,她很像那位影星玛丽莲·梦露,在美国妇女中有600万人患有这种症状。戴安娜的许多疾病,尤其是易饥和食欲过盛,正是这种深层的紊乱失调的症候,而且有拒绝治疗的倾向。
那么又该如何解释她的魅力,她的众多善举呢?这主要是媒体大吹大擂的结果,作者认为,戴安娜对爱滋病的关切是“出于个人考虑的动机,而不是关注社会问题的雄心”。面对紧急情况,戴安娜偶尔表现出行动果断,但这却说明不了问题,因为她这样做的时候为的是显示一种“虚假的成熟”。
作者笔下的戴安娜几乎一无是处了;但在对查尔斯的同情上却写得相当含蓄。
作者援引戴安娜一位亲属的话说:“她本来性格蛮好的,只是脾气坏了点。”当然,她的脾气,就是边缘性个性紊乱的病状。
无论这部传记与人们以往对戴安娜的印象多么大相径庭,但我们终于有了一种新概念。
另一部书是未上榜的,书名叫《科索沃十字路口》,副标题是《美国理想在巴尔干战场上遇到了现实》(Kosovo Crossing:American Ideals Meet Realityon the Balkan Battlefields)。作者是大卫·弗朗姆金(David Fromkin)。评家认为:起于1991年夏季的科索沃战争在今年6月结束了(但愿如此),今年肯定会有大批书籍撰写这一热点。本书虽称不上最佳,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该书作者是波士顿大学的历史及国际关系学教授,全书用轻松笔调写出有学识的观点,适于不同层次的人阅读。当然,其观点会引起众多争议。我们中国人也只能参考而已,无论如何,总是一家之言吧。
作者用了四分之三的篇幅叙述两个问题:第一,介于威尔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总统)的道德主义和以实力关系为基础的治国能力之间的美国外交政策的紧张;第二,奥斯曼及哈布斯堡帝国(曾先后统治过巴尔干地区)的覆灭。以此来说明全书提出的:“美国在其国境之外有实力做好事——甚至并不清楚什么是‘好’事——的程度问题。”
作者认为,美国“选择了卷入南斯拉夫的政治”,并没有为“其自身的任何特殊利益服务”。“一般说来,美国只在保护其生命攸关的利益时才出兵参战。”这一般规律反映了一个现实:美国选民不会容忍对一件并非利益攸关的事情轻举妄动。
在笔者看来,这位教授虽然精通历史和国际关系,却天真地忽略了一个基本概念:美国要独霸世界!这正是其根本利益所在。
黑暗中的心
今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动60周年,两部二战问题研究在欧洲出版。一部是法国的《文学之恶》,分析了被占时期为什么有的作家投入抵抗运动,有的却参加了维希政府;另一部是德国的《戈培尔日记》,共12000多页,分7册出版。两部都是对黑暗中人心的测量。法国人说,当年法兰西学院的名作家都跟德国鬼子合作了。戈培尔日记里描述了1933年到1939年间他搞法西斯宣传时,德国民众怎样自发地,几近疯狂地响应着他的号召。
《费加罗报》书评说,把某个人妖魔化,中间总会有过于绝对的成分。即便戈培尔,也还是个人,人的一切对他都不可能完全陌生。读戈培尔的日记,人们看到的也是一颗被理想和利益驱使的心,只不过他的理想和利益极端黑暗。这个小个子男人中学时候成绩非常好,精通拉丁文,但是同时代的语言除了德语什么都不学。他信奉民粹主义,同时又为一个半犹太血统的女教师神魂颠倒。他全心全意跟了纳粹,获得了绝对的地位和权力,也走向了绝对的腐败。19世纪下半期和20世纪上半期整个欧洲的价值系统几乎都建立在类似的基本逻辑之上。
戈培尔历来被当成希特勒的忠实信徒,在灭绝犹太人的问题上,他的日记里没有一个迟疑或者后悔的字眼,他的目标是明确的,手段是清晰的。但是他的日记偶尔也有与“元首”相左的想法,帝国末期尤其明显。1940年间,戈培尔多次写道:“元首像拿破仑一样,在神力引导下勇往直前,所过之处不留后路。”看似崇拜,实际上透露出他对希特勒过于贪婪和冒险的担忧。1945年前后,他又写道:“元首不停地干傻事,他把俄国引入战争,又招惹了美国,现在我们身陷绝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