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到《宫殿》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武夫 刘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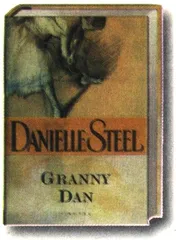
本期仅有的3部上榜新作中,海明威那部《曙光中见真实》,我们已经介绍过,另两部无非是“性+暴力”公式的产物,其实没有太多的文学价值。因此,本期的书籍介绍只有另辟蹊径了。
由《纽约时报》文化编辑约翰·达恩顿(John Darnton)撰写的《实验》(The Experiment),从书名上即不难猜出属科幻小说。
虽然现实生活中难分彼此的双胞胎只有4‰的概率,但由于人们的自然兴趣,往往构成文学作品中的插曲,甚至主要情节线索。双胞胎的人物和故事出现在作品中,不是笑料频生,就是惊险倍增,其核心无非是“误会”二字。时至今日,无性繁殖的“克隆”技术既已出现,且又引起人们对其前景的议论纷纷,写一部克隆人的故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实验》一书开始时是在佐治亚州海岸外的一座小岛上,那里设有一个秘密科学实验室。由上年纪的医生和勤杂人员监管着两个人:斯凯勒和朱丽娅。他们是一项医学实验的对象,要定时定期接受注射和不明所以的古怪手术。书中写道:“在他们的岛屿天堂里,通过精神纯洁和身体健康的摄生法(即采用指定的食物或规律的生活方式休养、锻炼,达到增进健康或提高运动成绩的目的),使他们度过长寿和丰富的生活。”——这便是“主日教义服务中心”的目标。
然而,他俩却发现了一具内脏已被取走的尸体,表明那个“中心”在骗人,于是在朱丽娅消失后,斯凯勒就逃出了小岛。他不久却看到了一个与他长得丝毫不差的人,遂尾随那人来到在混杂的环境中不辨人格的纽约市。
与此同时(该书经常使用这个词),与斯凯勒酷似的那个人:裘德·哈里,职业是记者和作家(这一点与作者身份相同,我们且不去管它);裘德本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却不幸地卷入了一场尴尬的谋杀案。他不久后去见一位双胞胎专家伊莉莎白(蒂姬)·台尔尼医生。当蒂姬把模样稍显年轻的斯凯勒误认作裘德时,斯凯勒却看出蒂姬与朱丽娅长的十分相像。自然,这两对相像的男女惹出许多纠缠不清的麻烦。原来,早在多利克隆羊出现之前的几十年,有一群无事生非的科学家便克隆了他们自己孩子的胚胎,目的是为他们提供待移植的器官——但他们必须活到150岁。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他们又开始克隆成人——目标是权要人物;同时进行延缓青春的研究。但后一项实验失败,婴儿都早熟而且都进入了消费期……
写科幻小说诚然需要相关的科技知识,作者在这方面还是没有令人失望。最近已发现多利羊的细胞比其年龄要老。其实,《实验》一书早已对此有所预见和解释:动物细胞在死去之前可以分裂50次,因此,在克隆动物和双胞胎之间仍有极细微的基因差别。
作者也没有回避由于克隆技术引发的社会伦理的复杂问题(至于器官、组织和医药方面的市场方面的问题,自不待言)。他还指出了克隆技术的哲学复杂性:大自然就是物种间和物种内斗争。物种要求自身的繁殖,而个体则要自身的长寿。前者需要变化和突变,而后者则需要不变和“壅滞”(医学名词,即停滞)。这一冲突是势不两立的。”
围绕医学难题这一中心,作者展开了社会的多层画面,从学术界到联邦调查局,从乱糟糟的社会到谋求平静的人生。是啊,问题是提出来了,但我们难道要求作者来解决吗?
8月份,《纽约时报书评》推出了一批以意大利为背景的作品,其中有二战后幸存的意大利作家小说的译作,也有英美作家以不同的意大利城市为中心的作品。下面我们就介绍英国作家丽莎·圣·欧宾·德·特朗(Lisa St.Aubin de Terán)的长篇小说《宫殿》(The Palace)。
故事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的威尼斯。主人公本是一石匠的学徒,后依附于一贵族,遭牵连成为政治犯而入狱,临刑时逃脱,遂取一绅士名,做上等人状,来到威尼斯,在赌场上赚了大钱,遂在翁布里亚(位于意大利中北部)建起一座宫殿,专候他的心上人——只在他15岁那年对他笑过一次——来住。
这位自称加布里埃尔的人,一生多亏他的几位师父。第一位是他的耽于玩乐的叔叔,教会了他如何像城里人那样玩纸牌和赌博;第二位是石匠,他把这年方9岁的男孩买下,从乡下带走,教会他热爱并学会大理石雕刻的技艺,后遂以善雕天使为业;第三位是一贵族,趁共同坐牢之机,教会他优雅的言谈举止和上等人的生活方式,此时同狱之人一个个被提出去处决。他们通过行贿,侥幸出狱,相约到威尼斯重聚;他在威尼斯雇了一个机灵的平底船夫,为他找到了适当的住所,很快便带他熟悉了全城,使他成为地道的本地绅士,那船夫就此成了他的贴身男仆、同伴、财务顾问乃至拉皮条的人。而加布里埃尔始终梦想着要修一栋石头大宫殿,有花园和湖河,以便吸引他的那位意中人。一夜,他在威尼斯最臭名昭著的赌馆中赢得了翁布里亚的一片土地,可以实现宿愿了。
这样一个神话似的故事似乎应该发生得更早才是,否则很容易把握不住时代背景,更显得老生常谈。但作者在写作手法上注意创新,以第一人称的叙述使全书始终像是内心独白,尤其那种细节描写之真实,使读者真想在意大利旅游时去参观一下那座宫殿。至于把主人公安排成一个雕刻大理石天使的能工巧匠,更是富有深意:洁白的石头无异于对人的品质的试金石,天使不消说是高尚的象征,那么雕刻的匠人呢?
跟人体起腻
(刘芳)
夏季大休假之后,法国文坛重新热闹起来,6位青年作家尤其引人注目,《费加罗报》评点说他们全都迷上了身体暴露和身体摧残,都在“跟人体起腻”。
最红的一部小说叫《肉》,宣言一样的书名,“viande”在古法语中指食品,今指家禽或家畜的肉,粗话中也有人体的意思。作者克莱尔·莱让德尔出自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她对肉体的描写让人联想到屠夫和兽医:“她睡在他身上,想最后一次爱抚他,乘着他还热。轻咬他的屁股、大腿,那些柔软的部分。然后是牙齿,它们总是咬得紧紧的。”《肉》的女主人公苏珊有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突然长出了男性生殖器,性和性别从此成了困扰她的问题——“我只想拿起刀,几下把这块肉剁掉。”
雷吉斯·克兰卡的《肉的辩解词》(原文也是viande)写的则是男孩被女孩过度挑逗之后的反击:“我坐在抽水马桶上,瞧着我的阴茎,这是我最大的空虚所在。我想起了她们强加其上的爱抚。我两手握住这柔软的、象征我是男人的小东西,在切下它之前,我深深吸了口气。”
似乎因为写的是破裂的身体,这些作家的语言也成了碎片。尼古拉斯·佩吉在《我吃一个鸡蛋》中这样说话:“我醒来,我搓了搓脚,我冷。我看了看天气,满天都是云。我走进厨房,跟C说了一会儿话。我冲了杯咖啡……”
《费加罗报》评论说,作家跟人体起腻,平白无故令人体受辱,意味着他们语言的终结,他们的文字都蜷缩成了结构重复的断句,甚至一个词。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弗朗斯瓦·努里斯则说:“小说有三件大事,时间、激情和社会,人体至少揭示了其中之二。它可用来丈量青春和衰老,也能用来证明犯罪和惩罚。在压抑和病态的社会里,人体难免成为供求关系下的商品,象征着生活已被彻头彻尾地商业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