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8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劳乐 施武 杨春燕 应明)
厕所
劳乐
我小时候一直管那个地方叫“厕所”,后来才知道这种叫法不是太雅。当然,那时我不知道有一种更不雅的叫法是“茅房”——虽然我一直不知道这种叫法的起源。后来我所知道的比较雅的叫法是“洗手间”。但高雅东西的含意总是有些含混,于是就出现过服务小姐真引导我到洗手池旁找“洗手间”的事。终于有一天我在《史记》鸿门宴一段中看到那里大大方方地写着“沛公起如厕”,从此我对“厕所”这种叫法另眼相待,觉得它颇有一些古雅的意味。
在英语中也有类似混乱的情况。通常人们觉得说“WC”没有什么,但实际上这个缩写的全称是“water closet”,对应的汉语和说“茅房”差不多,更雅的说法当然是“toilet”。和许多高雅词一样,这个词来源于法语。“toilet”这个词不仅本身高雅,而且经常可以为后面修饰的词语平添几分身价。”“soap”前面加上“toilet”就不再是肥皂,而是化妆用的高级香皂;千万不要以为“toilet water”是冲马桶(或者说:坐便器)用的水,它的实际意思是化妆水或花露水。“toilet table”指的是梳妆台,但你不应由此认为“toilet seat”指的是马桶——“toiler seat”的意思是马桶坐垫圈,真正的马桶是“toilet bout”。“bout”在英语中是“一次、一回合”的意思,在法语中则是指“物体末端”。
然而,无论怎么修饰,厕所总是给人不雅的感觉。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人们总喜欢在厕所的门面上做文章。在这方面做得颇为到位的是我见过的这样一家餐馆。一进门你会觉得它有四间包间:都是一律的精制木门框,门框上方一块扇子形的金属牌上书写着包间的名称。离大门最近的一间叫“人缘居”,第二间叫“地盎园”,第三间叫“天游部”,第四间就是“洗手阁”。另外一个可做文章的地方是男厕与女厕的名称。我听说过有一个厕所内分“听雨轩”与“观瀑亭”。加拿大还有一家广告公司把内部的男、女厕所分别以一片枫叶与三片枫叶来标识。据说不会区分这两间厕所的求职者将被以“缺乏图形想象力”的理由被这家广告公司拒绝。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厕所的形象设计也许是出于对整个企业或活动的形象统一的考虑。在某一次纪念莫扎特的音乐节上,音乐厅的男厕所的标记就是莫扎特,女厕所的标记则是莫扎特的夫人。
其实,相比起厕所的外表,我本人更关心的倒是它们的内部设施。直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习惯:住进饭店后首先检查它的洗手间。但是,我并不想在厕所中增加什么烘干、冲洗之类的玩意儿,因为我不想把厕所变成一个制作间或是消毒间。我只希望那里地方宽敞、明亮,各项设施干净、齐全、简单、有效。在我看来,一所家居中的厕所理应像一个与你熟识多年的老友:没有更多的花饰,但能够理解、包容你的一切。
13与14
文 施武 图 王焱
《格调》这么一本消遣书差不多掀起了一场新土改运动,给人定成份。这主要不是说作者,作者不一定熟悉这种运动,而是指译者。本来人家叫《Class》,照直了译可能什么事也没有。谁是地主谁是资本家得看他是不是有地产房产什么的。你要没有一片地,谁也不会愣把你划成地主——土改也是有政策的。说《格调》这个译名是新土改,因为它不讲政策,完全是文化大革命的逻辑,它不讲出身,只强调表演性。你是不是地主有没有地被搁置一边,被虚化了,关键是你有没有一副地主的做派和玩意儿。一个演员演像了坏蛋,就被当成坏蛋来批斗。放在现在的形势下,你穿上贵族的衣服,就可以自我感觉为贵族了,还可以按“革命”的逻辑说:你背叛了自己那个阶级,走上了正路。
凡是运动,免不了夸张。在这种夸张的气氛中,刚挣脱了贫困,小康起来的哥儿姐儿,竟仔细检点起自己是否沾染了中产阶级的贱毛病,这就不好了,不仅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还给自己添麻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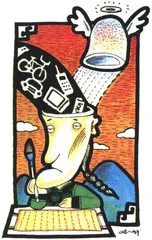
还是作者有点同情心,在书中专设了“另类”一章,给那部分追求高尚生活,又没什么经济实力的人指出了一条活路,多少让人喘了口气。一个社会不能让太多的聪明人自轻自贱啊!但是“另类”这样边缘状态让他这么一写,尤其是在“格调”的译名下,也被毁成了“某”一类,就显得没什么格调了,会臭了街。
Q原来是另类,自从看了这本书,尤其是“另类”一章,他就准备买一个最艳俗的床架把他那个被认为属于另类的床垫从地上搬上床架。后来他又改主意了。问其原因,他给我们讲了“13”的故事:
街边有一口井,井边有一个人天天围着井绕圈,口中念着:13,13,13……这一现象传到了科学家的耳中,深感其中必有奥妙,问及绕井人,发现他是个傻子,什么也说不出。科学家认定一定是井中有什么问题,傻子虽傻却可能有常人所没有的意识能力。于是,科学家来到井边,趴在井口,仔细向里张望。只听“扑通”一声响,傻子把科学家踢入井里,从此改口为“14,14,14……”所以Q说《格调》应该改名为《13》。 (本栏编辑:苗炜)
嗑瓜子
文 杨春燕 图 王焱
那日,一朋友的姐姐从日本回来探亲,临走,朋友想送姐姐点礼物,想来想去没什么特别的东西,于是想到了瓜子——那些袋装的简装的、被广告词儿说得香香的各种牌子的瓜子,为姐姐解离家后的寂寞,不是很好的礼物吗?可姐姐一听却笑了起来,说在日本这些壳类食品都是在宠物市场出售。什么?——听朋友向我转述此事,我有些愤愤不平——这日本鬼子也有点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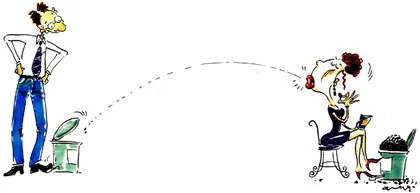
其实,我的这点愤怒只不过是从我的那点民族自尊心上冒出来的。实话说,我对瓜子从来就没什么好印象。我儿子曾有一口白而齐的美牙,硬是嗑瓜子嗑出了两个豁儿;再有,我是个常坐火车的人,每次看着乘务员拎着大扫帚把成堆成堆的瓜子皮扬得灰尘四起让我无处逃遁的时候,我都会由衷地厌恶起瓜子这种小食品。以至于,每当在公共场所看到一些人耸着肩侧着头聚精会神“咔吧咔吧”地嗑啊嗑的,我都会想起某种小动物。所以在听说日本人把这类食品归入宠物市场,还真有种他乡遇知音的激动呢。
我的这些想法可能有些偏激。人家书上不是说了嘛,壳类食品是美容食品长寿食品。公平地说,同一些人造的合成的小食品相比,瓜子一类食品确实是真正的“纯天然”。另外,天长夜短的,看个电视不吃点什么也真难熬。想想这些,觉得瓜子还是挺有功劳的。可是,有些事就是感情压理智——只要看到哪位,特别是那种衣着入时,形象尚可的男女站在汽车站,捧着把瓜子,目中无人地“噗噗噗”地吐着瓜子皮,我就无法不连人带瓜子地一齐烦起来,甚至会情不自禁地滋生出一种崇洋媚外的情绪——你瞧瞧人家美国人的休闲食品——玉米花,既天然营养又干净卫生,多好!可是这“多好”两字还没落地,脑子里就会又冒出了一句“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能让祖祖辈辈都嗑惯了“毛子嗑”(北方人对葵花籽的俗称。)的父老乡亲全都去吃美国爆米花吧——在我又一次地进入理智状态的时候,我清醒地意识到,我的围绕“瓜子的好处与瓜子坏处”这种理智与情感的冲突,一时半时是休不了战的,至于到底还要持续多久,只有天知道。
呆电脑
应明
电脑是个好东西,这毋庸置疑,但我仍不依不饶地对它有点意见。比如,电脑历来又聋又哑,它既听不懂人说的片言只语、自己也说不出像样的人话来。然而,这种情况据说最近有所改变,不能不令我跃跃欲试地想与电脑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对话。
先是在机器上装了个语音导航软件,想用口令指挥电脑做些基本的操作,如打开浏览器、播放CD、关机等等。一切准备停当后,我就想试试这东西是否管用,于是冲着电脑大声嚷嚷起口令,“打开文件”、“关闭窗口”、“保存页面”。不知什么原因,电脑好像根本听不懂我的口令,一点反应都没有。夫人和女儿见我粗着脖子对电脑穷叫,以为在发什么毛病。等她们弄清了原委,也兴致勃勃地对着电脑嚷起来。你还别说,有那么一两次电脑还真听话,竟照着她们的口令正确无误地执行了。我心里直怪这家伙重女轻男。弄了半天始终不能稳定工作,我也就再没有脾胃折腾下去。将这个什么导航系统卸去了事。我不是斯蒂芬·霍金,双手灵活得很。敲敲键盘或动动鼠标就能轻易完成的活犯不着跟电脑多费口舌。
后来又试语音输入,用一个市面上很火的软件。先装了个识别英文语音的,不料效果不好。我总认为我的英文发音虽比不得纽约人纯真,但在国人中也算是好的了,而电脑听不懂我说的英文对我的自信心实在是个打击。但转念一想这东西或许只适合老美用,我等用个中文的语音识别软件总不会有问题吧!谁知一试之下仍算不得理想。我说的不少句子它记倒是记下来了,但错误百出得让人不忍卒读。更好玩的是,如果你对电脑读一篇报上的社论或领导发下的文件,它倒能听懂个八九不离十;而你要是读上一段富有特色独具风格的文字,别说是子曰诗云,就是鲁迅李敖钱钟书,它也多半会觉得你不知所云。这不得不让人疑心建这语言模型的人一定是久经社论文件熏陶的国人。
由此断定,电脑即使算不得聋子也至少仍属听力不济。这恐怕会影响到说话。不知电脑是否也一样依旧哑口无言。为了验证这一点,重新装了个软件。这个被称作“读书伴侣”的东西竟能将任何文本用机器语言朗读出来。这多少让我有点惊喜。尽管机器语言听上去机械呆板、了无生气,平铺直叙、缺乏变化得使人昏昏欲睡,但不管怎么说你几乎能让它为你朗读你想听的一切。毕竟当屏幕让你的双眼疲劳不堪的时候,让机器帮你读读其中的东西也是一种休息。我现在就常这样,每每写就一段文字,就让机器读给我听听,看起承转合是否顺畅。但我担心听多了这种机器语言,会不会平日里说话也带上电脑的腔调。 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