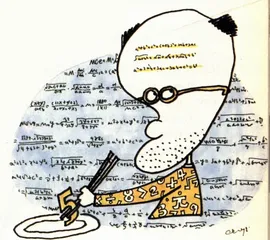生活圆桌(7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布丁 刘怀昭 施武 应明)

省钱
文 布丁 图 王焱
有一年春节,我忽然感到有必要给自己买套西服穿,我带着长辈给的压岁钱和单位发的年终奖金,准备去买一套观奇洋服。
去商场之前,我鬼使神差地去了趟王府饭店,结果见识了一下“范思哲”,那儿有一件西装上衣,极漂亮,导购小姐跟我说,喜欢可以试穿一下,我知道那东西贵得吓人,试也白试不如免了。掉回头再去商场看我的观奇洋服,却怎么看怎么觉得不好看,索性不买了,把钱存入银行了事。
我之所以认识观奇洋服这个牌子,是因为我看香港电视剧看多了,香港人似乎酷爱穿西装,电视剧里什么人都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电视剧结尾时总要打一串字幕,说哪几位演员的衣服是由观奇洋服提供。我想,买件这样的西服就行了,还算体面。除了看香港电视剧,我还有一个爱好是翻外国画报。尤其留意其中的照片和广告,这是因为外国字我认不全,所以对图像更敏感。从中我认识了一种瑞士手表,名叫“TAG HEUER”,一见钟情这个词儿不只是说男女之事,我跟TAG HEUER手表就是一见钟情,老想把它搞到手。这种手表在北京城也有卖的,17000块钱左右,我买不起,但买不起也有好处,因为我不会退而求其次去买别的便宜的手表,这也省了钱。
后来我总结,看了范思哲就不买观奇洋服,看了TAG HUNER就不买天梭飞亚达精工卡西欧之类,是个省钱的好办法。比如有人问我为什么不买辆车,我就说,美国军用吉普Hammer不错,比什么切诺基或北京吉普212强,要买就买Hammer,所以不能随便买辆车。
这么说自然透着一股对生活孜孜不倦的追求劲儿,实际上却是从根本上泄了气。咱们怎么折腾都过不上梦想中奢华的日子,索性破罐破摔,穿条板儿绿裤子瞎混吧。我岁数不小才明白这么个道理,说起来真他妈害臊。
(本栏编辑:苗炜)
夏日观察
刘怀昭
加州今夏的高温,直逼百年来的最高纪录。据我观察,这盛夏期间人们过周末的去处大致有三。
其一当然要数加州得天独厚的海滩。沿太平洋高速公路一线,接天壤地的碧海白沙,海风刺骨,沙烫燎脚,直教人一头扎到浪里才痛快。这一带比较著名的海滩当然要属马里布和桑塔·莫尼卡的了。其中马里布海滩因为常有好莱坞的人出没,所以老百姓强烈要求检测一下水质,怕跟着沾上爱滋病什么的。有关部门还真煞有介事地去测了各种指标,公之于众告知没事,云云。
太平洋海岸线那么长,人们却偏爱扎堆儿,据我观察,消暑倒在其次,主要是为了看人,并被人看:看人家(或被看)踩着冲浪板在浪尖上跳舞,看/被看胸部及胯上两抹阳光色调的布头儿。如果还嫌看/被看不够的话,还可以去圣迭各的“天体”海滩。在那里,看/被看的规则是明白无误的:不脱个精光不许光顾,连叫卖的小贩也不例外。总之,到海滩上消暑的属于彰显个性的一群,因此,据我观察,这里的人基本上属于45%那部分人(据报载,美国人已有55%偏胖)中的中、青年人口,也就是人们心目中的美国人形象。
夏日周末的第二个好去处,据我观察,便是遍布各区大大小小的图书馆、博物馆,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足够你在那儿消磨掉一天的好东西。耗到关门时,还可以免费借它十盘八盘CD、录像带回家继续消受。不过最妙的还是逛书店,在Barnes & Noble和Border's这些书店里摆的东西,除了借不走,好像随便你怎么样。我曾在洛杉矶市中心的Border's 书店的咖啡座里见到一个大胖子,盘腿坐着,一边搓脚丫儿泥,一边翻看戴安娜逝世一周年的精美纪念画册。他前面桌子上有一杯插着吸管的奶昔和一个只剩下点心渣儿的碟子。
至于第三个消暑的去处,就是呆在家里那儿也不去。这是一连几天电视天气预报之后的忠告。但据我观察,肯听取这个忠告的多半是年迈的那部分人。对此我并没有机会上门查访,因为在美国,除非人家正式邀请你,是断没有串门儿这种事的。我知道左右的邻居开什么车却不知他们长什么样——大家都是开着车从自家车库里钻出来,开着车驶进自家车库里去——那么我的观察从哪里来呢?当然还是电视上,据报道,今夏本地颇有两三个老人热死在家里。被采访到的死者邻居震惊之余说,根本不知比邻而居的是个老人:“否则打个电话去探望一下也好啊!”问题是谁也不知谁的电话号码。其实政府和各种民间服务机构早就面对社区职能逐渐解体的事实,并不寄希望于邻里之间守望相助,因此通过各种渠道广而告之,要独住的老人一有不适赶紧拨911。但据我观察(还是从电视上),老人们多不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饿狗
文 施武
在我刚开始读小说的时候赶上了那段什么书都少见的日子,搬了几次的家更是什么书都见不着了。偶然地在一个经常上锁的抽屉里发现了一本单行本的《哈姆雷特》,我像无头苍蝇一样逐字读了一遍。我记得那里全是繁体字,尽是不认识的,读着极费劲,而且好像不是哈姆,而哈孟雷特,是田汉译的。多年后跟一个学中文的姐们说起来,她说我一定是记错了。我后来把那本黄澄澄的《哈孟雷特》拿给她看,她才给田汉加上了这个功劳。那时候人好像多了一种嗅觉,能嗅出哪儿有书,自从找到了《哈孟雷特》,以后的日子居然能时不时翻出本书来。在学校里,哪个老师有书又肯借也能嗅出来。《战争与和平》就是一个语文老师借给我的。那天放学后,我把书包里的书本都塞进课桌,然后背着空书包进了办公室,像等着挨训一样站到了老师办公桌前,其实这是为了挡住别人的视线,这时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书塞进我的空书包。我忘了我是怎么走出办公室的,也忘了怎么和这位老师接上头的,更忘了我是怎么跟他商定妥的。
在信息匮乏的时候,人会像狗一样耳聪目明,尽管如此,食物太少还是免不了挨饿,成天像只饿狗。
突然之间,信息多了。你不仅能读很多书,还能知道作者的小名,或是否同性恋;不仅有很多电影看,还能知道那里面的女演员离过几次婚。还没等你想明白你想知道什么,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就快把你撑死了,这时我们很难保持狗一样的耳聪目明,因为胃口已经坏了,给什么都一样了,不饿死就行了。
《死屋手记》里的苦役犯在蹲了10年大牢后令他极为感叹的一点是,在这10年间他没有一分钟的独处时间。一个人在10年间没有片刻独处,这和10年间没见过一个人影相比,不知哪种情景更可怕。
在眼前的信息盛宴中,挑食可能是一个不坏的毛病,只是变得比较困难。难得我的朋友B小姐仍然有那么好的胃口,无论哪个名牌服装发布的信息,她都有雅兴一一道出,细微的变化对于她仍然是津津乐道的信息。我免不了想到第欧根尼见到衣着讲究的雅典青年时说的话——装模作样。另一些长发蓬乱、破T恤毛裤角的人就像古希腊的斯巴达青年,第欧根尼见到他们的打扮说的是“更加装模作样”。
在所有事情都以信息形式被充满时,活出个人样可真不易。
数学人生
文 应明 图 王焱
一切做学问的专业人士中,我最崇拜的莫过于数学家了。个中原因主要是:我仔细琢磨过了,如果让我改变现在的职业,不少行当我立马就能履新。比如说做官;另一些工作我努力也能胜任,比如说当个足球裁判什么的。但要改行当个数学家我就是用尽吃奶的劲恐怕也当不了,想要滥竽充数地混混也肯定混不下去。人对自己达不到的目标总表现得要么是不屑要么是神往。在我通常取后者,因为这比较本份。
当然还有另外的原因:小时候颇喜欢数学,也自觉有一定悟性。在班中做个数学课代表是家常便饭。当然,现在看起来,当时的数学教育很成问题。缘故是“文革”之中,一切知识都被打上“活学活用”的烙印。使得数学课上的代数几乎都是做计算亩产和钢产量的应用题,而几何又成了机械制图的代名词,我至今仍记得画过手扶拖拉机的什么凸轮。由此对数学一直很隔膜,也很偏狭地认为全中国的数学家可能都在算亩产或是画拖拉机。
是徐迟先生的《哥德巴赫猜想》改变了我对数学和数学家的看法,也第一次知道了我们还有陈景润那样杰出的数学家。自此之后,数学的纯洁、干净、明白,可以证明对我来说均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不消说也蕴含着一种独特的力量。
在我眼里,像陈景润那样的人是幸福的。您想想,终其一生从事一个问题的研究,心无旁系,其投入和陶醉绝不是旁人所能感受、也不是旁事所能比拟的。而没有什么值得投入、没有什么可以陶醉正是眼下许多人生活既富足又不幸的根源。另外,陈景润的一生无论如何做成了一点事情,其“1+2”证明是举世公认最逼近“哥德巴赫猜想”的伟大的成果。而至他辞世时这一问题也未能得到解决,在我看来也不坏。他可以带着它去和哥德巴赫本人甚至与上帝讨论了。如果我今天死掉,我就想不出能带什么问题去难难上帝和众多先贤。
甚至安德鲁·韦尔斯在这一点上也比不得陈景润。费马大定理在折磨了众多数学家三百余年后终于遭遇了克星。韦尔斯自10岁上初次知道这一著名难题后,孤独地潜心钻研30年,最终一证而闻名于世。一方面,这个刚过不惑之年的英国人可以如释重负安安稳稳地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他的数学了,但另一方面我也实在担心没了费马大定理可证,他是不是会闲得慌。使他的余生显得一片苍白。
数学家还有一个吸引我的地方值得一提,您就是想破脑子也想不出证明了费马大定理或是哥德巴赫猜想能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会给数学家带来什么实际的好处,甚至并不能保证他们得菲尔兹奖。而正是这种不计成败、不计功利、一门心思要证明自身智慧的做法算得上是一种最干净的生活,在浮躁、喧嚣、急功近利的今天显得尤为难得和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