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52)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吴宏 田七 施武 布丁)
屋里堆满了书籍
吴宏
几年前,读过余华的一篇小说,名字叫作《西北风呼啸的下午》。这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而其中的一句话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中。小说中的主人公被一位陌生的来访者指责为“卑鄙的小市民”时,主人公说道:“我不是什么小市民,这一点我屋里堆满了书籍可以向你证明。”这句话算是说在我的心坎上了,因为我的屋里也堆满了书籍。
有不知内情的客人来我家,看到屋里堆满的书籍总以为是父亲的,因为父亲退休前是在一个名为研究所的单位工作。我向父亲指出,冒充光辉的形象是不对的。后来,遇到产生误解的客人,父亲会解释一句:“这些书都是我儿子买的。”但,我又发现,客人们又会误以为书是我弟弟的。可能是弟弟戴眼镜的原因。一个人戴眼镜好像并不只是说明他近视,似乎还能说明他读了很多书,很有学问。每当遇到这种情形,我就会有一种被伤害的感觉。
一天,弟弟新认识的女朋友第一次到我们家来作客。之后,弟弟对我说,在送女孩回家的路上,女孩说他感到我们家里堆满的书籍很吓人,并担心今后他们会不会有共同语言。弟弟赶紧申明,那些书不是他的,他很少看那些书。我想,吓人之感可能来自书架上那些《某某主义》、《某某论》和《某某学》之类的书名。想不到书籍竟会使女孩产生这种恐怖的感觉,这也使我从某一种梦想中惊醒。
有一位长辈在参观过我屋里堆满的那些高深莫测的书籍之后,建议我适当地读一些琼瑶的小说可能会对我有些好处。她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觉得我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倾向,读一些浅薄的东西可以减少一点这种倾向。当时我不以为然,现在想来还是有点道理的,可能所谓的解构主义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我对弟弟说,今后如果有女孩问我这种问题,我就说这些书都是你的,我从来都不看这些书,以免把人家吓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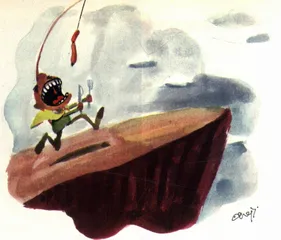
滋味
文 田七 图 王焱
对生活认真的态度也会体现在吃东西的方式上,有一句话叫“活得有滋有味的”,就把活着和吃联系得很紧。
我的家乡有一家小店叫“鱼头店”,店里卖以鱼为原料的各种好吃的菜。最著名的“白浇熊鱼头”端出来就叫人食欲大开,它的半边鱼头已经把一个大盘遮满了,鱼头上再浇满了红椒沫白姜泥。还有用“划水”(鱼尾)和鱼鳔做的菜,必须预订才能吃得着。这样的菜馆在其他地方少见,我也觉得“鱼头店”是可以为我这个地主脸上添彩的好东西,每逢有朋友来我总是首先介绍它。
在长沙,那里朋友的绝招是拉我去吃一种叫“黄丫叫”的小鱼。这种鱼没什么特别,但吃的方式很特别,因为吃的地方在那块著名的橘子洲头。每年夏季涨水的时候,橘子洲头的很多地方都要被水淹没,所以那里的饭馆并不是常年开张的,而且开店的也不是专业饭馆,而是当地的居民。这样,一桌客人来到,一般就要4斤“黄丫叫”,其中两斤红烧,两斤炖汤,就着自己带的酒和长沙的酷热的天气,客人可以吃得痛快淋离。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吃“黄丫叫”的地方并不通公共汽车,也很少有出租汽车等候。所以吃客一般都是自己开车来。这样,到橘子洲吃“黄丫叫”的意味就很丰富了,不但有美味,野趣,还隐隐透着一种让人仰恭的富贵劲儿。
这几年北京的名食有一个明显的脉络:从1994年的酸菜鱼、到量大味重的东北大菜,到河南的红焖羊肉,到上海本邦菜。虽然“本邦”意味着什么意思很多食客并不太明白,但上海菜显然是精致和偏高档的意味,一盘黄泥螺要卖到几十元,人们感叹生活真是越来越好啦!
不料今年下半年风向一变,北京街头不知何时兴起了吃四川名小吃“麻辣烫”,一时街头和麻辣烫专门店遍地开花,受到市民的极大欢迎,原因很简单:一二块钱一串的麻辣烫一人吃花不到20元就管够,味道又绝对刺激。
这一个轨迹如果用一条曲线来表示的话,真像是股市:上海菜处于峰顶,突然跌人谷底后,麻辣烫就来得正是时候。生活也变得低档了。
所以有人趁此推出吃“国宴”大餐。什么是国宴呢?据说不过是川菜少点儿麻,南菜少点儿辣,但名字却叫出了老板再创食业牛市的决心。
这是叫我怀疑的地方,这么追求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因为有个对吃极精通的朋友前两天告诉我说,目前北京味道最好的“鱼香肉丝”出在功德林,那个只做素菜的饭馆。而我呢,虽然饭量不大,但吃起来却象饕餮,并且顿顿要有肉,缺了不行。
游戏的乐趣
施武
老张生了个儿子,胖胖乎乎看不出什么特点,两个月之内老张以及所有家人朋友都没有发现这个胖小子有什么特别的天份。这其实没什么奇怪,他再是个神童也不至于在出生两个月就急着展现吧!可是老张很着急。因为他没法给儿子起一个一辈子都适合他的名字。两个月来,老张盯着儿子,盯着字典,企图在“张”字后面缀一个出奇点的字。后来他天眼一开,在解构主义精神指导下,悟到:名字,符号也,根本用不着因循什么,于是,他那胖儿子就成了“解X奔”。没人能懂老张这意思是什么,这倒也不要紧,可是“他怎么不姓张?也不姓妈妈的韩”?老张答:“姓是什么?游戏而已。”这意思我明白,姓不是天定,人类先民都没有姓,只不过是人定一种命名规则而已。
话虽有理,可是凡人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天定的规矩。除了温饱大事以及由此导致的科学、政治、经济中的规矩由天而定,什么不是游戏呢?
一天天挣饭的日子之所以能让有高级智慧的人还能过下去,并且还得过得有点滋味,游戏是一个少不了的动力。玩游戏就得守规则,我从维特根斯坦的书里懂得了“followingarule”的重要性。
体育比赛之所以好玩好看,绝不是因为它是天定的,或多么性命攸关,而是因为它是游戏。一场篮球比赛中,球员在相关的规则中玩,如果你眼看对方球员举手就要投出决定胜负的一球时,你忽然从裤兜里掏出一张扑克牌中的“大王”甩将出去!不管你自己得意不得意,这不仅压不住人家的球,而且会认为你那“大王”是垃圾。你要是老这么干。就不会再有人跟你玩了。
给小孩起名字当然也可算是游戏,正因为它是游戏,并且有相关的规则,所以才会父母们煞费苦心,才会有名字的“好听不好听”之别。
老张给他儿子起的名字,由于不守规则,所以没人再去认真对待,因为它无所谓好不好了。由此我又想到女权主义(时髦的说法是女性主义)的一些抗议,与老张有殊途同归的毛病。女性主义对妇女权利、地位等人性方面对大义的申明是文明的进步,但是由此把很多游戏性质的行为也看得与大义相关就没劲了。比如Ladyfirst规则,它并不真的指向一切领域的Ladyfirst,也不足以表明男性对女性的尊重或小看。动真格的尊重或歧视一定发生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日常行为中的Ladyfirst大不了是一种性别游戏。男女毕竟有别,别就别在性别上,天地造化,性别之间要相互取悦。取悦的游戏不指向婚姻,婚姻是两性之间的人性结婚,或政治、经济,或别的结盟。取悦是性别之间的游戏,游戏就得有规则,Ladyfirst就是一个规则,还可以有别的规则。
如果把游戏中的规则看得过于严重,游戏就被取消了,性别游戏被取消,性别之间除了性行为之外,就没有区别了。其实,服装有男女之别,发式有男女之别,首饰有男女之别不都是游戏规则吗?连小鸟都会在异性面前乍乍羽毛。人在温饱问题解决之后,吃饭之所以还显得有趣,要归功于“到哪儿去吃”,“和谁一起吃”等游戏内容。(本栏编辑:苗炜)
读游戏攻略
布丁
早两年,我酷爱电脑游戏,如今却很少玩了。但每周都会买一份游戏报纸,每月都会买两本游戏杂志,阅读刊登在上面的游戏攻略。
古人云,作文当如行云流水,行其所当行,止于其不可不止。古人还说,作文要言之有物。游戏攻略符合这两条要求,讲的是怎样打通一个游戏,自然是言之有物,作者在文中大谈其游戏感受,胡乱地发议论,自然乱云横飞落花流水。
本来,我觉得游戏攻略该算是一种新文体,可想起李渔的《闲情偶寄》,才明白此类文章早就有。只是人家李渔当年可玩的东西多,能讲究房屋设计能排戏能种花等等,把生活中的游戏写成文章,“口之能言者,物也,非尤物也”。还有一些更好玩的事,他肯定没写。
现在的生活比起李渔那时是不是更无趣了?我不知道。但如果让我选,是只玩电脑游戏,还是找一帮姑娘唱戏、摆弄家里的古玩等等勾当,我还是挑后面这花样儿多的。因为它热闹,有别人参与,不像玩电脑游戏时那么孤独。
思想家说,现在的社会让人越来越孤独,这一点我深有感触。早两年,我打电脑游戏时,常要跟别人交流该怎样过关,向人讨教一些游戏的技巧。那阵子,游戏媒体不如现在发达,夜里打着游戏,忽然有电话来说“那个洞里有个大怪物,该怎么对付?”等等,心中顿时有股暖意,茫茫黑夜,有人跟你面临同样的考验,有人跟你想着同样的问题,那种交流的温暖虽然只是个“虚拟空间”中的事,却也能消减几分现实中的苦闷。
如今,这种事不再发生。无论你打哪一款游戏,都会很容易地在报纸上找到它的攻略。你没必要问别人什么,买份报纸或杂志,对着电脑打,遇到问题就翻出来按照人家的指点玩下去就行。如此,电脑游戏就变成了个更孤独的事。
我相信,信息社会越发达,人们的交流就越简单。(从这一点上看,网络游戏今后肯定会缓解一大帮人的孤独感)。
记得早两年我打电脑游戏时,也想着能有份报纸,刊登各种游戏的攻略,那样会方便许多。信息的发达或许正出于人们渴望交流的要求,然而,它一下让你特满足,事情就索然无味了,因为这时双向的交流已变成单向的灌输。
我接受这种灌输,阅读各种游戏攻略,并试着把这阅读当作一件最有趣的事来做。可惜,我很少再打游戏。因为其中那可怜的一点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不复存在:你对着电脑打游戏,翻着报纸找攻略,没必要再问谁“哪儿有怪物?怎么过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