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44)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纪志仁 黄侯兴 杨汉民 贾抒 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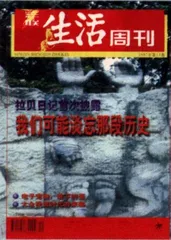
回头看日本侵华史,可怕的确实是我们自己的麻木与遗忘。一个忘记历史的惨痛,忘记曾遭受过耻辱的民族,实在难以在历史发展中崛起。
南京纪志仁
高考制度亟待改革
编辑先生:
近日大报、小报都刊载着今年高考的日期:7月7日至9日,北京最高气温达34—36摄氏度。可以想见,这3天,全国有多少考生将要在考场内忍受酷热的煎熬!这对于考生及其家长来说,简直就是一次无谓的折磨。
记得1956年我在北京参加高考时,也是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走进考场,汗水如注,刚打开语文试卷,鼻血就流出来了,鲜血把卷纸染红了一块。我一手用手帕捂住鼻子,一手答卷、作文,真是苦不堪言。考场外停着一辆救护车,这3天内不知运走了多少昏厥过去的考生。我虽然坚持下来,但到最后一天,也头晕目眩,走出考场,已经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闷热的夏夜难成眠,考生在这一段日子里紧张地复习功课,睡眠更是少了;待到面临考期,已经疲惫不堪,精力消耗殆尽,即使平日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也难于得到正常的发挥。
据说,为了应付高考,现在一些家长想出了种种法子来磨炼自己的孩子。例如,为着适应考场内的高温天气,孩子在家复习时不准许开空调;为着保证夏夜的睡眠,晚间不准孩子吃西瓜,以防尿频;为着保证孩子全身心复习功课,停止了全家一切娱乐活动,包括看电视;一些郊区、县远离考场的考生,有的家长还要求孩子每天坚持一小时在烈日下骑自行车,以“锻炼耐力”等等。这些“磨炼”,比上战场打仗,还要显得严酷和无情。
自新中国成立迄今近50年,伏天高考,年年如是,循环往复,不知多少悲剧从这里发生。为什么不可以加以改革呢?日本等许多发达国家,早已改为秋季高考;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已改为春季高考。在这方面,我们何不吸取他人成功的经验,多给青年学生一点温馨呢!
为着青年学生的身体健康,为着考生在考场上能发挥出正常水平,我建议我国教育部门考虑,把新学年改为春季,高考也改在春季举行。我相信高考制度是可以改革的,改革是会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拥护的。
北京黄侯兴
谁来医治教师心病?
编辑同志:
读完贵刊的《谁来医治“灵魂工程师”的心病》,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或许因为我也是教师,也是文中所说的教师吧。文中以科学方法得来的事实,我深信不疑。但“心病”从何而来,我忍不住也想说几句。
我在农村初中当了15年教师,对此深有感触。社会衡量学校的唯一尺度是升学率的高低,对一所普通初中来说,标准就更简单了,只看学校有多少学生考取重点中学。而大多数校领导竟也顺应社会(或者是出于无奈),大力试行应试教育。他们在学校管理上,以升学率为中心,集中精力抓升学考试的科目: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放松了历史、地理、生物、音乐、体育、美术等的教学。把学生考试的分数与教师奖金挂上钩,分数也是教师评优、评先进、晋升的重要条件。我班的学生考试分数比你班高1分,比你班高一个百分点,我的教学水平就比你强。
在这样的氛围中,教师为了争取那不至于使自己丢面子的奖金,只得舍其他面不顾,逼学生出“高分”。教师们便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使出各路招数,甚至使出绝招。有的罚学生抄写作业,极端者罚学生把词语或公式抄上百遍;有的教师恨急了就体罚学生,一不满意就是一顿棒喝,此类也有恶性事件见诸报端;有的教师就发挥嘴上功夫,轻者只企及学生本人,重则连累学生家人。这样的非正常教学行为虽然不是经常发生,但频率也可以。
为了逼学生得好分,教师加班加点,现在星期天不允许上课,就延长每天的在校时间,学生从早晨6点多踏人校门,天将黑才能回家。诸如活动课、劳动课、班会课等,只是课程表上的一种摆设。学生百分之百地变成了考试机器。
这是病态的教育、畸形的教育,深受其害的又何止是教师呢?在两班的工作环境里,教师又怎么不会得心病呢?那么“灵魂工程师”的心病准来医治呢?仅靠尊重、关怀是远远不够的。
教育本来就不单是教师的事,而是全社会的大事,是国家的百年大计。要医好教师的心病,也只有改革教育体制,只有靠强盛的国力。国力强盛了,教师的心病也就医好了。教育走上正规了,中国也就不愁不会富强了。
江苏无锡县杨汉民
“手拉手”方式好吗?
编辑先生:
社会上“手拉手”活动搞得很热闹,发起者希望在捐助困难儿童的同时,使城里面的“小皇帝”们受到教育,出发点当然是很好的。
但我在是否让儿子参加这种活动时却有些顾虑,当然不是经济方面的。每当在电视里看到这两种生活境遇完全不同的小孩手拉手在一起时,我总是觉得心里很难过、很别扭。这种友谊有些不自然、不平等。我很怕捐助的一方会产生优越感,更害怕接受捐助的一方会感到压抑。对儿童来说,心里的失衡难道不是比物质上的贫困更可怕,更让人难以接受吗?
每学期儿子总要找些八成新的书交到学校,由学校统一捐给困难地区,我觉得这种方式更好一点,何必要知道帮助的是谁呢?换个角度说,如果我是个家庭困难的孩子,一定更愿意接受学校发下来的书,而不愿轻易接受什么“小恩人”的帮助,更不愿意有那种比较的尴尬和依赖的幻想。
各种机构和基金会是否可以再想些其他办法呢?比如提供贷款。接受贷款在使人得到机会的同时也得到了压力和动力,更容易激发起人们强者的自尊和自信;而接受捐赠多少会使人感到弱者的沮丧和无奈。
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下一代人的心灵是我们必须加以小心呵护的,来不得半点轻率。怎样才能使生活优裕的孩子懂得帮助他人、尊重他人;怎样使生活贫困的孩子在得到学习机会和经济资助的同时不伤及心灵的尊严,这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不知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有什么更科学、更合理的建议?
北京林业大学贾抒
“光污染”和“专家们说……”
编辑先生:
近年来,一种新的论证方式却越来越多地见诸于报端或电视广播,这就是引用“专家们说……”来证明某种立论。试举一例:前不久,中央电视台在配合世界环保日编播的一条新闻中,引用了据说是某些“专家”对于新型建筑物上采用玻璃幕墙造成的污染的一些观点,读来颇感新鲜:
其一,说是由于玻璃幕墙反射阳光,会使附近的建筑物受到额外的照射,室内温度将会因之升高。从原理上讲,此言不谬,因为太阳能的一种利用方式即基于此,也许幕墙在夏季造成“热污染”以后尚能在冬季帮邻居节省一些供暖费用作为补偿。不过如果人们从量化的指标上来细抠一下,就会对由这些玻璃板随机反射的不断变化角度的太阳光线,是否真能在一座固定的房屋内造成人们所能察觉的温升(据说有4摄氏度之多)顿感怀疑。
其二,说是根据光学原理,那些凹形的玻璃幕墙会使太阳光聚焦,从而有使焦点处的物体燃烧并引起火灾的危险。如果这条新闻为此配发的下一个镜头是用一个凹面镜而不是凸透镜聚焦点火的话,可能这种形象化的说明将能更清楚地表达上述意图。但画面编辑上的这点小小的失误比起“专家”们给我们开的玩笑来说就算不了什么了。众所周知,只有旋转抛物而才能把平行光线精确地会聚到一个点上,即使是球面镜也仅能形成一个光斑。而这些“专家”却要我们相信,以建筑施工的精度安装在大略为圆柱或圆锥凹面上的一些透光或半透光的玻璃板,竟能形成一个是以汇聚太阳光点燃什么东西的精确焦点!
如果说,以上两条尽管离谱,但还算沾点物理学定律的边儿的话,那么下一条可就更有想象力了:说是在茶色玻璃板中,含有某种放射性同位素(姑且信之,此处不议),由它们制成的幕墙反射的太阳光,就会把这种放射性带到四面八方去造成广泛的污染。这可太恐怖了!如是,这位“专家”关于光量子能够携带放射性物质的伟大发现,不仅大慨能成为新一代高科技武器的理论基础,而且肯定会获得诺贝尔奖金。可惜的是,这样的立论却只是毫无事实根据的信口开河,用之连初中物理课都考不及格。
现在许多媒体都正在为社会上“科盲”之多感慨不已,又都在对各色伪科学愤慨有加。请问,提出和在电视节目中播出上面这些“光污染”妙论的“专家”和编辑们,究竟是属“盲”还是姓“伪”?
对于玻璃幕墙这样一种事物,人们尽可见仁见智地从城市美学乃至反腐倡廉的角度上讨论它们是否会带来“视觉污染”或“精神污染”。但如果真要从物理学意义上探讨“光污染”之类的课题的话,在“大胆地假设”之后,千万可别忘了还得“小心地求证”。因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我们还是老实一点吧!”(引自《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801页)。
清华大学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