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在别处:天外有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刘怀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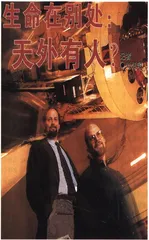
发现类地行星的天文学家马西和巴特勒
“生命在别处”(Life Is Else-where),米兰·昆德拉在解释为什么给他的小说起这样一个书名时说,这种表达是一种诗意的抒情,而“抒情诗般的态度是人类存在的基本形式之一”。在他这部小说中,还有这样凄美哀婉的句子:“在晚霞褪去之时,一切都辉映在乡愁之中”。
饶有意味的是,很可能要不了多少年,“生命在别处”这样的表达就与诗意无关了,它可能会成了另外一本新书的书名一一这本书非但不抒情,连科幻也算不上——书中会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一个硬梆梆的事实:天外有人。
这种说法已不算耸人听闻。本世纪以来,随着关于UFO(不明飞行物)扑朔迷离的传闻,“外星人”一直是科学幻想作品的主角。近几十年来,随着人造卫星和登月火箭的成功发射,天文学家正在一步一步地丈量出现实和幻想的距离。今年一月中旬,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杰弗瑞·马西(Geoffrey Marcy)和保罗·巴特勒(PaulButler)公布了一项新的太空探测成果,从而把一项迄今尚在理论探讨和假设阶段的课题一下子引入了伸手可及的事实论证范围内。在此之前,尽管有科学家们经年的苦心监测,尽管人们一直不懈地洗耳静候着来自域外的微弱的电波信号,尽管围绕着人类的所来所之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有着种种神学和世俗的纷纭争议,却一直没有什么具体的科学根据来挑战这种认识,即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我们人类创造的文明以及我们的生命形式在宇宙间是独一无二的。
“那儿有人吗?”
1996年1月,美国天文学会(American Astronomical Society)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召开了会议。当杰弗瑞·马西和保罗·巴特勒出现在会场上时,全场鸦雀无声。几天来,天文学界一直在风传这两个人将在会上抛出重大新闻。终于,马西走到麦克风前宣布:“我们到这里,来宣告我们发现了两颗新的行星,它们绕着类似太阳的恒星沿轨道运行。”
实际上,人类已不是第一次发现类似的行星了,但这一次马西和巴特勒的发现有些不同寻常:这两颗新发现的、尚未及命名的行星的表面温度足以使水以液体的形式存在。根据我们目前所知,姑且不论生成生命的必要条件都有哪些,其中液体形式的水的存在是绝对的先决条件。
马西和巴特勒的观测是在俯瞰加州硅谷的里克天文台(Lick Observlatory)进行的,这里具有世界上最先进的分光仪。去年10月,这两位天文学家就曾在此验证了瑞士日内瓦天文台对另外一颗绕类似太阳的恒星运行的星体的观测。这颗行星在45光年以外的飞马座。该行星的表面温度高达1300℃,因此不可能有生成生命的液体水环境,但它证明了类地行星存在的可能性。马西兴奋地回忆说:“当时我有点精神分裂的感觉。虽说我们让瑞士同行抢了先,但还是充满了幸福感,因为它预示着我们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世界就要被我们发现了。”他和巴特勒不仅深信类地行星的存在,而且立誓要做发现类地行星的第一人。他们立即投入了紧张繁杂的观测和数据分析工作中,为此专向同行借用了价值10万美元的计算机装置来专门重新检索8年来的观测数据。去年12月30日,当他们根据数据提示将注意力投向日后的发现的时候,巴特勒回忆说:“我兴奋得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马西和巴特勒新发现的两颗行星便是他们一直苦苦寻找的有生命生成环境的类地行星。
这两颗星体远在35光年以外的大熊星座附近,最快的火箭也需数百万年才能到达;如果那里果真有某种文明的生命形式存在,并愿意对我们的探索有所回应的话,也要等上往返共70光年的电磁波传递。马西和巴特勒尚无法对这两颗行星作较为清晰的观测,但他们的数据分析表明,“上面不难有雨水和海洋的存在。”
马西和巴特勒的宣告将改变天文学的进程。事实上,这一发现已激发了新的寻星热。不久前,美国哈佛大学启动了名为“10亿波道地外文明信号”的探测工程,利用3架射电望远镜在氢谱波段内进行大宽度扫描,以期能够接收到来自太空的智能信号。在马西的讲话过后,美国宇航局的官员丹尼尔·高尔汀随即宣布了一个新的太空探索项目,其目的“不仅是监测,还要在25年内获取类地世界(Earthlike worlds)的清晰到能分辨海洋、山川、陆块的图像。”
至于那两颗行星是否确有生命存在,目前的科技尚不能给出一个完满的答案。这两位科学家勾勒出的这两个新世界主要气体构成有硫化氯、氨、沼气等有毒气体,而水虽以液体形式存在,却温度高到可以用来沏茶。因此,如果上面果真有生命的话,当与地球上的情形迥乎不同。据马西分析,这样的生命形式应该是一生、世代处于悬浮状态而不接触“地”面的。到底这样的生命形式离奇古怪到了何等程度,实在超乎人的想象。这难免让人联想起科幻小说中外星人通常被描述的情况,如我们在科幻电影《外星人》(E.T.)或《领航员》(Navigator)中看到的那些,大都摹仿人形,顶多面目可怖些,但总的感觉是如出一辙。地球上唯我独尊的人类难以想象出其他种类的文明社会形态会是怎样。
无论如何,既然已在太空中观测到了承水行星,那么对其它生命形式的有无的回答就是早晚的事了。目前,天文学家已把自己的研究聚焦在更进一步的奥秘上:类地世界在哪里?得克萨斯州圣安尼奥的天文会议一结束,天文学家便纷纷回到自己的望远镜前要看个究竟,并又开始在计算机里翻检那些陈年的数据了。他们翘首期待着1997年在哈勃望远镜上安装一个新的红外摄像机,以便配合旨在25年内获取类地世界清晰图像的项目(该项目命名为“原初”)。
人类需要重新定义自己?
为什么人类会着迷于异域生命的存在的可能性?探索地球以外的生命实际上是对我们人类自身的探索,它将帮助回答这样一些亘古之谜,即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在这茫茫宇宙间的位置是什么。这样的困惑一直萦绕着人类文明进程的始终,比哲学本身更古老,成了各种神话的起源。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地外文明的发现不仅会刷新我们的自然科学认识,也将改写我们人类的宗教、我们的信仰体系、以及我们全部的世界观。
其实,当我们回首时,会惊讶地发现这样的事实:从人类文明露出端倪至今,尽管已经走出了迢迢上万年的路程,但我们对自身和所置身的环境的认识,则仅仅始于300多年前。当伽利略第一次举起望远镜向茫茫天际望去的时候,人类对自身和自身环境的自然科学探索才真正启动,地外生命(Extra-Terrestrial Life)的概念也才超出了哲学的抽象和文学的抒情。1894年,美国的天文学家劳威尔在亚利桑那州建立了宇宙观测站,试图寻找他深信存在的地外生命,但迄今仍未找到。1960年,天文学家弗兰克·得莱克(Frank Drake)发起了著名的Ozma天文研究项目,尝试寻找地外文明的电波,自此开始了人类称之SETI(the 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意即“寻找地外智能”)的行动。尽管至今尚无实质性进展,但目前已很少有哪个天文学家怀疑“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了。
“外星人”的存在在理论上的可能性,意味着人类需要足够的思想准备重新调整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天文学家的探索趋于设想地外生命的形式高于地球上的状况,甚至其演进情况超出了人类思维的理解能力。这意味着曾被世代的神话置于宇宙中心的我们的地位正变得愈来愈边缘,在我们眼中意味深长的地球也开始变得如同一粒淡淡的尘埃。
“果真如此的话,我们怎么办?”
遗憾的是,尽管人类在随着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心理状态,但呼之欲出的宇宙格局的重构或许还是超出了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从亚里士多德到牛顿再到如今,神学之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发言权,甚至直到现在仍然和科学联姻,恰恰因为科学自己尚未解决关于生命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尽管达尔文的进化论给出了物种演进的大量信息,但人的意识的起源仍是当前人类学中争论最激烈的问题;在生物学的传统认识中,生命是兆亿分之一概率的分子的偶然连锁,因而它在宇宙中其它地方再度出现的可能性趋于零。智慧生命的存在既然是如此这般的奇迹,一切似乎就无法不追溯到上帝身上去,关于人类与上帝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所有神教的核心。因此,地外生命的存在,尤其是如果它们有着更高形式的文明的话,将给人类这种自我意识中的尊严以沉重的打击。比如,基督教的“复活”的观念将立即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的挑战:基督救赎人类,他同时管不管外星的事?他是否也是地球之外的所有智慧生命的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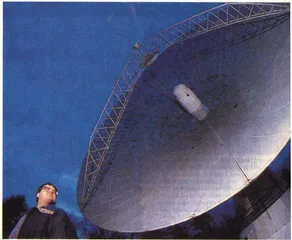
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天线装置时刻恭候天外来客的信号回应
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提醒人们说:“记住你作为人的尊严”,但现状让人难免有点难堪。一位日本的基督徒小心翼翼地表示:“我不知其它世界是否有‘原罪’之说,说不定那里的生命依然生活在伊甸园中,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怎么会乐意与我们(这些被上帝放逐的人)接触呢?”另一位美国人说:“你问‘那儿有人吗?’但比这更难回答的问题是,果真有的话,我们怎么办?”
以对生活的审美观照为人生真谛的中国人倒是处之泰然许多。当被问及“外星人存在的可能性是否会给你出乎意料般的新鲜刺激”时,一位清华大学力学系的学生洒脱地说:“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它说明认识是没有边界的”。
但现实无法令人释然。一方面,人类对自身的状况依然充满困惑,另一方面,人类自身的文明之间尚且时时存在着激烈的冲突。同时,人类不仅对自身,而且对地球上其他物种的认识也仍然处于初始状态:地球上被发现和归类的动、植物尚不到总数的一半;人类对占地表70%的海洋更是知之尚少,以至海洋学界有句名言:“我们对月球的了解要比对(地球上)海洋的了解透彻得多!”在这种情况下,探索中的地外文明又将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巴特勒天文外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