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体育的灰姑娘童话
作者:苗炜
“晨曦微露,杭州市的明珠——西湖一派宁静。在一座水泥筑成的水榭上,密密麻麻站着练太极拳的老人。在绿树掩映之下,一个中年人正在练声。到处都是从事只有一个人才能进行的娱乐性运动的人们。他们有的钓鱼,有的骑自行车,有的活动筋骨,有的打太极拳。一名男子倒退着向后走,两只手各转动着一只健身球。
“从表面看,此情此景与西方有关中国是一个安静、注重内省和保守的国度的观念不谋而合。但这一想法具有欺骗性,会使人误入歧途。”
这是一篇题为《中国综合症》的文章的开头,作者名叫亚历山大•沃尔夫,全文发表于1995年10月16日出版的美国《体育画报》,眉题为“中国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越来越多地受到困扰着西方体坛的种种弊端和诱惑的影响。”
在这篇文章发表后的10天,沃尔夫应当有机会看到他所描述的西湖的清晨会有另一番情景:世界一级方程式摩托艇今年第7站比赛正在紧张准备,轰鸣的引擎声打破了西湖的宁静。一项在欧洲开展的奢华运动被杭州购得了其中一场的主办权。对沃尔夫笔下那些宁静的杭州人来说,西湖,仅有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积聚在那里的精神价值还远不够,这颗明珠要有另一层光泽。
其实沃尔夫不难发现,他在中国的确能够找到各种令人生疑的西方体育制度的证据:高额奖金以及围绕金钱发生的磨擦、买断某位运动员的合同、偶像般的教练等等,沃尔夫还提到了今年3月在辽宁召开的体育人才交流大会,称其商业化程度令西方自叹弗如。
中国体育确实大张旗鼓地进入了商业化的1995年。但要在其中寻找具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却不是一个异乡人所能完成的事。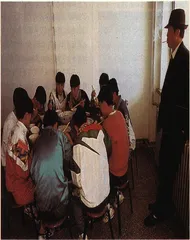 1995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城运会上,石家庄市女子篮球队爆出了一条新闻。该队从教练员到运动员每人自掏腰包1000元前来参赛。热情的南京观众得知此事后便为他们捐款,连南京市副市长也掏出100元聊尽“地主之谊”。石家庄代表团的领导因此责怪女篮教练给家乡造成了不好影响,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石家庄市并非穷得没有参赛经费,只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作一些尝试。他们介绍说,一些项目自筹资金参赛,如果能取得好名次体委再给报销。石家庄女篮水平低,本不打算赴南京参赛,但球队想通过实战提高水平,所以自掏腰包而来。南京观众捐来的钱要转赠给苏北地区的希望工程,这份心意自然应当得到感谢。
1995年10月,在南京召开的城运会上,石家庄市女子篮球队爆出了一条新闻。该队从教练员到运动员每人自掏腰包1000元前来参赛。热情的南京观众得知此事后便为他们捐款,连南京市副市长也掏出100元聊尽“地主之谊”。石家庄代表团的领导因此责怪女篮教练给家乡造成了不好影响,他们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石家庄市并非穷得没有参赛经费,只是要在体制改革上作一些尝试。他们介绍说,一些项目自筹资金参赛,如果能取得好名次体委再给报销。石家庄女篮水平低,本不打算赴南京参赛,但球队想通过实战提高水平,所以自掏腰包而来。南京观众捐来的钱要转赠给苏北地区的希望工程,这份心意自然应当得到感谢。
城运会上的另一件新闻是水上项目落后的兰州市代表团在游泳比赛中获得两金两银一铜的成绩,但兰州游泳队根本没有教练员,夺奖牌的3名选手都来自上海。这就是“雇佣军”现象,实力雄厚的上海游泳队将大批二线队员租借给其他城市,一方得利,一方得名。
本来,此届城运会不搞参赛城市的奖牌榜排名,力求“淡化金牌意识”。但不少城市仍把名次看得很重。而“自筹经费、体委报销”和“雇佣兵团”这两项尝试,都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运动员的利益受到了比赛的影响。
中国体育在1995年的最大失利是哥德堡的世界田径锦标赛,本已形成的女子中长跑的优势荡然无存,马家军的分崩离析、新老交替是一年来的老话题。
应当承认,“马家军”风波是我国体育商品化潮流中一个典型教训,对出场费、高额奖金这些纯粹市场化的问题,只能以纯粹的市场化思路去解决,否则金钱就还会成为体育比赛中的磨擦力而不是润滑剂。如果当初王军霞等人与马俊仁签定合同,确定利益分配,走一条职业运动员的道路,大概就不会产生后来的是非曲折,王军霞想多拿冠军多挣钱就要承受教练员的压力。两年前的“马家军”,的确有能力形成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具有传奇色彩和魔力的俱乐部,在田径运动员由业余转向职业的进程中领先一步。马俊仁念念不忘的训练中心,很可能就是一个略显粗鲁的职业化模式。但现在,事情并没有按照某条更合理的轨道发展。 由于面临明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中的突破仍寄希望于女子中长跑,马俊仁与王军霞等人的现任教练毛德镇、女子中长跑另一位著名教头罗维信受命共同组成了一个教练班子。以体育比赛成绩树立国家威信的思路并没有从主流位置上退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思路已深深根置于一大批体育工作者的头脑之中,并且可能成为体育全面走向市场的障碍。
由于面临明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田径项目中的突破仍寄希望于女子中长跑,马俊仁与王军霞等人的现任教练毛德镇、女子中长跑另一位著名教头罗维信受命共同组成了一个教练班子。以体育比赛成绩树立国家威信的思路并没有从主流位置上退却,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一思路已深深根置于一大批体育工作者的头脑之中,并且可能成为体育全面走向市场的障碍。
体育走向市场、运动员职业化的前提是承认人对金钱的需要,并以此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提高其敬业精神。但这一想法并没有能随体育商品化的过程而被大多数人接受。
11月19日,北京国安足球队在先农坛主场战胜广东宏远队,获得甲A联赛亚军。比赛结束两小时后,主教练金志扬和国安队的5名队员坐到了北京电视台的直播室回答球迷的提问。
国安队在1995年共踢了5场商业性比赛,全国球队无出其右者。但主教练金志扬却表示了他对“商业”两字的反感。他说,国际比赛就是国际比赛,以往是政府出钱,现在不过改由企业出钱。他的这番话让人怀疑商业比赛的赞助者提供给国安队的出场费和奖金是否最终落在了球队的手中。
显然,作为一支球队的主教练,金志扬先生把比赛依旧看得很单纯:己方的11个人对付对方的11个人,力求把球踢到对方的门里去。但是,足球在中国的大方向并不是对着一个2米多高、7米多宽的球门,而是广阔的市场。在这样一个“踢球”的过程当中。“球场”上的“犯规”与“不合理动作”相当不少。
95全国甲A联赛的一大新闻是昔日足坛“十冠王”辽宁队降至B组。在辽宁队最后一战负于青岛海牛队以17分垫底之后,辽宁省体委崔大林先生表示,他对辽宁队降组负有责任。话锋一转,他又说到,十连冠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现在是市场经济,辽宁在观念转变上较为迟缓。崔先生讲这番活时,似乎已忘掉了辽宁队曾在全国率先实现了“企业赞助、合办球队”的“东药模式”。10年前,他们最先想到把一支实力强劲的球队的名号卖给企业,应当算是观念上的一个大突破。问题是:当年的突破为什么没能继续下去?
人是善于自我欺骗的。辽宁队在年初转会中失去了18名队员,这也成为辽宁队降组的一个借口。事实上,在年初上交足协的球员注册中,辽宁队旗下有40名球员,遥遥领先于其他甲A球队,卖掉队员只是主教练对人员的取舍而已。
远东集团是继东药、新世界之后与辽宁足球队共建俱乐部而又事败分手的第三家企业。当时,辽宁队指责远东一方投入资金不到位,投入水份大,违约在前,所以才有全队集体退出俱乐部之后果。
王洪礼教练在今年3月份曾说过这样的话:“与企业合作的失败,使我们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球队要走向市场必须摆脱企业的束缚,球队的兴衰不应受一家企业兴衰的牵连,球队不应受企业某个领导人个人意志的操纵。我们与企业的所谓三次‘婚变’,绝不是为了钱,或者说,钱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我们一直在探索一种机制,使俱乐部真正拥有造血机能,真正独立自主地到球市风浪中去摔打。简单地说,就是创建名符其实的职业俱乐部”。
如果我们简单地理解这番话,就会产生疑问:在全国大多数俱乐部都是靠企业输血、已经使得有人来警告提防国有资产流失之际,辽宁队能有如此打算实在是观念上的又一次突破及实践中的又一次革命。何来而后观念沉旧之说?
既然辽宁省体委方面已表示了不止一次对股份制俱乐部的重视,而且请来了商业人士来筹划此事,何以这个寄托着辽宁队员、球迷及各方人士关注的俱乐部没有建成呢?
有两件事可以让人琢磨出其中奥秘,一是当张桐坡将自己公司的200万元投入俱乐部时,辽宁省体委就停止了对辽宁队的拨款;二是辽宁体委认为球队资产为2900万元左右,这使得张桐坡必须筹划到3000万以上才能获得控股权,而实际上由于入股企业多,体委就是最大的股东。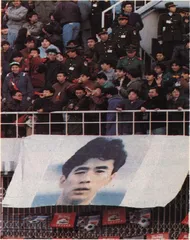 按经济规律办事,某些人的理解就是去抓钱。拥有一支球队是抓钱的资本,功利主义有时是旗帜鲜明的,而在某些人嘴里,改革也可以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包装。
按经济规律办事,某些人的理解就是去抓钱。拥有一支球队是抓钱的资本,功利主义有时是旗帜鲜明的,而在某些人嘴里,改革也可以是急功近利的一种包装。
在辽宁队降组后,球队的三任教练利用媒介展开了对攻,先是总教练李应发说自己“俯仰无愧天地”,而李树斌表明总教练“垂帘听政”确有其事,李应发曾叫他“推功揽过”,杨玉敏更是把矛头对准李应发,说他为当上俱乐部总经理而策划了“远东地震”,为自己的利益而对股份制俱乐部建设设置障碍。最后,辽宁省体委在1993年全运会后的权力之争也被披露。
而俱乐部的策划人张桐坡却成了足球职业化道路上一个“悲壮”的英雄,但如果了解一下辽宁俱乐部的发展方案,则会发现这桩买卖确实有利可图。作为俱乐部的一大股东,中央电视台会全年转播辽宁队的比赛,而张桐坡担任总经理的梁艳体育广告艺术中心与中央电视台一直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显然,中央电视台的加入会使辽宁队与其他球队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而不与利益集团结盟是新闻从业者的基本道德。辽宁足球股份制俱乐部的发展方案,是基于这样一个不正当竞争的前提之下的。而这种违背职业道德、违反市场游戏规则的方案竟得到了各方的默许。
足球职业化的基础是职业俱乐部,足球的发展就在于各俱乐部的完善,并且在竞赛机制、后备力量培养、市场开发等方面形成良性循环。按中国足协对注册俱乐部的要求,职业俱乐部应有自己的二线队员。而今年风风火火的北京队正式在册的二线队员,只有一个人还是从国安二队名下领工资,剩下的队员已组成了威克瑞俱乐部。类似的情况是广州二队拉出去成立了广州松日队,该队已打入明年的甲A联赛。
一个国际化都市拥有两支或更多的俱乐部队并不是件坏事,如米兰之有AC米兰和国际米兰,伦敦有7支超级联赛球队。但是,在目前中国足球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完善一个职业足球俱乐部重要,还是多扯几面俱乐部的大旗重要?
短期行为的泛滥岂独足球职业化过程有之。与辽宁足球队降组相对照的是广东省在明年将有4支甲A球队,除广东宏远队、广州太阳神队外,组建刚刚3年的深圳队和广州松日队一道杀入了甲A行列。
4支广东球队已给一些队伍造成了威胁。甲A联赛尚未结束,北京就风传高峰明年将转会深圳,这种捕风捉影的消息来自于对广东球队购买力的恐惧。在今年年初,广东球队就曾使山东队、青岛队失去了一批战将。
经济发达地区将在更多的领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是改革的大势所趋,足球也概莫能外。
在今年甲A联赛结束后,甲A球队是否由12支扩充到14支又立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王俊生的表态值得把玩,他说,没有定下来的东西实际上是定下来了,现在是12支队伍,没有新的决定就是12支。但定下来的东西也可以改变。是否扩大队伍,你可以发表你的看法,我也可以发表我的看法,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
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中国足协当时已与经营甲A联赛的国际管理集团进行接触,如果能获得更多的赞助,则甲A球队就会扩编。在12支甲A俱乐部大部分都还没有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的时候,中国足球的热闹很让人怀疑其“泡沫成份”。
12月份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又成为舆论的焦点,人们关注是否会用“扩军”来使辽宁队留在甲A,尽管按照国际惯例,即使甲级队扩编,也只会考虑乙级队的前几名,打不好的球队只能降级,根本没机会打什么附加赛。
会议通过的转会细则最终使降级队掌握了一个特权,他们可以不允许自己的球员转会。而在甲A球队服务未满四年的年轻选手,未经俱乐部同意也不能转会。尽管他可能在自己的俱乐部中只是坐板凳,而到了其他球队就会踢上主力。
名为“职业化”的改革却要牺牲球员的利益。而来自上层的指令希望每支甲A球队能帮助一支足球水平落后地区的球队,所为“一帮一,一对红”,以利益为主旨的职业球队要肩负道义的责任,尽管他们可能对自己的后备力量还无暇顾及。
足球,作为中国体育改革的突破口,的确已踢进了市场的大门,但是“触球”的脚并不是都穿着市场的鞋子。由上而下贯彻的“改革”,也由于决策者的无力和各方的磨擦处于一个相当漫长的“磨合期”。
行政指令、不正当竞争、利益磨擦、权力与金钱的较量和交融都存在于体育商品化的过程当中,而利益造成的麻烦可能最终还要靠利益这把锉刀磨平。商业的角逐不像赛场上的角逐那样容易看到,但它慢慢会使运动员、比赛澄清一种新概念,由目前的混乱变成清晰。只是现在看来,还遥遥无期。
有那么一个美丽的童话,童话中的仙女能把朴实无华的灰姑娘装扮得明艳照人落落不群。商业化很可能就是中国体育期盼的仙女。乒乓球队向大企业发出了“认购”的邀请,希望组成职业俱乐部,水平参差的冰球也组成了有4支球队参加的主客场制联赛。篮球在对照NBA形成自己CBA,整个走势是正确的。
但别忘了那个童话的结尾,灰姑娘要穿上那只有魔力的鞋子才能变成王妃,中国体育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削足适履,又怎样避免穿新鞋走老路。 马家军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