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7)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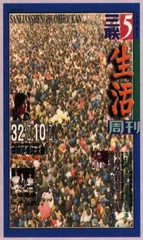
几个家庭妇女要是没有靠山,短期内集资32亿几乎不可能。我们无锡人还不至于愚昧到这等程度。邓斌究竟怎样被推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有保留的曝光,对我们的警示意义总是有限的。
无锡 张祥和
呼唤合理救助
《生活周刊》主编:
下班路上终于又见贵刊面市,买了一本,读到“为了孩子的生命”那则读者来信,心就像被撞了一下,难以再读下去。一路上我都在心里默念着,又是求助,求助,他们真能得到足够的捐款吗?孩子还能有救吗?踏进门,电视正播放北京化工学院师生为一患肾坏死的学生集资10万余元,却未能在社会上引起反响的消息。沉重之余,憋在心中的话不吐不快。
我是位大学教师,收入不高。过去我也常对公共场所的乞讨者施以爱心,当看到美丽的夕阳下,乞讨者们从各处有说有笑地汇聚一起收工时,也曾怀疑自己的爱心被欺骗会失去价值。以后,我只去关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1987年,一位同事因患肝癌,家庭陷入严重困境。我发起了募捐救助,3天内一个只有数百人且多数是学生的单位就集起数千元。近几年,通过传媒,我们知道了在社会保险尚不发达的今天,需要救助的人很多(疾病、灾难、助残、扶贫等等),募捐难度也越来越大。今天的现实不是你是否有爱心,而是有否施爱的经济实力。沧海一粟的捐赠已不可能给需要救助的人带来真正的帮助。
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有些得到大量学生、士兵和工薪族捐款的患者,在捐款尚未用完时,或者已被治愈,或者已经去世。那么,通常情况下余款就归他的家庭所有,这是合法的。但另一方面,有些患者因筹措不到足够的经费,却只能走向死亡。捐款人节衣缩食的初衷是治病救人而非助人发家致富。由于救助捐款行为的自发和无序,此初衷往往得不到充分体现。有识之士曾建议:政府和民间应设有救助捐款的管理机构,使捐献人的每一分钱都得到合理的使用。
期望贵刊能引起讨论,倘若我们能找出至少一条合理救助的办法,那他将是杰出的贡献。
北京 严可
懒得做饭?
编辑同志:
进入90年代,一切向钱看,挣钱似乎成了大家的唯一价值,这也无可非议。大家希望富裕,总比封闭起来捆在一起贫穷强。问题是:我们在竭尽全力挣钱时,也在不断地舍弃许多也许从将来看是挺宝贵的东西。比如现在大家累了一天,都懒得做饭。以我家为例,一周中起码有两天晚餐(中午大家都吃在单位)是速冻食品。除速冻食品,也是买点熟食,怎么省事怎么凑合,凑合几天后就全家下楼到馆子改善一天。过去,三五好友一聚,翻翻菜谱,做一桌酒菜是一份雅趣。如今,已再无这等雅兴,多花几个钱到馆子少了许多麻烦。此种情况,我想绝非个别。想到我们这一代已懒得做饭,那么下一代、再下一代呢?中国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在这样不知不觉中,一个一个被我们自己舍弃。从这种角度看,这绝非是小事。
北京 林清
可悲的“圣诞大餐”
编辑部的朋友:
我是北京一家外国独资企业的员工。“圣诞节”又将来临,我非常想和你们说说近日的感受。
和往年一样,我的外国老板和同事都“飞”回本国去过节了。对于我们这些余下的中国员工,辛苦一年后能“领红包、过洋节”自然也是乐事。男友已在一家饭店预订了“圣诞大餐”,该饭店按欧美传统要求就餐者必须着黑白礼服以示高雅。我为此订做了一套礼服。
但是,昨天电视上播放的晚间新闻让我再也没那份“雅兴”了。
新闻说,世界动物保护协会日前对欧洲几家木材公司提出诉讼,原因是这些公司在非洲滥伐森林,导致赖以生存的大猩猩们无家可归。更有甚者,欧洲木材公司不付给雇佣的黑人饭费,反而鼓励他们猎杀大猩猩吃!我来不及捂住眼睛,血腥的画面已出现了……
最可怕的是新闻的最后一句:“很多欧洲的大饭店为他们的圣诞大餐预订猩猩肉。”
就算欧洲人不肯承认“进化论”,不肯承认人和猩猩的亲密关系,信耶稣的他们也当以慈悲为怀呀!
想到文明的人们穿着礼服、举止高雅,而面对的盘中餐竟是猩猩肉,我就觉得恶心。
北京 刘雯
时尚不是唯一内容
《生活周刊》编辑部:
“生活”是一个我们所能知道的最大的词,因为我们的一切都只能在生活中得到,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也都是生活中的事。我是一个科学工作者,写论文和做饭时,我都同样感到是在生活着。
但是,近些年来,在我们的四周,“时尚”、“时髦”、“潮”等同义词似乎占据了价值评判者的位,变成了生活的唯一内容、唯一标准。无论衣食、无论悲喜、无论工作或玩乐都有“潮”可赶,其种类及形式在一个时期内都有一个为亿万人仿效的模式。连“吃”这种最具个性最动物性的行为也被“时髦”所改变着。一时时兴吃酸菜鱼,所有人都吃酸菜鱼;说吃生猛海鲜,人人又都有了吃生猛海鲜的胃口;说吃“麦当劳”,人们又都改了口味去吃西式快餐。
其实,蜂拥而至是一种极不成熟的消费心态的体现。而媒体似乎和商家沆瀣一气,在某一时期把某一时尚推至非此即傻,非此即非“生活”的地步。相信不是我一个人对穿墙而入的“卡拉OK”声感到闹心。没有“卡拉OK”时,并非有那么多人爱唱歌。有了“卡拉OK”,似乎不唱就压抑,不唱就没过上文明生活。说苛刻点,这种人云亦云是低智商的暴露。
但愿《生活周刊》所描述的生活是健康、成熟的。
北京 李建章

质疑“世界第一楼”
编辑同志:
11月25日《新民晚报》刊了一条消息,称浦东环球金融中心设计图“对外展示”,并附有一张设计图的黑白照片。该建筑由美国K.P.F.建筑师事务所设计,由日本森大厦株式会社出资的森海外株式会社,联合日本36家金融机构和企业共同投资。项目总投资8亿美元,占地3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16900平方米,楼高460米,95层,被称为“世界第一楼”。此楼设计顶部中间为一圆形孔洞,侧面造型又非常清晰地似一把刺向天空的刀刃。它建成之后,也会像现在黄浦江两岸各新老高层建筑一样灯火通明,并不断变幻颜色。如果出现黄光,那么整个浦西岂不处于日本“太阳旗”的照耀之下?我看到这条报道和图片后,感觉非常不好,又不知向何处去诉说。听朋友讲起贵刊出刊,特呈上此函,不知贵刊能否过问一下?
上海 黄阿炳
比萨饼应该收服务费?
编辑先生:
比萨饼自进中国以来,生意兴隆,它区别于“麦当劳”、“肯德鸡”的明显特征是:有领座员,点菜,送餐上桌;此外,加收15%服务费。
这15%乍看上去有点奇怪。因为在中国,只有饭店的餐饮部门才会收取服务费,一般最高也不过是15%。而这些地方所得到的服务是与吃比萨饼截然不同的。在饭店吃饭,随时有服务小姐照应,而比萨饼作为一种快餐,几乎是端上桌就不管了。当然,这15%也很难说不合理。在商业行为中,凡被接受就是合理的。尤其比萨店目前每天的顾客川流不息,一家比萨店经理说:“我帐单上有这15%,你接受你来吃;你不接受,你可以不来。”
国外的快餐业到中国往往变了质,最典型的莫过“麦当劳”。汉堡包本是一种最快捷方便、便宜的食品,可在中国竟有举家穿越半个城市去品尝的壮举,又有排起长队在门外等座的场面。比萨饼在国外也只是一种普通小吃,在中国却堂而皇之地成了中档消费,这种困窘当然是每时每刻都在西方阴影之下的国家无法回避的。想到俄国的比萨饼曾经分为两种,一种付美元,得到的服务与我们相仿;另一种付卢布,顾客要等上两个小时。在捷克,美味廉价的传统小吃受到冷遇,英国的咖啡馆60%以上被美国的快餐挤垮,中国茶好像也有被可口可乐挤掉的危险。粗俗的快餐文化替代精致文化好像已成为一种趋势。有多少人意识到了汉堡包、比萨饼是一种更可靠、更不易引起反感的渗透呢?
北京 尚晓岚
电脑产生的负效应
编辑同志:
我的孩子不能说智商不高,他小学成绩一直优秀,以三好学生报送重点中学,现在上初中二年级。去年,我们作为智力投资给他买了一台电脑。没想到,这孩子一下子成了电脑迷,他可以在电脑上自己设计程序,自己编排动画。这本是好事,开发智力嘛,令人担忧的是,学习成绩却直线下降。不是不会做,而是没有兴趣。11月期终考试,他居然可以拒绝做卷子,交了白卷。老师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些题我都会,但做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我们已不准他再玩电脑。可家里不能玩,他又到别处去玩。这样的情况,是否也算严重的社会问题?你们是否可以关注一下?
北京 王林
上街应该带块石头?
编辑同志:
您好,我是一位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的“工薪族”,跟那些驾着“奔驰”、“宝马”,甚至“法拉利”车的大款们无冤无仇。本来嘛,他有他的道,我有我的路,互不干扰,应该相安无事。可是最近越来越觉得不对劲儿了。我每天经过一座环绕立交桥,这是汽车和自行车交汇的地方,按理两者都应该放慢速度,相互理让,可是有好几次,我差点被急驶而过的“奔驰”或“宝马”卷到车轱辘底下。我保证我是个守交通规则的人,每到经过立交桥或路口时,我更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可是仍免不了被刺耳的刹车声和急剧的喇叭声吓出一身冷汗。现在北京堵车已成家常便饭,照理汽车应该严格遵守交规,循序而行。可是总有个别汽车(当然是以豪华轿车为主)明目张胆地闯入自行车道或者人行道,车身几乎贴着你的身体而行,且速度不减,喇叭声吵得人心慌。若是赶上雨雪天就更让我生气了。曾有过一次经历:刚下完雪,我穿着一件新买的羽绒服骑车下班,被从后面快速经过的“奔驰”车溅了满身污水。让人气愤的是,那辆车上的主人不但没有下车向我赔礼,反而愠怒地咒骂我,没等我反应,就一踩加油门消失在夜色中。我连它的车牌号都没看清,再说就算记住了又向谁诉说呢?我曾与一位好友谈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坐这种车的人不是高官就是大款,就算让警察逮住,最多也只是交点罚款而已,没准回去还能报销,再说这点钱对他们来说算得了什么呢?那位朋友半开玩笑地给我出了个馊主意:以后上街兜里预备一块石头,遇上这种不道德的主儿,就让他的车开花。我听了只好苦笑,我希望贵刊能够把我的经历登出来,并且为我出出主意。
一位不愿留下姓名的读者
难道为降低成本?
编辑先生:
我发现贵刊第五期用纸与以往不同,乍一看显得薄,也不那么白,让人觉得不如前几期那么厚重、豪华、高档。我以为这是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不免有些婉惜,也有一位朋友说,这样的纸张才算找到了《生活周刊》的感觉。他说这种纸虽薄却富有弹性,可以随着手的感觉走,国外高档刊物用的都是这种纸。编辑先生能否就你们改纸的问题作一个解答。
南京 沈洪根
沈洪根先生:
本刊从第五期后试用的57克进口轻涂纸,是国际流行周刊用纸。这种纸张因加入了玉米淀粉,所以轻柔而质感好。我们在国内首先试用这种纸,是希望更接近周刊的感觉。
欢迎广大读者来信,反映问题,参与热点讨论。本刊热线电话:北京(010)4076724 传真号:(010)4076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