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cal的PRD——第二届广州三年展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崔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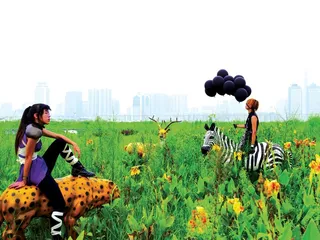 ( 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缩写为PRD
全球-本土性:Glocal
)
( 珠江三角洲Pearl River Delta,缩写为PRD
全球-本土性:Glocal
)
在珠三角,任何可以想象的“现实”都会出现在这个已经成为缩影的“超城市”中,但真实可信的东西却又难以寻找:被零散化及具有零散化能力的事物、同质性与具有同质化能力的事物、混合包装又让人难以琢磨的事物……而这些都是第二届广州三年展最兴奋的主题之一。
第一届广州三年展时候,高悬在博物馆建筑外墙上方的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毛泽东或江泽民的语录标语,而是几个巨大的反讽的红色英文字母“In God We Trust”(我们相信上帝)。那次展览更多是关于十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回顾,黄永平最终被喝令撤下来的美国飞机、王广义的文革雕塑等很多作品或多或少是关于“政治隐语”和“领导权威”。《纽约时报》曾经对此评论:“第一届广州三年展的艺术家们已经在低声中学会对话。如果第一届三年展是一个预言的话,中国的实验艺术应该会比以往更加男性化、更充沛活力气概。”
三年过去,美术馆外墙上还是依稀可见那几个褪了颜色的字母痕迹,展览主题和气氛却和当初绝然不同。11月18日,第二届广州三年展开幕,广东美术馆人山人海,仿佛所有广州艺术中青年都出动了一样。展览的所有平面设计非同凡响,展览画册的创意把单一的作品陈列通过人工粘贴作品主页的方式变成“复性立体”,往精细内容处引导,不同的质地和图像冲击已经让人对展览有很大的期待。用红色工地木板、绿色钢管及水泥架等现代工地上的材料全新布置的美术馆展厅也特别令人瞩目,地板、墙壁、地面都做得相对粗糙:布展的两个法国建筑师平时就生活在香港,一直在对珠三角进行文化研究。他们设计的展场重新打破了惯常美术馆的精细格局,那种建设迁徙变化中的珠三角马上就给人深刻印象。
广场上舞狮击鼓,欢庆热闹更是衬托徐坦作品《九月九的酒》的自娱自乐:劳工最常用的蓝白红条纹塑料包被放大成三层楼高,从中间进去还有粗劣的卡拉OK设备和录像设备,都是街边工地里这些广州城市劳工移民的日常生活。这个巨型大袋子在艺术馆门前的优雅广场上被风吹得晃晃悠悠、自信不足、得过且过的样子。周浩、吉江红的系列影像、摄影作品《民工自拍像》也同样非常细致而朴实地展现了这座南方湿热城市的“另外”的主人:他们也是使这座城市每天都得以生长的有机力量。
曾经负责威尼斯双年展“广东特快”项目的策展人侯翰如是这次三年展的艺术总监,更加针对珠三角的全球化、城市化和富有差异的现代化,联合汉斯和郭晓彦等其他策展人把展览主题定为“别样——一个特殊的现代实验空间”,准“自由放任”地堪称“后规划”城市化的典型个案:“珠三角”的经济、环境保护、外来劳工压力、城市的记忆保存等等问题几乎无所不包,在侯翰如看来,劳工这样的“城市移民”其实就是全球化的内在循环,两千年前的边陲流放之地现在已经是遍地枭雄。
 ( 道格·阿肯的《全新性感都市》,装置 )
( 道格·阿肯的《全新性感都市》,装置 )
广东的文化来源和大中原文化有很大区别,它代表了一种大一统文化里的异类。从康梁时期到今天的经济特区,珠三角一直充当着中国的改革先锋,娱乐工业、流行文化与大众传媒都发展得极其成熟。然而,实验艺术与智性活动相对而言却被边缘化了。它特殊的历史和性格、广东人理性而务实的思维方式,比其他地方更少极端和对立,更超然、更多样。从事当代艺术的广东艺术家也很特别,他们没有太多的喧嚣和功利性的作秀,完全是一种随心所欲、自由自在的状态。艺术家与文化工作者必须将自身组织起来,组成各种自给的群体,同时他们的作品也要经常在街头、建筑工地或家庭空间中创作并加以展示,这自然就会使作品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高雅与低俗之间的传统分别也被有系统地跨越了。这次的作品整体看也不同于一般艺术展枯燥无味的氛围。西方评论界普遍认为“全球政治艺术正在形成,中国正处于它的前沿,政治一词在中国应该可以宽泛地理解为艺术品中出现的表现社会的主题”。这次的三年展显然是带着更有活力的思考向外张开自己的“社会”视野。对今天的中国艺术家来说,如果他们的作品要有某种政治性声明,那么它们也是以讽刺性的间接方式得以表达,波普艺术已经过时,王广义也必须承认:“我试图除掉显而易见的文化对立,代之以强调其自身的那种带有模糊性的朴素力量。”
广东美术馆馆长王璜生、策展人郭晓彦和他们的团队是非常追求“以一种务实态度和超现实情怀”来努力实践文化理想的勤勉打拼类型,推崇卡塞尔文献大展的历史文化感方向和力度。这次的三年展以卡塞尔文献大展为榜样,同样拓宽了时间和空间上的纬度:于2004年11月28日启动的“三角洲实验室”跨越了3年时间,每两至三个月举办一次,强调多重学科的交流、对话,邀请库哈斯、扎哈·海迪和“威尼斯双年展”金狮奖艺术家在内的国际国内艺术家、建筑师、学者等共同完成课题研究、专题讨论:“全球化经济条件下的博物馆经济”、“个体的声音”、“经济,环境与空间”、“存留,记忆与想象”、“边缘,迁移和新城市世界”和“凝视城市”,其中部分参与者更被邀请参与主题展览展出他们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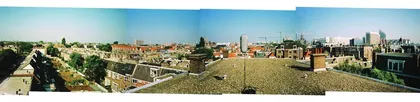 (
贾斯汀·本奈特的《日冕》,声音装置 )
(
贾斯汀·本奈特的《日冕》,声音装置 )
策展人侯翰如在思考问题时不希望总局限在中西方对比这个层面,他提出应注重个人态度的差别。因为“东方、西方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情绪化地谈这个问题,显得幼稚,而且过多地和权利、利益相联。如果从个人感受的角度去看待差别,就要有意义得多。”所以在选择艺术家的角度上,也是更注重作品与主体与当地环境文化之间的联系,“我喜欢的合作者,最好一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二是有批判自己背景能力的,三是能批判性地看待当前处境的。他们应当对社会变化提出独特的思考方式、价值观念和表现方法。我还把鼓励艺术家针对特定文化情景来创作视为策划的中心环节,我策划的展览总是不断地推动个人与社会背景之间、与未来以至乌托邦的未来之间的相互关系。”
“非常建筑”主持建筑师张永和此次与美籍华人建筑师杜鹃等共同创作了《城市标尺》,为了得到对城市空间更密集更富经验的观察和理解,试图用多种工具浓缩、提炼城市的视觉信息并增加其密度,对城市进行密度建筑概念上的干预和证明,那些效果图都具备难得的幽默和实践性。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库哈斯从1995年就开始组织他的哈佛大学学生对不同因素影响下的大都会现状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其中包括对珠江三角洲五个城市(香港、深圳、广州、珠海和澳门)的研究;探讨古罗马城市状态的名为“罗马系统”的研究;以尼日利亚首都拉各斯为研究重点的研究。他认为,珠江五城市是由几个差异巨大的城市组成的一个超大尺度的城市地带,这些城市一起构成了一个新的“巨型都会”模型,一个“极端差异的城市”(COED)。城市间巨大的相互差异决定了它们的功能、合理性以及相互依存的关系,“中国建筑设计周期非常短:一个40层的建筑方案,由三个人和三台苹果电脑在十天时间内完成,设计成果也许是贫乏的”。但他并不认为如此匆忙的设计过程是导致城市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由于大都会的不稳定性,建筑师无法把握和控制环境质量,他更倾向于把这一切归于大都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建筑学对此无能为力,文化也同样。所有人都抱怨我们面临无差异、无特色的环境,我们说,我们要创造美、可识别性、质量和秩序,但也许,事实上我们拥有的城市就是我们所最渴望的。”侯翰如在研讨会中曾把这种种问题称为“后规划”,但是从中国实际情况看,作为基本的“规划”根本就是欠缺和被肢解的,前面的问题纷繁复杂,好像还没到“后规划”的阶段。
 (
雷姆·库哈斯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设计》 )
(
雷姆·库哈斯的《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设计》 )
库哈斯这次终于借三年展机会在珠三角有了第一个作品:广东美术馆时代分馆。与其说是作品,不如说是观察和创意。他主动拒绝了房产商提供的大片空地,而把一座分为底层、最上层和中间层的“社区美术馆”加在一栋已经成形的楼盘中,最主要的并不见得是它的创新建筑形态,更多赋予它独特性意义的是真正加入到普通人“生活”中的“美术馆”这套思想。
普通人的概念在开幕式曹斐的戏剧《珠三角枭雄传》更得以体现:明显有着年轻人甚至大学生戏剧的锐利和无畏,从三太公、十三姨、女白领、公务员、盲妹等“主流之外的民众枭雄”主题,中学生大学生为主的非职业演员,拼贴寓意的本土民间野史、遗闻轶事、时下珠三角的热点新闻、舞台音乐表演形式都是她非常具有自我辨识性的选择,在昔日珠三角对应今天迷离现实中更能呈现转型社会的缩影。演出出奇地放得开,过瘾的不只有半中半外的艺术圈观众,那些十几岁和二十出头的演员在演出结束的后台非常兴奋的状态最让人感动,那是互动创造者最简单地抛却条框和名利的满足。好多的艺术品没有沟通,没有激情,没有沉淀,没有责任,没有清冽之气,而这些在曹斐的独立戏剧里都有,非常难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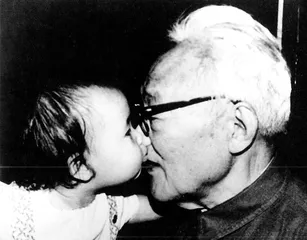 ( 杨诘苍10米×6米的巨型装置《珠江》
)
( 杨诘苍10米×6米的巨型装置《珠江》
)
痛苦的艺术实在是太多了,但是也完全不可避免地被震动:旅居巴黎的艺术家陈箴在2000年去世,他的《水晶体内风景》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将水晶玻璃制成的11个人体主要内脏器官展示在一个特制的体检床上,构成了一幅晶莹透明的“水晶体内风景图”。陈箴曾在笔记中写道:“得了病就已经晚了,最好是不要得病,这就是我的药方。”蒋志的影像作品《香平丽》也是同样面对变性人这个题材毫不退缩,深入到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三个屏幕前反复播放的艳舞/变形手术等片断总是会让很多观众驻足,所思所想恐怕不只是对这些“都市幸存者”的猎奇。
很多国外艺术家专门为此次三年展访问广州,参加实验室计划,并创作各自的珠三角作品:贾斯汀·本奈特也把24小时的广州声音记录浓缩成一个12分钟的声音装置,黑暗的空间里人们能从中分辨和想象一个城市里熟悉而陌生的生活,很有禅定和默契的意味。著名的美国艺术家道格·阿肯把珠三角看成一个个躁动不安、复杂多变而又充满活力的女郎,更特地为珠三角画了一张艳丽的电影海报——《全新性感都市》,特地诗歌作注:“在这崭新的电子都市/我是玻璃,是街道,是混凝土/我高耸如头顶摩天大楼/我匍匐深入潮湿屋槽下/我焕然一新,迅速并活着/我燃烧热量/我不能停止/我被变化激活,我改变着/我将改变你/我将与你共眠/我由你打开 我是你/我就是全新性感都市。”入口大厅的杨诘苍的装置作品对此就是很好的中国式呼应:“我们什么都会,只是不会讲好普通话。珠三角” ■
 ( 林民弘的《椅子》,装置 )
( 林民弘的《椅子》,装置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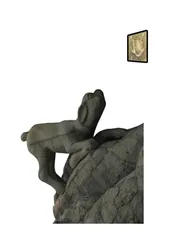 ( 林一林的《想念多莉》,装置
)
( 林一林的《想念多莉》,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