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荣氏家族命运的几个时刻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珞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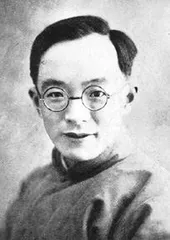 ( 近代苏州实业家
刘国钧
)
( 近代苏州实业家
刘国钧
)
时刻一 20世纪初 白手起家 “小无锡”勇闯大上海
关键词一 艰辛创业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14岁就不得不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学徒。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15岁就乘着小木船从无锡郊区也摇进了大上海。
在兄长引荐下,荣德生进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第一桶金。荣德生于是南下广东,发现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量最大,尤其在兵荒马乱中销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 刘鸿生
)
( 刘鸿生
)
保兴面粉厂在1902年(光绪廿八年)3月17日(农历二月初八)正式开机,一昼夜用麦约两万斤,出粉300包左右。由于保兴面粉厂股本一半是朱仲甫的,故朱担任了总经理,朱利用官场老关系,向清政府立案并取得专利10年。荣德生任经理,荣宗敬继续在上海管广生钱庄,并担任保兴的对外业务。
做惯大差使的朱仲甫,见当年营业并无多大利益,觉得乏味,又去广东官场活动,退出保兴,于是股东重新组合,资本增至5万元。荣氏兄弟股本增至2.4万元,成为最大的股东,厂名改为茂新面粉厂。这便是荣氏企业日后腾飞的发家厂和“根据地”。
 ( 盛宣怀 )
( 盛宣怀 )
关键词二 经营之道
荣德生每到上海,总要物色杂志和机器样本,他向美商要来最新式的白乃里斯粉机样本,对方为了推销,说可分期付款。荣德生早就想买美国机器,无奈那时缺少资金,分期付款正对胃口,就订好机器,先付两成,余八成分两年付清。“只有欠入,赚下还钱,方有发达之日。”1913年,“小无锡”闯进了大上海,他们进而在上海开拓面粉工业的新天地。“固守稳健,谨慎从事,绝不投机”的遗训也成为荣氏集团一直坚守的理念。
 ( 张謇 )
( 张謇 )
时刻二 20世纪三四十年代 民族工业首户 认同主流政治文化的近代苏商
关键词一 民族工业大发展
 ( 荣毅仁家族上海福新第二面粉厂的职工住宅 )
( 荣毅仁家族上海福新第二面粉厂的职工住宅 )
1914年到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忙于打仗,稍稍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工商业大都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各交战国粮食生产萎缩,不但无力输出,还要大量采购。我国面粉价格便宜,产量多,自然成为各国竞购对象。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抵制外货声浪高涨,民族棉纺工业又获发展契机,一个个申新纺织厂破土而出。到1932年,申新系统9个厂共有纱锭52.15多万枚,线锭4万枚多一点,布机5300多台,固定资产4180多万元,职工3.17万人,年产棉纱占全国民族资本棉纺织厂总产量的18%多,棉布产量占29%多,因而荣氏兄弟又成为棉纱巨子,荣获“棉纱大王”的称号,成为中国最大的民族资本棉纺织集团。据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荣家是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在国际上称得上财团的,我国恐怕也没有几家。
关键词二 对主流文化的认同
无锡的盛宣怀及杨宗濂、杨宗瀚兄弟,荣宗敬、荣德生兄弟,常州刘鸿生、刘国钧等人,还有南通张謇、南京的范旭东等实业兴国的苏商,数量多,发展快,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居全国之最,据有关材料统计,截至1919年全国工商注册的工厂共375家,江苏达155家,占全国同时工厂数40%,位居全国之首。其强势群大多分布在纺织、面粉、火柴等轻工业,而且大多分布在苏南,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地。
近代苏商形成的背景有二:一是民族危机的加深,“实业救国”是他们共同的理想;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启蒙影响,无论是从官僚、买办、新旧知识分子中转化而来或是从传统古代苏商中衍化出来,无不体现了这一点。他们面对民族危机,又充满爱国热忱,主张“实业救国”,主张“商战”。主张义利结合的荣氏集团,则创办纺织染工业专科学校、江南大学以及图书馆、公园和公益学堂等反哺社会。
时刻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红色资本 新中国建国到公私合营
关键词一 留在大陆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于是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处缓刑,后交了100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关键词二 恢复生产
荣毅仁回忆道,“1949年,共产党百万大军横渡长江,挥戈南下。我是怀着‘共产党政府绝不会比国民党政府更糟’的信念留在上海不走的。虽然如此,心中仍然存在两个疑虑。一是生命安全有没有保障,二是办实业有没有希望。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大批撤离,传说解放军要进城。第二天我就开车出来,一路上,只见解放军官兵果然都露宿街头。车到成都路浦东大厦时,一个解放军战士拦住我,说:前面敌人还未清除,不安全,劝我不要再向前。解放军军纪之好,真是秋毫无犯,同国民党军队相比,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时,我的第一个疑虑开始消除了。
“6月2日,也就是上海解放后的第七天下午,上海市军管会请我和其他同行到外滩中国银行四楼参加工商界人士座谈会。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共产党的‘大官’陈毅市长。他中等身材、体格魁梧,气宇轩昂,着一套洗得有点发白的布军装。令人惊异的是,脚上穿的是布袜草鞋,同我在马路上见到的解放军战士没有什么两样。陈毅市长讲话(风趣诙谐,刚柔相济,边说还边捻着桌上的花生米,嗑着瓜子,神态可亲可敬。他向我们阐述了党的经济政策,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鼓励我们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还说有什么事可找人民政府商量,政府会帮助大家的。文质彬彬的潘汉年副市长也在会上讲了话。这个会使我心中存在的第二个疑虑开始打消了。会议一结束,我就赶回公司,对等候在那里的经理、厂长们说:‘明天就开工。’”
关键词三 社会主义改造
回忆起上海解放初共产党和工商界合作恢复生产那一段,荣毅仁说:“上海市人民政府不仅帮助我们缓解劳资矛盾,还采取一系列措施,扶持我们民族棉纺织工业。如鼓励进口外棉,免征进口税等。为了缓解申新系统资金的困难,上海市政府还通过人民银行以及新华银行、四明银行等给申新数量不小的贷款。”
50年代那一段,对荣毅仁来说,感触最深的自然莫过于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他说:“上海解放以后,私营工商业者切身感受到共产党是可亲、可信的。但他们在新中国的未来命运究竟如何?这是他们经常在想但并没有很好解决的问题。到了1955年底,毛主席亲自来给我们做工作了。10月27日和29日,毛主席两次约见工商界的代表人物谈话,第一次在颐年堂,只有黄炎培、陈叔通等少数人。第二次在怀仁堂,人数比较多,我也参加了。毛主席告诉我们:只要了解社会发展趋势,站在社会主义方面,有觉悟地逐渐转变到新制度去,个人的命运是可以掌握的。他要大家安下心来,不要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建议减少吊桶,增加抽水机。这对我们是很大的教育和鼓舞。1956年1月10日,毛主席还亲自到我们申新九厂来视察。毛主席一下车,看到我,便亲切地说:你不是要我到你厂里来看看吗?我来了。毛主席到已经公私合营的申九来视察,对上海的公私合营工作有很大的鼓舞和推动作用。1月20日,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现在的上海展览中心)举行了上海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工商界代表向曹荻秋副市长递交了合营申请书,并当场获得批准。”说到当时的热闹情景和大家那种兴奋的心情,荣老显得很激动。他说:“定息多少,是合营后大家最关心的事。多数工商业者是‘坐三观四’,嘴上说只要三厘,心里想四厘。毛主席党中央看透了大家的心思,宣布定息一律五厘,七年不变,还可拖个尾巴,大家十分开心。到这个时候,私营工商业者的前途和命运得到了解决。可以说是两只脚都踏进了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