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沈宏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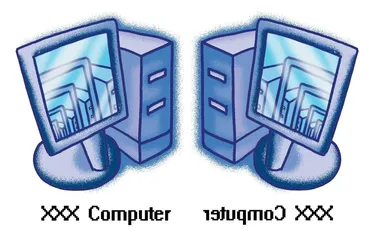
图◎陈曦
凡以windows系统操电脑(或以同一系统为电脑所操)者,都晓得桌面上有一图示叫作“我的电脑”,英文版windows里,又被标记My Computer,图标就是一台电脑,主机显示器连键盘,全乎。
“我的电脑”和My Computer虽是同一个意思,而且我们今天所用之电脑,大体上也都属于“个人电脑”,即英语PC(Personnal Computer)泛指的这些电脑,不过诡异之处,在于电脑这东西,尤其是非符号化的这台实在的电脑究竟属谁——我的?你的?个人的?集体的?某些情况下,想多了也会令人发疯。我认为,电脑产权令人发疯的程度,可能并不输给国有企业产权的界定。
段子说:某用户遭遇技术故障,打电话到电脑公司客户服务部。客服人员发现对方对电脑知识了解不多,遂循循善诱之:“第一步,请打开‘我的电脑’。”
“咦,你的电脑我怎么能打开呢?”
差点晕倒的客服人员做了一次深呼吸,尽量耐心地对用户说:“好吧,既然这样,那就请打开你的电脑吧。”
“可是我的电脑早就打开了啊。”
对话至此,理科出身的客服不由得当场吐血三升,彻底晕倒。
除了语言上的公案式迷惑,“我的电脑”有时还会遭到更高层次的挑战和质疑。曾在某报读过这样一则故事,说某国营单位新买了一批电脑,忽一日,处长大人驾临办公室巡视,对同志们正在使用的电脑发生了浓厚的兴趣,看着看着,突然把脸一沉,然后指着电脑屏幕上那个“我的电脑”的标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说:“同志们,这些电脑都是用国家的财政拨款购置的,都是公家的财产,人民的财产,你们怎么能把它当成‘我的电脑’而据为己有呢?现在我宣布,马上把‘我的电脑’统统都给我改成‘国家的电脑’或者‘人民的电脑’!”
这并不是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笑话,事实上,领导非常懂行,因为只要用鼠标右键点击(虽然懂得使用右键的人总数上并不会超过习惯性使用右手的人)这个图标,“我的电脑”这四个字其实是可以任意篡改的。就公私观念而言,不仅“我的电脑”可以改成“国家的电脑”或者“人民的电脑”,从个性化以及人性化潮流出发,爱看清宫电视连续剧的,可以改为“朕的电脑”,生性谦逊有礼的,可改写为“鄙人的电脑”或者“妾身的电脑”;弗洛伊德的“粉丝”就更幸福了,他们同时拥有以下三个选择:“本我的电脑”,“自我的电脑”以及“超我的电脑”。
诗人马雅可夫斯基,15岁加入布尔什维克,常在作品中称十月革命为“我的革命”。有看不惯者于某次朗诵会递字条责之曰:“马雅可夫斯基同志,您说您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可是您的诗里却总是‘我’、‘我’、‘我’⋯⋯这是为什么?难道您还称得上是一位无产阶级集体主义的诗人?”好一个小马哥,当堂反唇相讥:“向姑娘表白爱情的时候,你难道会说‘我们’、‘我们’、‘我们’爱你吗?尼古拉二世却不然,他讲话总是‘我们’、‘我们’⋯⋯难道你会因此认为他是一个集体主义者吗?”
尽管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未来派”诗人,但他的时代不仅没有电脑,就连用电可能也成问题,不过“我”和“我们”之争,同样也适用于电脑的归属。windows预设的这个“我的电脑”,表面上相当于马雅可夫斯基诗歌里的那个“我”、“我”、“我”,而在事实上,这些表面上的“我”皆遭到了我辈凡夫俗子的严重误读,也就是说,以一个少年布尔什维克的觉悟,表面上是“我的十月革命”,实际上则是“我们的十月革命”;以一位少年电脑天才的智能或者无数少年电脑天才的集体智能,表面上的“我的电脑”,其实都是“我们的电脑”甚至“他们的电脑”。
网络时代,任何一台未能连线的电脑基本上就是一堆废物,属于“我的电脑”;任何一台接入网络的电脑,理论上都可能受到“数字尼古拉二世”——黑客的侵袭,通过恶意技术手段在线上分享你的资源,甚至控制你的电脑,把“我的电脑”变成“他的电脑”、“我们的电脑”、“他们的电脑”、“丫的电脑”以及“丫们的电脑”。你的电脑也在不知不觉间从有我之境陷入无我之境。连线之后,“我的电脑”理论上便不复存在,在黑客或者红客、白客的控制之下,“主观”的电脑变成“客观”的电脑。颜色各异的恶意“客体”实际上充当了任何一台个人电脑的“大对体”主体的后现代焦虑,诚如齐泽克所言:“没有始终暴露在大对体的凝视之下,以至于主体需要(照相机、摄影机)的凝视,使之成为自己存在的本体论保证。”电脑的产权或所有权依然还是你的,使用权却无可争议地旁落到不知名的他人手里。当然,后者在对主体造成创伤的同时亦有效地抚慰了主体性的焦虑。因此,你的电脑,我的电脑,不管是你的还是我的,我的还是我们的,你大爷的还是大爷我的,任何争论已毫无意义,所有运行于windows系统的电脑,其实都是比尔·盖茨的电脑。■ 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