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信仰者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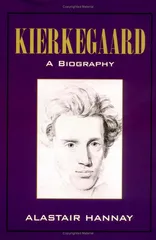 ( 《克尔恺郭尔传》 )
( 《克尔恺郭尔传》 )
1837年5月,哥本哈根大学的学生克尔恺郭尔遇到了15岁的雷吉娜·奥尔森。从此,这位姑娘改变了他的生活和现代思想史。他为之神迷,开始跟她约会。“下一刻你将和我如此接近,势不可挡地充满我的灵魂,我将得到提升,感到无比美好。”他被这个可爱的孩子深深地打动了,她让这个男人对生活充满渴求——没有她,他将继续生活在他父亲的苛求和上帝的苛求之下。她顿时将他从桎梏中解救了出来。
1840年9月克尔恺郭尔向她求婚,相信她会让自己的生活丰富多彩。然而还不到一年,在1841年8月,克尔恺郭尔在给奥尔森送了四年花、写了四年情诗之后,突然对美丽、富有的奥尔森小姐说:“不要再继续排演那必将发生的场景了。忘记那个写下这些的人吧,原谅那个不能让姑娘快乐的人。”奥姑娘花了两个月才能面对现实——两个月后,她站在克尔恺郭尔面前,将他写给她的字条慢慢地撕得粉碎。克尔恺郭尔一部新传记的作者盖尔夫(Joakim Garff)认为,“这个小小的动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她不再是纸上的雷吉娜,她回到了活生生的现实之中”。
后来克尔恺郭尔在他的书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起初,只存在一种性别,即男性。男人的优点和辉煌让创造了他的众神很不是滋味,嫉妒了起来,于是他们又创造了女人,把女人作为能够魅惑男人的惟一诱饵来设计。“众神这样创造了女人:如夏夜的薄雾纤柔而缥缈,却又像成熟的果实浑圆而丰满。她承担着所有世人的渴望,却轻盈如天上的飞鸟。她体态婀娜,按精确的比例设计,而看起来却似乎荡漾着美的曲线。她圆满而完整,却又仿佛刚刚造就。她像初雪一般清凉,怡人,爽心;她肌骨莹润,艳若桃花;她是欲望所趋的目标,令人息心静虑。”
于是很多男人上了神的当,拿神的诱饵当最后的晚餐吃。但也有的男人依旧能让诸神嫉妒,他们识破了神明的把戏,他们常常品味诱饵然而从不落网,日子过得比诸神还奢侈。克尔恺郭尔或许在1841年也突然间识破了神明的把戏,拒绝上钩。传记作者对此的解释是,克尔恺郭尔觉得自己更适合做一位作家而不是丈夫,他给雷吉娜写信只是为了打磨写作技巧而不是表达真情。这么说有点不合情理,克尔恺郭尔认为无论是追求真理还是信仰上帝,都要用感情体会,都是痛苦的过程,他更愿意借痛苦来接近真理和上帝,而不是过世俗的婚姻生活。
克尔恺郭尔1813年出生于哥本哈根,1855年死在那里。他是家中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家人都叫他“叉子”,因为小时候家人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他的回答是“做一把叉子”。为什么呢?“因为那样在饭桌上我就可以去叉任何我想吃的东西了”。思想史家们由此类比说,克尔恺郭尔的作品惹火了哲学界和神学界,像叉子一样扎向了不可侵犯的教会。“哦,路德,你有九十五条论纲。可其实只需要一条:《新约》中的教会根本不存在。没什么需要改革的。”
 ( 克尔恺郭尔 )
( 克尔恺郭尔 )
他一生中只离开过丹麦五次,他曾热烈地称赞过丹麦语:“一种能充分表达笑话和认真的语言;一种能用锁链轻巧地套住它的孩子的母语。”可是他的同胞哥本哈根人对他很不友好,《海盗船》杂志上一系列漫画把他画成驼子,拄着拐杖,双腿瘦小,两条裤腿还不一样长。这令克尔恺郭尔很受伤,“我将慢慢地被一群鹅践踏致死”。更糟糕的是,1846年,他的裁缝说他的名声也被毁坏了,要他去别的地方做裤子。
克尔恺郭尔在哲学上最为鲜明的特点是他对黑格尔的批判。黑格尔建构了完整的哲学体系,描述理念的演化过程,他的著作好像抽象超脱,远离现实世界。克尔恺郭尔则认为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在追求真理,人不应该被抽象的理念压倒,用中国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他也不自命为哲学家,而称自己是诗人、布道者。他没有构建严谨的哲学体系,而多用反讽、寓言的手法表达自己的思想。
这部新的传记主要是收集了很多奇闻逸事,作者甚至翻阅了克尔恺郭尔的病历。该书2000年在丹麦曾经风行一时,但是美国人觉得那是因为克尔恺郭尔在丹麦是民族英雄,而且那里的冬夜很漫长。 痛苦信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