味中求道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宝)

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慢慢进入消费社会,各式各样的消费代理人就会出现。消费代理人的责任是指点你怎样开开心心地花钱,帮助你吃好玩好。有人爱好旅行,应该有导游;有人偏嗜看碟,应该有荐碟人;有人专门泡吧,应该有夜店指南;有人要小赌怡情,应该有麻将法师;有人喜新厌旧,应该有离婚律师;有人热衷用化学合成物自我毁容,应该有美容大王……非常多的人喜欢餐饮,所以应该有食经写手。
台湾的叶怡兰女士,周游列国尝遍百味,对各地美食的考察体贴入微,她的《玩味——Yilan的味蕾漫游笔记》(三联书店,2005年1月第1版)态度虔诚,文字清丽,是当代汉语美食作文中的上品。
叶怡兰玩味,高人一头在味中求道。她推崇法国和日本的美食,特别注意到:在法国,“美食被视为一门绝高的艺术”,在日本,“美食已经成为一种全民共通的信仰”。
这些国家的美食之道是,主厨是艺术家,他们以“创作者的理想与热情,不求糊口、不为营利,而是以追求高度创作表现与艺术境界的达成为目标,即便需要借贷举债也在所不惜”。另外他们的料理态度狂热专注,“从食材、烹调、器皿、盘饰到整体用餐空间,每一个环节锱铢必较苛求到极致;追求美味于是像追求幸福一样,值得耗尽千金耗尽心血力气来换取”。以法国的食材为例,有“收成后还得再送到特定养殖田里精酿过的贝隆生蚝,数百年古老盐田结晶出的布列塔尼盐之花,需在特定洞穴养成、不同地窖气味风格就不同的Roquefort起司,只能以手捞捕、肉质细嫩一碰就碎的狼鲈,本已失传、经过下气力重新复育、香气比一般草莓浓厚二十倍的野草莓……”而且所有食材“从产地、品种、年份一一讲求血统身世来源”。
中国美食很少食材意识,现在似乎连药材都不讲究产地、年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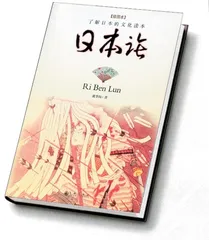
叶怡兰写了那么多的美食文章,几乎不提中华料理的主流菜单。我冒昧地猜测回避表达的是不以为然:烹调为重、环节散漫、马虎粗糙的美食有味而无道。
目前中国的食经写作也和中国的餐饮一样粗糙。我们没有米其林餐饮指南那样权威专业的作品,美食文字大多是抒情暧昧的散文。美食作家上焉者是叶怡兰那样的散仙,下焉者多为乞食百家的野鬼。

戴季陶的《日本论》(九州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七十年前在言说日本的中文著作中首屈一指,七十年后恐怕还是名列前茅。戴季陶对日本“理解的精确”,至今仍然可以独步天下。七十七年前,戴季陶说:“‘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这段话今天会有许多人听着刺耳,这就叫先知的力量。
时尚、流行一类的话题,已经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收编为学问,尤其是女学者,出专著、开网站、做项目、搞调查,潮流事物的清单全在她们的学术视野里。时尚对女人的诱惑不可抗拒,那些脸色灰暗身材平常的女教授过去是被花枝招展的姐妹逼进学堂,她们何尝不向往生活中的光鲜和虚荣,现在研究课题和经费日益开放,终于能在学问的名义下爽一把。
《时髦的身体——时尚、衣着和现代社会理论》([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著,郜元宝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第1版)的作者是英国艾塞克斯大学的老师,她选了一个很打眼的题目,估计很多对学术没有兴趣的人都会为书名掏钱。
《时髦的身体》把近代以来西方文人学人哲人有关时尚、衣着、身体的各种说法排了一遍,全书到处都是引文,作者自己好像没什么想法,或者有想法也不敢说。书中提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棉质白色汗衫白色内裤和拳击短裤是男性同性恋的性感标志;弗洛伊德对服装的性解释:“毛皮衣象征着阴毛,领带和帽子象征着阴茎,而鞋子、腰带和面纱,则象征着阴道”;头发蓬乱象征叛逆和批判,所以艺术家的头发又乱又脏,而头发光滑则体现顺从,律师和银行职员都是一丝不苟……可惜作者是位有洁癖的学术女性,对这些我以为比较刺激的题目一笔带过,不做任何讨论。
作者温婉的女性风格还表现为她对经济学兴趣缺缺,书中很少摘录经济学人对时尚和身体的发言。她说“身体实际上一直显示着生产与消费之间那些不容易看清的联系”,但她自己也没有说明白。从简单的经济道理看,身体变成一个重要话题,是因为时尚产业不断地在刺激强化对身体的谈论。这样的谈论越热闹,越仔细,时尚产业就越兴旺。■ 叶怡兰味中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