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331)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文侠 尤梓江 洋洋 山谷 刘浩 李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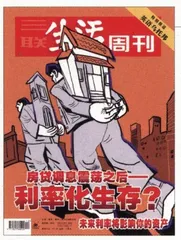
利率化生存?
“这期封面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利率化生存。利率该升还是该降,不是普通人能操心的,那是格林斯潘或者准格林斯潘们的专利,欧美如此,我们也不例外。所谓发达国家贷款品种丰富利率可选,那也是别人给定的选择,其设计也是与时俱进的,不保证永远不变。在我看来,央行的调控或许还可以进步,但享受和承受利率变动的后果,是我们必须学会的。”
北京 文侠
官样文章里的花样年华
4月1日愚人节,有人告诉我:“教育厅规定,3月份起,高中一二年级不许早读、夜自修和周末补课。”这是真事,但听来像“愚人节新闻”。都4月了,这规定还没传达到一线教师。早读、自修和补课,是任何一所还想正常招生的学校的作息表神圣不可分割的部分。虽然理念先进,但这个规定实在太超前了,加上没有针对现实困难的解决措施,几乎所有老师都怀疑它能否落实。但可以肯定的是,教育史学者会据此为今日教育记上“人文关怀”一笔。
提出政策却不在乎落实还有一例。我所在的学校向来不坐班,今年却安装了一台指纹考勤机。于是上班路上,我偶遇在家校间往返“晨练”的一位同事,口里还嘀咕着:“我从家里来,带着手指头,按在校门口,赶紧往回走,一天两三回,不是为减肥,起早又摸黑,时间最浪费。”我安慰他:“人生自古谁无迟,却喜早点有的吃。”耐人寻味的是,校领导私下曾坦承,早知道考勤机没有作用,但他不在乎。可以肯定的是,由“高科技”三字修饰的“考勤制度改革”一词将多次出现在今年的工作总结中。
浙江 尤梓江
“办事”过敏
偶一位老友,生性老实,讨了个恶妻,常被拳脚相对。一日,朋友终于爆发了,哭着喊着要偶替他主持公道。
偶从“民法”中找到一条有关公民的人身权益保护法,整好材料,就上司法部门控诉去了。好家伙,竟然有那么多人来办事。没后门可走,只好老老实实排队。好不容易轮到偶了,哪知那司法同志挥挥手:“这点小事找居委会解决去。”我欲争辩,他说:“快走,要不告你妨碍司法公务。”居委会的阿姨热情接待了偶,可听完这事忙摆手:“这事已经调解N次了。男人嘛,应该多迁就一下女的。”偶说,再这样下次非出人命不可了。“你要真叫劲,就找妇联去吧!”阿姨说。偶这才发现社会的缺陷,竟然没有男联。妇联就妇联吧,了解了偶老友的情况后,妇联同志非常气愤:“想不到天下有如此恶妇。”偶心中暗喜,可那同志话锋一转:“这事呢,偶为你那朋友不平,可我这里只是管妇女权益不管男的。还是去找派出所吧。”偶嘀咕着来到派出所,人家回话:“这事呢,属于民诉案,还是找司法部门吧。”
无奈,偶对可怜老友说:“你老兄还是抓紧学武防身才是上策啊!”
无锡 洋洋
电话录音
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晋升,应酬也多了,搞不清自己在这滚滚红尘中忙什么,反正很少能按时归家,更别说回老家看望父母了。
上次出差,经过老家,顺便回去看看。推开虚掩的大门,听到母亲在打电话,声音很高。“妈,你和爸爸身体都好吗?天气冷了,你们一定要注意身体。”奇怪,电话里传出的竟是我的声音?我走进屋,儿子以前学英语用的“步步高”复读机躺在桌子中央,母亲坐在桌旁,脸上洋溢着满足的微笑。父亲告诉我,每次电话显示我的号码时,母亲总是先按下复读机的录音键,再按电话机的免提键。当老两口闲得无事,便打开复读机,听听我的声音。
我眼睛一酸,想起目不识丁的母亲为我付出的一切。父亲多病,她白天干农活,晚上织草包维持着生计和我的学费。一次夜里我腹痛难忍,母亲背着我去10里外求医,在漆黑的路上摔了好几次,而每次摔倒,她都关切地问我“痛着了吗?”现在,我有了满意的工作,温柔的妻子,可在我享受幸福人生的时候,竟然无暇顾及自己的母亲。我没有勇气当面承认错误,只能以这篇文章向母亲忏悔。
江苏东台市 山谷
新书预告
2005年1月15日是《三联生活周刊》 十周岁,我们编辑了《〈三联生活周刊〉十 年》一书,想给刊物的成长留下一点记忆。
该书以文集的形式讲述周刊从创刊至今各个时期的理想追求,生存状态,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三联书店独特的文化背景使这本书讲述的编辑部故事也极富个性。文集撰稿人除三联书店领导人,以及参与创刊的一些新闻界、学术界著名人士外,主要是在周刊发展各个时期工作过的编辑、记者。文章对办刊理念、新闻操作手法和文化内涵、文章写作的特点等都有涉及,一些记者以亲身经历写就的采访和 写作故事,对于有志于新闻事业的年轻学 生不无裨益,也是关心周刊的读者过去无 从了解的文章以外的世界。
该书近28万字,436页,定价28元。将于近日出版。
全国各大书店有售。向周刊读者服务部邮购,可八折优惠,挂号费3元。
咨询电话:010-84050434 84050425
邮局汇款:北京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邮编100010《三联生活周刊》收
银行汇款:开户行:工行王府井支行营业室;账号:0200000719004641092;户名:三联生活周刊
莫让农村古树保护成“飞地”
不久前《三联生活周刊》有一篇广西读者的来信中提及当地“古榕树进城”的事情,这让我不禁联想到了最近西安市民普遍关注的一件事——大雁塔北广场建成时,这一带就进行了必要的绿化,广场上一下子全部栽上了几百棵碗口粗的银杏树,但一年过去,却枯死近半,听说这样大的银杏树每棵都要花费上千块钱。
如果说这些树木只是算作“大树进城”,单单只是对金钱的耗费的话,那么笔者上个星期回家时在渭河边的所见所闻就让人更惴惴不安了!
回家后,我陪爷爷去河边散步,发现沿河岸的几家苗圃都不约而同地用吊车栽植古树。我听爷爷说,这些树在这里只是做暂时的停留,原来这些古树都是这些苗圃从当地及附近的农民手里花大价钱买来的,等到“名花有主”之后他们就可以很快倒手,狠赚一把了。我们居住在西安这样的古城当中,每每会从媒体报端见到,某地某街道有人对古树进行破坏的消息,但这些消息相对于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农村古树大规模的掠夺又算得了什么?
西安 刘浩
标准答案
机关里发了一套试卷。题目不少,满满4页。选择题、是非题、简答题、论述题等等。好在测试是开卷的,内容尽在三本书里,而且同事之间亦可探讨。
做了1/3,我的懒劲便上来了,以为某些问题无需翻书,估摸着也能答出来,未必非得用“标准答案”。同事当即否定了我这风险太大的做法。他说的道理,我当然也懂。我们的评分机制其实也就是一种易于懒人操作的标准模式。撇开标准一途,则险莫大焉。此时放下试卷,探讨其得失,实在也太“迂腐”了。这简直就是拿自己的“仕途”不当回事,开玩笑了。于是,只得依旧例,一路“标准”下去。
成绩几天后下达,果然是“高分”。欢欣之余,心里总是有些嘀咕:看问题分析事理,若全是一个“标准答案”,几个相同的“要点”,肯定解决不了我们工作中可能遇到的各类问题。这个道理,谁也明白。不由得有些担忧,长此以往,人岂不也会变得僵化教条起来?与现在倡导的创新精神背离得太远。
安徽铜陵 李维明 三联生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