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威辛:在遗忘和纪念之间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贾淼 蔡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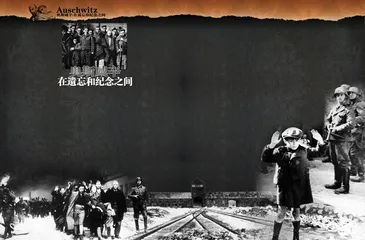
解放者的“遗忘”
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主任、流放史专家阿纳特(Anette Wieviorka)为代表,一批历史学家认为苏联红军解放奥斯威辛的行动当时并不在计划之中。阿纳特认为,虽然莫斯科方面还没有最后公开与此相关的历史档案,但根据当时一些亲历者提供的资料来判断,这完全是一次突发性的行动。在红军向波兰西部推进的过程中,先头部队——60军的某一分支——偶然进入了奥斯威辛。没有迹象表明奥斯威辛是他们预定的进攻目标。不过解放者并非对奥斯威辛的存在一无所知,毕竟这个集中营在1940年就运转了,而且关押过不少苏联战俘。
1945年1月27日这天,进入奥斯威辛的部队把分散在三个营区里的7000名幸存者集中到1号主营,给他们分配食品,并进行了简单治疗。留下来的都是垂死之人,其余5.6万名“有工作能力”的囚犯早在1月17日和21日间被党卫军带走,在冰天雪地里徒步向其他集中营转移。这就是后来历史学家所说的“死亡行进”——数千人因为严寒和筋疲力尽死在路上,还有一些被党卫军队员枪杀。历史学家一直想弄清楚一个问题:1月27日红军是否发现了奥斯威辛里面发生的灭绝罪行?阿纳特对此是肯定的:以前他们可能没有听说过,但在和幸存者交谈之后就应该有所了解。他们看到了毒气室、焚尸炉的残迹,不远处成堆的眼镜、假肢、鞋子,还有7吨没来得及运往德国本土加工的头发。但是接下来红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对奥斯威辛进行调查和搜集,好像没有对里面的杀人生产线引起足够的重视。苏联国内报纸上刊登了波兰这边的战事消息,但奥斯威辛没有占据什么重要位置,更谈不上细节。成立“历史委员会”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而且最后给出的是一个错误结论:他们估计奥斯威辛的死难数字为400万人——事实上在100万左右,并对其中犹太受害人占90%的事实只字未提。这个错误数字后来被西方媒体广为刊载。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出入?有两个解释:将数字夸大4倍是出于宣传需要;而隐瞒犹太受害人的身份,是因为他们认为受到纪念的纳粹受害人都应该是反法西斯主义战士,而不是遭驱逐的犹太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被掩盖,奥斯威辛作为反法西斯纪念地也仅限于关押过战俘的1号营,至于作为犹太灭绝营的贝克瑙,即奥斯威辛2号营,很长一段时间被漠视了。
对于1月27日被解救的人,苦难并没有立刻结束。他们被送到按国籍设立的集中遣返中心等待遣返,主要设在波兰克拉科夫和苏联敖德萨两个地方。混合在大批战俘和劳工里面,这批人显得那么微不足道,完全被淹没了。1945年3月底第一批遣返船队在法国马赛港靠岸,一共2000人左右,其中奥斯威辛1月27日的幸存者不到10个。部分奥斯威辛幸存者历经了漫长的令人心酸的回归旅途,从一个遣返中心辗转到另一个,直到1945年秋天才得以抵达自己的祖国,而这时候设在巴黎的接待中心都关闭好一阵子了。他们经历了和别人完全不同的肉体苦难和灵魂伤痛,在那样热烈的也是混乱的局面下却无法和人言说。即便都是集中营幸存者,也还有抵抗战士和犹太人的区别。刚开始,奥赛车站被选作收纳他们的接待中心,但是由于一些幸存者过于可怕的身体状况,接待处改在了吕特提亚旅馆(Hotel Lutetia),垂危的人可以随时送到附近医院。
真相姗姗来迟
按照我们现在的推想,奥斯威辛发生的犹太灭绝罪行一定成为战后街谈巷议的轰动新闻。并非如此。以法国为例,事实上在3.7万名回返的人里,犹太幸存者不过2500人,而且大多数是外国身份。那是满目疮痍的战后,供给困难,疾病流行,大多数人都为生计而受煎熬,谁还会关心你是在奥斯威辛失去了所有亲人,还是被战争的炮弹夺走了孩子?几乎没有人肯倾听他们的奥斯威辛遭遇。和抵抗运动的英雄、死里逃生的政治家相比,犹太幸存者都是小人物,而且一无所有:家人都死了,家当被抢了,住房被占了……他们根本找不到陈述的途径,也没有力气了。
在奥斯威辛被解放几个月之后,大约在1945年4月,位于德国境内的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也被盟军解放,英国记者拍下一组照片,第一次向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展示了集中营的罪恶:推土机正在推埋成堆的尸骨,身穿条纹囚衣的幸存者骨瘦如柴目光绝望……人们以为这就是传言中的死亡营证据了,事实上这还不是,人们仍然看不见奥斯威辛贝克瑙营的无声杀戮:外表正常的女人、孩子、老人,穿着自己的衣服走下火车,被送进“浴室”就再也没有出来。灭绝营就是一条专用的屠杀流水线——火车源源不断地将犹太人从各地集中营运来,只需两三个小时,一整列火车的人便可以被“处理”干净。纳粹集中营很多国家都有,包括德国本土,而6处灭绝营则全部在波兰境内:除了贝克瑙,还有切尔诺(Chermno)、贝泽克(Belzec)、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索比波尔(Sobibor)和马伊达内克(Majdanek)。在这些灭绝营都被公之于众后,还曾经引起过一个小的争议:奥斯威辛作为犹太灭绝的象征是否恰当?除了消灭犹太人的功能,被分成三大营区的奥斯威辛还是纳粹生产基地、战俘集中营和苦役营。相比之下,贝泽克才是完全意义的犹太灭绝营,在那里有80万犹太人被送进毒气室。特雷布林卡有120万犹太人。但是这几个营都被纳粹彻底销毁了罪证,没有残留档案,也几乎没有幸存者。一个没有了历史痕迹的地方怎么纪念?所以还是选择了奥斯威辛作为记忆的现场。
1961年,以色列特工将藏匿在阿根廷的纳粹战犯艾希曼(Eichmann)绑架回国受审,判处绞刑。在审判过程中,世界舆论第一次提到了“种族灭绝”的事实。之前的纽伦堡审判,尽管案卷如山,犹太人的战时命运并不是重心,但从审判艾希曼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犹太人遭遇了怎样不同一般的迫害,历史学家开始提出诸如“欧洲犹太人被灭绝境遇”这样的课题。
在“艾希曼审判”之前,犹太人自己同样也在回避灭绝记忆。对于他们保持沉默的心理,历史学界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犹太人已经成为被迫害的对象,所以他们不愿再成为被哀悼和怜悯的对象;另一种则认为:如果无人听说犹太人的苦难,那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去听。但是中立和客观的学者,比如阿纳特,觉得沉默是战后犹太人和犹太社团基于实际的选择:他们希望能够尽快重新融入所在国家,恢复身份和归还财产,而清算战时遭遇在那些年并没有被大多数犹太人作为主要目标,对灭绝罪行保持沉默也被大范围接受。“艾希曼审判”是一个转折,中东“六日战争”则再一次让犹太人感觉到在世界上的身份危机,他们开始向“二战”纳粹种族灭绝罪行公开清算。
从上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人逐渐接触真相,80年代对种族灭绝行为的披露到达高潮,此后各种反思一直延续。随着时间流逝,还活着的亲历者已经只剩下当时的孩子,十四五岁或者更小。和战后搜集到的回忆性文字相比,他们的证词相对来说是苍白的,而且难免有很多是成人之后从别人描述中得到的印象补充。奥斯威辛仍然有无数的谜团没有答案。■
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
——一个幸存者60年后的反思
每一位幸存的犹太屠杀亲历者,都在用自己的姿态返身面对那场浩劫。有人做《苏菲的选择》,在无辜负罪的痛苦中,用拒绝个体幸福来为人性赎罪。有人如“猎手”西蒙·维森塔尔,毕尽余生追踪纳粹在逃战犯。有人是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煎熬11年,以镜头逼视灭绝营这些“被毁灭的毁灭”,9个半小时长度的纪录片每放映一次就是一次葬礼。还有人以德国哲学家阿尔诺为路标,在“奥斯威辛以后”的人类生存命题里寻找历史哲学和认识论的密码
“那年我6岁半,一天夜里被几个戴墨镜的法国警探抓住。他们把我推到门口,那里站满了拿枪的德国兵,在卡车前面排成一堵人墙……一个法国警探说,必须把我消灭,因为不久以后我就会变成社会的祸害……”法国著名的精神病学专家鲍里斯·西鲁尔尼克(Boris Cyrulnik)为《新观察家》杂志奥斯威辛纪念专题撰文,回忆童年的可怕经历。他父母在这次波尔多地区对犹太人的大搜查中被捕,后来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鲍里斯侥幸逃脱,和电影《美丽人生》中那个小男孩一样,孤零零地活在太阳之下。60多年了,他从未忘记过那个法国警察说的话,还有他说话时的神情。
现在鲍里斯终于可以告诉60年前那个惶惑不解的男孩了,他的同胞为什么要将一个孩子理直气壮地送向死亡。他在文章里说,“60年以后我想,他(警察)能够在240次大搜捕中连续消灭1645名成年人和239个孩子,一定是在服从发自内心的道德召唤。因为只有当服从被文化神圣化以后,一个人才能毫无罪恶感地杀害无辜”。在鲍里斯看来,服从可以令杀戮行为去责任化,因为这种行为已经被纳入整个社会体系之内。这种情境之下重要的是目标,过程无关紧要。组成这架社会机器的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在指定给自己的价值阶梯上攀援。服从的才能,帮助体系运转的天赋以及处理各种关系的技巧,将迅速决定他们最终处于阶梯的顶端还是底部。对于他们,重要的、能带来幸福感的就是攀援本身,任何微不足道的怀疑都将打碎梦想。这种幸福的参与使他们在一种恶的结构里顺从大流。比如纳粹灭绝营,它和人类过往的杀戮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现代技术和工业组织紧密合作的杀人系统,是特别讲究科学和效率的国家机构。据披露的历史档案,用什么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有一个时期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引起过生产比赛一样的竞争。1942年3月17日,纳粹专家维尔特设计的第一所灭绝工厂切尔诺开工,6间毒气室,每天最多可杀害1.5万人。3个月后出现了设在华沙东北的特雷布林卡营,它是维尔特设计的最大一所灭绝营,有13间毒气室,每天可处死2.5万人。维尔特在他的结构里是称职和高效的,对他以及集中营的工作人员而言,是屠犹还是生产没有根本差别,都是需要全力以赴表现才能的岗位。
鲍里斯认为,同为“服从”,也有不同背景之下的两种含义。当两方敌对,服从一方意味着承认失败。而个人对团体的从属却相反,它将服从行为高尚化了,一旦团队的灵魂人物提出了完美的清洗计划,服从者便会以人类的名义去参与反人类的罪行。鲍里斯还记得,送往集中营之前他和很多犹太人被关在改成了监狱的犹太教堂里,有个德国兵每天都到他旁边坐一会儿,给他看家人的照片,“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手势上我明白,他是想告诉我关于他家人和孩子的事情,那个孩子和我一样大,长得也很像”。但是小鲍里斯随即就看到这个慈爱的爸爸用枪托猛击其他几个孩子,因为他们上卡车的时候不够快。
法国被解放那天,戴高乐下榻波尔多大酒店,小鲍里斯被人带去给将军献花。晚上有个潜进饭店行刺的人被抓住,遭受围殴。这人一拳那人一枪托,暴力是一个缓慢而悠长的过程。那个人死了,被鲍里斯所敬爱的解放战士打死了。从那天开始他领悟到,人类境遇的核心就是双重性。
不带任何罪恶感地消灭某一个群体,过程永远都一模一样:先对这个群体实行去社会化,使之变得容易受伤害;然后是去人格化,用低等动物来影射这个人群,比如老鼠或者蛇蝎,使他们失去最后尊严;当那些万众景仰的人通过行政命令来实施最后一步时,置人于死地已经不会有犯罪感了,因为“消灭一群老鼠毕竟不是罪行”。而这种手段在人类的历史上,并非纳粹独有——这才是鲍里斯最想说的。■
党卫军:令人警惕的信仰
德国古老的鲁内文书写的两个字母SS,时至今日都是这个臭名昭著的组织的标志。这可能是纳粹政权中最为危险、最为有效、同样也是最为残酷的暴力组织。他的教父希姆莱甚至专门为党卫军设计了一种戒指,作为一种荣誉的象征。这枚戒指除了一个签名、一个十字,最令人难忘的是戒面上骷髅头的浮雕。在希姆莱看来,这种荣誉叫做忠诚。这种令人警惕的信仰,比暴行更容易被宽容和忽视
“二战”结束后,德国国防军的许多将领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纳粹党卫军的憎恶。在他们看来,战争中的杀戮是一种公平竞争中不可避免的流血,具有骑士精神的军人应该对屠杀战俘和平民的暴行感到羞耻。然而实际的情况却是,“二战”德国国防军的某些部队在战争中也做出许多同党卫军一样的可耻之事。正如最新的历史资料发现,国防军和武装党卫军的区别远没有人们常说的那样大。党卫军中的作战部队武装党卫军的士兵们试图证明,他们只不过是普通的战士,他们与那些在集中营里的党卫队毫无关系。然而没有人忘记希特勒在1941年进攻苏联之前曾对他三位国防军总司令,以及其他一些陆军指挥官强调过的话:“和俄罗斯进行战争不能讲骑士风度。这是一场世界观和种族对立的斗争,因此必须前所未有的无情。”
所谓前所未有的无情,在党卫军“突击部队”中被交代得很清楚,那就是跟进在国防军之后,有计划的在占领区搜寻纳粹信条中那些必须清洗的种族。虽然在战争后期,由于人数的缺乏,许多党卫军士兵属于被迫应征,这让他们对自身的无辜感更加强烈。但无可置疑的是,在纳粹的所有组织中,只有党卫军愿意执行希特勒残酷屠杀的命令。
在组织这个前所未见的嗜血组织时,忠诚这种道德伦理被当作一种政治宗教,成为建构党卫军组织的信条。党卫军人员的挑选如此严格,似乎让人错以为在挑选仪仗队员:年龄在23到25岁之间,必须有两人担保,身体健康,体格强壮,身高必须超过1.70米,更重要的是,必须是纯正的雅利安血统。这样精挑细选的小伙子除了进入党卫军的作战部队去侵略他国,要么就成为年轻的胸怀“纯洁”人种伟大任务的屠夫。
许多党卫军和战犯生前身后最喜欢谈的就是道德和素质。党卫军领导人海德里希就被认为是“无条件服从的一代人的先驱”,被纳粹人种理论看作是“理想新人类的代表”。他是个优秀的击剑运动员,还擅长游泳和滑雪。为了证明自己的勇气,他甚至学会驾驶梅塞斯密特109战斗机,并要求作为一个飞行员参加战斗。但在执行纳粹屠杀任务上的坚决和无情,让他获得了“布拉格屠夫”的称号。战后在纽伦堡法庭遭到起诉的德国党卫军基辅突击部队领导人布洛贝尔也没有任何后悔的表示。他依然和当时犯罪时一样具有强烈的优越感。他甚至令人发指的认为,那些党卫军的刽子手“神经受到的伤害要比那些被枪杀的人厉害得多”。他在临终遗言中说道:“作为军人,我遵守纪律,忠心耿耿”……现在纪律和忠诚却将我送上了绞架。
不仅仅是年轻人被训练成野兽。在1942年到1945年期间,党卫军部队还接收了3000多名德国妇女,并按照“领袖”的意志将他们培养成为具有“真正的信仰、国家社会主义的世界观和党卫军精神的女性党卫军兵团”。奥斯威辛-比尔克瑙集中营和卢布林-马伊丹尼克集中营的两位女性典狱长就因为残酷的暴行在战后被盟军枪决。但战争结束五十多年后,当有人问一名曾经担任集中营看守的女性党卫军成员赫尔塔·波特是不是做错了时,她却回答:“我错了吗?没有。错误只是存在集中营。”
参与暴行的不仅仅是个人。许多德国企业在战争中也通过残酷压榨那些集中营内的囚犯而获取暴利。许多企业光是为了使之投产就要付出上万人的生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当时的企业今天仍然是风光无限的跨国集团。也许他们也能够像赫尔塔·波特那样,认为错误只是自己生错了时代。
许多人认为,如果没有战争,如果没有国家对他们的要求,像海德里希这样的德国人也许会作为一个工程师平静地度过一生。半个世纪过后,当集中营的土地被修剪整齐的青草覆盖时,一种新的情绪在和平的空气中萌生。某些经历暴行却得以安然度过余生的人认为,他们在战争中只是为国家尽了义务。至于义务本身,每个人都可以认为那不是他能够考虑的事情。对此神学家鲁本斯泰因曾经写道:“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成魔鬼或者变态的人,这很吸引人。因为这种观点保护了我们对自己的幻想。如果我们将国家社会主义者当作或多或少普通的人,这并不表明我们原谅他们的行为或低估他们带来的危险。相反,这意味着我们认识到,道德和正直让人类集体免于彻底崩溃的束缚是多么弱小。”■ 遗忘纪念纳粹集中营军事历史之间党卫军女集中营犹太民族奥斯威辛种族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