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们终于开始为人民服务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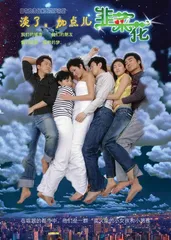 ( 戏剧《淡了加点韭菜花》海报 )
( 戏剧《淡了加点韭菜花》海报 )
将于1月27日在北京北剧场上映的戏剧《淡了加点韭菜花》的海报非常“眼熟”:包括毛宁和瞿颖在内的6名演员相拥着躺在蓝天白云之间——没错,这就是那部捧红了性感明星布莱德·彼得的老婆的著名肥皂剧《六人行》的经典造型。不过令导演田有良郁闷的是,在宣传中,他不能再拿《六人行》做宣传点了,因为另一部在1月3日结束了第一轮演出的戏已经打出了《翠花快乐六人行》的旗子,而这部《翠花》其实是他在2002年春节前推出的《翠花,上酸菜》的第4版。同时,他在2003年推出的《想吃麻花现给你拧》的第2版《麻花2:情流感》也正在北京海淀剧场上演——田有良在2002年1月提出的“贺岁戏剧”,在2005年的1月,迎来了一次“全面引爆”。
“贺岁戏剧”只是一个与时间有关的商业噱头——无论是《翠花4》还是《麻花2》,很难不让人产生这种印象。《翠花,上酸菜》里尚不失校园青春气息的“释放自我”的表演方式到续集里已经扭曲成了靠作践演员取悦观众的最低级的搞笑方式。在《麻花2》里,刘孜必须要靠把自己的身体扭成麻花以及和另一位女演员比赛抖动胸部才能赢得观众的掌声和笑声,而另一位演员则不得不频繁地扑地叩头。《麻花2》里的多位演员来自中戏的相声大专班,他们非常不忘本地在戏里表演——毋宁说是炫耀了相声里的绕口令技巧,但可惜他们同时也继承了曾被侯宝林和马三立老先生狠狠批评过的靠“出洋相”来博取“廉价笑声”的“传统”。或许喜剧是一门“审丑”的艺术,但真正能打动人心的喜剧永远建立在观众对演员和戏剧的敬意之上,何况这“喜剧”里的笑料和包袱牵强到好像是先有了一堆零散的肉,再为了把这些肉整在一起而造了一个七零八落的骨架,用“加长版小品”来形容显然更为合适。
《麻花2》的导演邵泽辉在请人来看戏的同时一再强调:就看个乐子。邵泽辉说他排戏的过程中和出品公司发生了多次争执,而争执结果就是他几乎砍掉了所有表现人物内心细节的戏和严整的故事结构,大部分的笑料和包袱被保留了下来。到演出开始,他已经变成了一个“不在乎评论家说什么”,只关心看老百姓是不是笑了,承认自己“就是在打工”的导演。他说:“我知道你看不下去,但是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就只能在这儿,再复杂一些他们就看不懂了。”
再“复杂”一些,老百姓真的就看不懂了么?打着“时尚M剧”旗号的《翠花快乐六人行》原计划达到1000万元的票房,却在演出30场,票房还未达到100万元之后停演。尽管有“明星地址黄页”、“比刘翔还跑得快”这样的“时尚笑料”,还有“M剧”这样的时尚概念,但许多观众在出场之后表示,笑料老套、人物关系混乱让他们看得“不知道在说什么”。
“环境发生了变化”,“从前的先锋导演可以以在小圈子里出名而出名,而现在即使是国家院团都开始讲排戏的成本和利润”。在采访中,曾是“先锋戏剧”“铁托”的邵泽辉这样解释他接下《麻花2》的原因。很显然,大家都已经开始意识到了为人民服务的必要性,但未必都搞明白了人民是谁,人民的欣赏水平究竟到了什么程度——当然,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无可避免地存在着投机,有时候是有意,有时候是下意识。
 ( 戏剧《麻花2》剧照
)
( 戏剧《麻花2》剧照
)
田有良说,三部贺岁戏下来,他树立了这样一个观念:观众是谁?观众就是你,就是你爸爸妈妈;就是我,就是我爸爸妈妈。创作人员和观众在智力和情感上都是平等的,你尊重观众,观众才会被你感动。在创作的时候如果抱着观众是傻瓜的想法,演出现场观众就会笑得非常不舒服,觉得自己笑了也是傻瓜。
《韭菜花》有一个细节:妹妹给足不出户搞创作的诗人哥哥送饭,诗人在屋内有一个回应。最初,田有良安排诗人的回应是“狼嚎一声”;演员和看排练的人都笑了,但他认为笑声不对。现在,他安排诗人很“酸”地给妹妹念诗:“妹妹,你是这世界上惟一的孤儿。”他说,尽管还不太理想,但路子比较对了。《韭菜花》的结尾,诗人忽然看到了操持家务的妹妹的记账本:今天收入8块钱,给哥哥花5块,我3块。诗人一下子“从天上回到了云端”,发现自己所谓的“理想”不过是一种“自私”。田有良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象征意味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