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拍卖:十年走了多远?
作者:曾焱(文 / 曾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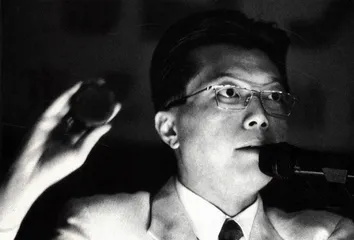
拍卖师郑晓星
为何十年才一拍
时隔十年,拍卖师郑晓星成了对接两次拍卖会的一个历史性符号。记者请他比较一下两次主拍的感受,他非常技巧地回答:“1993年是一次实验。”
在一些评述10年前那次文稿竞买的文章里,郑晓星被认为是最大的受益人之一。1993年10月28日之前,他只是广东省拍卖业事务有限公司的地方拍卖师,而在这之后他的名字和照片登上了国内外大小媒体,变成了被全国各地拍卖会竞相争夺的“中国第一槌”。到现在,郑晓星仍然保持着频繁的曝光率,操持1993年文稿竞买的总策划人王星的名字却已经基本从媒体上淡隐。王星当年的职业身份是《深圳青年》的普通记者,但是从活动立项到最后完成,背后不难看见当时深圳市有关部门力促这次创举的作用力。一篇署名汪延的文章是这样记录的:王星有了成熟的想法后,和《深圳青年》当时的社长王京生沟通,对方立刻看到了其想法中所蕴涵的历史性意义,同意以杂志社的名义作为主办单位,只是要求王星独自承担活动的运作经费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运营风险。活动章程序言随后就在《深圳青年》上发表,作为当年在全国青年中很有影响力的一本杂志,显然不可能为一个完全个人意义上的策划行为刊登一篇宣言式的东西。现在回头找到这篇文字,依然可以从一些句子里读出那个年代最流行的悲壮感——“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出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经济腰杆,流通起来”、“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声,将声透五千年,声动千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从字面上看很明显,王星等人.意在对观念的挑战似乎远远大于交易形式的完善和建构,这也比较符合当时深圳作为全国新思想生长土壤的定位。《深圳青年》以杂志社的名义向深圳市团委、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报告,当时的深圳市委副书记林祖基批示“这也是一项改革”,观者不难理解为市委市政府对于文稿竞买意识形态上的认定。这一出发点决定了后来王星出面所做的大量幕后工作势在必行:尽管是实验,已经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为了保证卖方也就是愿意参加拍卖作家的数量和质量,王星花半年时间所做的工作大部分超出了商业框架:第一,他以“此次活动是一次全国性的以社会效益为主的非赢利性的探索实验”为理由,向深圳市税务局申请了免税,意味着参加拍卖的作家将名正言顺不用交税;第二,太平洋保险深圳公司为参拍文稿提供保险,即使流拍,也能保证作者得到基本稿费收益;第三,拍卖公司免费主持拍卖,免除佣金等等。而对于买方——基本上锁定为企业,王星也在10月28日的现场拍卖前做了大量铺垫,比如后来被报道为首开记录、以8.8万元竞买了两部作品的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就是由王星等人做了大量细致的“预售”工作,而在场外成交后,主办方还专门为该公司现身说法,请了很多企业家,目的是感染和说服他们效仿。现在来看这些细节,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令人其敬,但从商业操作的角度就并不那么正规。
如果仅从交易的表面数据来看,十年后由深圳文博会主办的这次拍卖会并没有超越十年前的竞买:1993年的公开竞买,9部作品全部拍出,拍卖总额为300来万元,其中女作家霍达的《秦王父子》拍出100万元高价,报告文学《深圳传奇》88万元,刘晓庆的一个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也拍了17万元。而这次刚刚落槌的剧本拍卖会16部作品流拍5部,11部文稿总拍额接近600万元,单部最高成交价100万元也没有超过十年前的纪录。十年前参加拍卖的作品有顾城、谢烨的《英子》,有名作家史铁生、张抗抗、霍达,此次拍卖除了梁晓声的剧本《红磨房》——而且只拍出13.5万元——作品拍出最高价的剧作家姜一和十年前的名家相比,在名气上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从纯粹交易的角度,文博会承办办公室主任叶建强接受本刊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认为,“拍卖的成功超过我们的预期”,“文稿市场比十年前成熟了很多”。据介绍,这次拍卖在一个月内征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部作品,卖方基本属自发形成,虽然在质量上有待完善,但一定比例的流拍说明买方也是比较理性和市场化的。在开拍前,郑晓明按照拍卖程序宣布收取3%的佣金,拍卖结束后他告诉本刊记者,原定的莫言作品之所以在此次拍卖中缺席,原因是对方提出的底价在拍卖行对市场进行研究之后,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会在以后作另外的安排。拍卖公司在此次拍卖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显然也比十年前更加重要和更加符合利益准则。
拍卖是适宜文稿交易的方式吗?
也许正因为没有确立一个规范的商业赢利模式,1993的深圳竞买在产生了巨大社会轰动之后,并没有激励后来人,拍卖公司也没有从中看到可操作性。在11月19日下午的此次拍卖结束之后,主拍的郑晓星向本刊记者承认:“如果没有深圳市委市政府参与,拍卖行可能仍然不会主动举办这样的拍卖会。”
深圳市拍卖行有限公司的周垒告诉本刊记者,无形资产拍卖是操作难度最大的一个领域,除了股权拍卖、广告段位和冠名权相形之下比较普及,其余都门槛很高,事先需要大量的市场调查,分析得利可能。只有在买方市场远远大于卖方市场的时候,拍卖才会有可行性。北京“2000年书稿交流会”遭遇交易寒流就是一个例证。据当时的报道,主办单位北京市版权局版权管理处统计有近300名作者、600余部作品参加书稿交流会,但总共成交少得令人吃惊:5部签约,41部达成意向,不到全部参会作品的10%。按照主办方的估计,“书稿交流会”是一种透明的交易方式,应该会聚集一定人气,但是业内人士分析,成交量主要由书稿整体质量决定,出版社对作品的要求比较高,而参会的绝大部分是业余作者,整体水平有限,真正有名气的作家很难主动选择这种交易方式。至于出版社,一个是对培育新作者缺乏耐心,另外冒险判断市场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同样的情况在这次深圳拍卖会上也有一定表现。流拍的五部作品90%为不知名作者参拍,比如深圳一位年轻作者在拍卖会上推出自己已经发表的11部长篇小说,开出的改编权底价总共只有10万元,但仍然无人应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参拍买家表示,对于这样知名度不高的陌生作者,公司很难下决心购买,虽然可能后面有巨大的利润空间。另一家以5万元拍得一个剧本的深圳知道文化传播公司,其总经理吴东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也坦率地说,举牌是因为开价实在便宜,而且事先也看过剧本,对市场风险有一定估计。作为刚刚涉足影视制作的公司,他们觉得拍卖不失为一种公开和透明的剧本交易方式,存在用小成本挖到好作品的可能性,从某种程度上避免了违反市场规则的抬价。但是对于参拍文稿的整体质量,他表示仍然有所期待。
“下一次文稿拍卖还需要等上十年吗?”拍卖师郑晓星和文博会承办办公室的回答都是一样的:“肯定不会。”文博会承办办公室主任叶建强告诉本刊记者,深圳市委市政府有计划在深圳促成一个南方甚至全国的文稿交易平台,每年举行一到两次的竞买拍卖会,为文化产品市场规范化提供支持。如果准备充分,明年上半年深圳将再举办一次文稿拍卖,拍卖范围将从影视剧本扩展至其他文学作品比如长篇小说。郑晓星也透露,拍卖行业对这类交易的市场培育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