绑架事件的中国背景
作者:朱文轶(文 / 朱文轶)
以马苏德为首的武装绑架分子
我们并不安全
在解救中国人质的过程中,绑匪所属及人质滞留地的部族首领迅速配合巴政府组成谈判团,参与谈判。到10月13日,表示声援的部族首领越来越多。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部族长老的权威向来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他们给绑匪施加了强大压力,来自绑匪首领马苏德部落的一些长老甚至给马苏德本人打电话说,除非他释放两名人质,否则整个部落都将遭难,而且他本人还将面临部落处罚。坦科城的大部分商店也以罢市来抗议绑匪对中国工程师的绑架。“因为国家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威望,来自巴政府和民间的友好,的确让我们意识不到自己会受到恐怖主义的袭击。”曾在巴基斯坦居住过多年的巴问题专家——中国社科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张玉兰说。
张玉兰说,多数巴基斯坦人对美国对他们的“实用机会主义”态度一直抱有不满,对在巴的中国人则格外亲近。“‘9·11’后巴基斯坦为反恐事业做了很多工作,但当印巴边界局势紧张时,美国却非但没有发挥作用,反而谴责巴基斯坦,因此,很多巴基斯坦人都认为,美国总是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抛弃他们。”

王恩德
张玉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两次到过巴基斯坦,她说,巴基斯坦曾经发生过针对中国工人的俾路支省铜矿绑架事件,“把人绑到了阿富汗,后来由沙特阿拉伯长老出面斡旋,交了赎金,人质很安全”。其后也发生过一些零星的绑架事件,国内都没有报道,“但那些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钱。但这次绑架事件却有明显的政治背景。那些被‘美巴联盟’激怒的恐怖分子,专找最让政府头疼的问题来跟政府叫板。”
对中国人的态度成为可以让政府头痛的要挟之一。张玉兰分析,今年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分子频频袭击中国人,原因之一是,伊战后,那些和伊斯兰世界矛盾加深的国家出于安全考虑,大多提前撤走了他们国家的工程人员,而中国人自认为安全系数最高,留在巴基斯坦的最多。中方目前在巴的各类项目有几百处,受攻击概率较大。二是中巴关系友好,为了为难巴政府,恐怖分子选择中国人作人质或袭击对象有意影响中巴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金灿荣说,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中国人在世界大多数地方与恐怖主义绝缘的时候,在巴基斯坦一年之中却密集地发生了3次”。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小强认为,在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由于局势不稳定,已经成为高危敏感地区,“这些地区的恐怖和极端势力借助非常规手段,譬如乱抓滥杀外国人等,来达到其他途径无法达到的目的。因此有针对性或偶然性的突发事件随时可能发生。”前联合国人质问题特使詹多梅尼科·皮科说:“这些人不怕被抓住。对他们而言,下场如何并不重要。”“要么达成交易,要么杀人质:对他们来说,两种结果都不意味着失败。而在其他多数绑架案例中,通常一个结果是好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坏的。”皮科曾在上世纪80年代成功说服黎巴嫩真主党释放人质,他将这些人称为“战略恐怖分子”。
傅小强说,另外,随着中国在海外投资和援建、重建项目的增加,中国企业与当地一些个人的经济利益也可能发生冲突,“三年前菲律宾的中国人质事件,也有一种猜测是,绑匪受人雇佣,企图逼走中国电力技术进出口总公司工程人员,停止即将完工的总价值高达30亿比索的水坝工程,以使其他建筑公司接管该工程”。
“非传统安全”时代的新思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认为,巴基斯坦人质事件应区别于传统的安全观念。他说,“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是主权的安全;而“非传统安全”挑战的不一定是国家,也不一定是国界,它挑战的可能是个人,或者一个大区域。全球化使这种“非传统安全”更有突发性,影响范围更宽广,层次更模糊,并几乎开始改写国际关系与国际战略的定义。“这迫使我们必须打破从前的研究范式。对‘非传统安全’,国家只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同样很大。我们还要重视个人的安全与权利。公民的知情权实际成为面对这种新问题的一种必须措施——只有每一个人都了解,‘非传统安全’才可能被克服。”
这是许多时候我们觉得恐怖主义或者某些个体的人质事件离我们很遥远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过去在体制上与观念上都对此没有做好准备。”王逸舟说。现在,这种“非传统安全”以越来越多样的面目出现,越来越广泛的国际恐怖主义是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因为它们的突然性与复杂性,常常使一国政府陷入无能为力之中。
“中国以前缺少相应的观念。”王逸舟相信,我们传统的国家动员方法,只靠政府来解决所有问题,正如基辛格所说“外交是少数人密室内的事情”,它某些时候异常有效,但面对人质事件这些新问题,它会让许多人有置身事外的感觉,“普通公民会不满于信息屏蔽,好像解决问题只有国家,但其实许多事情都是只依靠国家力量无法解决的”。

在菲律宾,规模较小的武装组织阿布沙耶夫将绑架变成一种“产业”。图为警方抓获的阿布沙耶夫反政府武装分子
王逸舟说,“邓小平时代的工作重心是搞好自身发展,非常实用。在那时,我们很少讨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义务与责任、在地区一体化中的角色。我们知道自己在‘经济全球化’中位置却忽视了‘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的参与。现在,‘负责任大国’、‘崛起的大国’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领导人和外交家的表达中。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已经在世界上扮演更重要角色,作为中国公民在海外的现状也发生了变化。”金灿荣补充说,从国家来讲,应该继续保持有道德、有正义感的软形象,政府应该继续加强与大国和地区有影响国家、国际组织之间在反恐问题上的沟通,“对于海外安全的客观现实,有海外建设项目的公司首先要在选择项目时,不仅做经济评估,还要对当地的安全性和政局稳定性进行认真评估。项目开展一定要紧跟安全保卫措施。在进入他国前,应尽力回避有威胁的地区,外交部门的工作当然更为重要。”
这也许是中国政府新思维的开端—一如何以更主动的姿态强化国家形象,将保护海外公民的安全提高到一个新的角度。“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在朝韩问题、印巴冲突上开始扮演越来越积极的角色。”王逸舟说,“这是一个积极的延续。”
“传统安全”是国家安全,主权安全;“非传统安全”挑战的是个人,或者一个大区域
今年系列人质事件关键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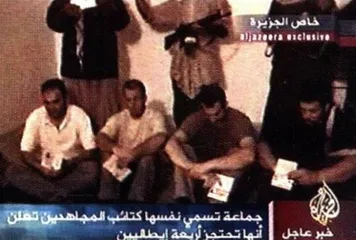
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是报道处死人质的第一个媒体。卡塔尔的半岛电视台4月15日突然收到了一盘录像带,编辑首先将内容大致浏览了一遍,看得心惊肉跳:这是纪录处死意大利一名人质过程的录像,被处死者是36岁的法布里特西奥·库亚特罗基。武装分子还通过录像带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他们之所以杀死人质,是因为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此前拒绝将2700人的意大利军队撤出伊拉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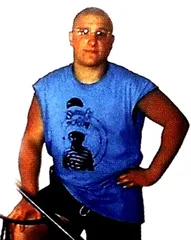
斩首录像
2004年5月11日,一段斩首录像被上传到互联网。被斩首的,是26岁的美国商人尼古拉斯·伯格。这是第一个被公开斩首的人质。此前,他在伊拉克遭到绑架。伯格的父亲接受美国电台采访时说“我的儿子是因为乔治·布什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罪过而死的。”当然,没有政治因果不成其为恐怖主义,这也是产生恐怖行为最主要的原因。然而,不幸的是,这种想法也在被绑架者、他们的亲人以及许多普通民众中引起了部分共鸣,被他们以另一种方式加以解读。这种情绪也加剧了泛恐怖主义的扩大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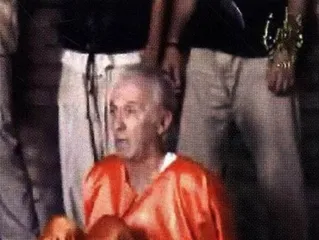
英国人质比格利
比格利是伊拉克人质事件中最悲剧的人物,他的生死在一个月内一直为人关注。比格利是9月16日同两名美国人一起在巴格达遭绑架的。绑架者提出条件,要求释放被关押的伊拉克女囚犯。随后不久,绑架者处死了两名美国人质。而9月22日,一家伊斯兰网站播放的录像画面显示,上周在伊拉克被绑架的英国人质比格利还活着,他呼吁英国首相布莱尔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尽力帮助挽救他的生命。27日晚上,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出面表示他正在努力与绑架比格利的那些人取得联系,在英国首相布莱尔势难向绑架者妥协的情况下,像阿拉法特这样的重量级政治人物出面干预此事,这让比格利的命运转机有了一线希望。在9月28日一批人质被释放后,英国天空新闻台10月4日报道,英国人质肯·比格利的兄弟保罗·比格利说,肯已经被移交给了伊拉克的另一个叛军组织,肯被转移以后,可能达成交赎金放人的协议,许多人对比格利的命运都开始抱有乐观态度。10月6日晚又有戏剧性变化,英国军情六处(Ml6)用巨额酬金买通了两名绑匪帮助比格利逃跑,而且比格利也成功脱逃达半小时之久,但最后还是被绑匪抓回。10月9日,比格利还是在位于巴格达西南35公里处的拉梯费耶镇被斩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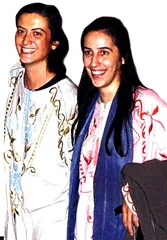
托莱塔和帕丽
9月28日人质“大赦”
9月28日,伊拉克绑架者“一反常态”地先后释放了10名人质——其中9月7日被绑架的、为一家援助机构工作的两名意大利女子托莱塔和帕丽被释放,随后两名法国记者被释放。这被视为在国际社会努力下人质危机缓解的征兆,而也有国际专家认为,两名意大利人质在伊拉克的工作属于救援活动,并不是在为联军服务,这也是她们被释放的一个原因。而埃及人质更和联军没什么关系,埃及在伊拉克并没有派兵,但危机并没有缓解。



俄罗斯别斯兰人质事件
9月1日早上9点(北京时间13时)刚过,身穿黑色衣服、头戴面罩的武装分子闯入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的学校,将刚参加完开学典礼的学生、家长和教师赶进学校体育馆劫为人质。武装分子与赶来的警察交火,造成人员伤亡。当地时间9月3日下午1时刚过,俄罗斯紧急情况部工作人员得到武装恐怖分子同意,开车进入学校收集9月1日上午绑架发生时被害人质尸体,爆炸声突然响起。人质以为爆炸声是营救行动开始的信号,开始逃跑,武装分子以为强攻开始,特种部队则以为是恐怖分子开始屠杀人质。强攻解救人质后,人质死亡人数不断增加,最终逼近400人。其中有100多名是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