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通一代”10年梦
作者:舒可文(文 / 舒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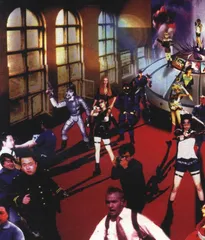
《11.17恐怖事件——虚拟人类的第一次宣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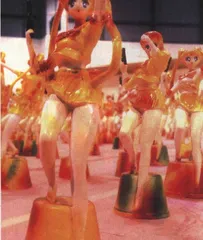
《中国楚河汉界——美少女大战变形金刚》
“卡通一代”是广州一个艺术群体对他们作品的命名。1994年的时候,商潮涌动,广告形象、卡通人物、玩酷时尚带来了一整套的新时代视觉符号,顺带着是一整套的生活理念。这些理念心悦诚服地遵循者来自伴随其成长的一代,黄一翰、响叮当等艺术家把他们作为卡通一代,并以他们的趣味和兴奋点调整了自己的创作。于是麦当老成了他们的“叔叔”,米老鼠、加菲猫成了他们的“兵马俑”,“楚河汉界”两边大战的是美少女和变形金刚,所有针对青少年的商业文化产品都是他们取材的对象。后来他们在上海、北京、广州、贵州、海南等地走访20岁上下的青年,做了上万份调查,概括出101条有关卡通一代的生存档案,这个档案所指向的趣味似乎更加强了他们制作“卡通一代”作品的依据。
这个人群看上去是一个个无阶级的形象,身着个各色懒散的服装,头发的颜色只要不是天生的,什么颜色都行,高声宣称自己是长不大的孩子,好像对当权派的成人世界看也不看一眼,实际上被商业当权派实实在在地牵着手。
而“卡通一代”作品的制作方式看上去也是无规少矩地全无界限,样式上有行为、表演、绘画、诗歌,制作招贴,像批量生产的商品一样,他们的制作方式有一部分采用大量的图像排列,或军团般的装置复制,的确是这个乱哄哄年代里的采样标本。
到现在已经有10年时间,他们把十年来的作品结集到一个巨大的书本中,不知是对十年的总结,还是预备告别,在现代语境中,尤其在中国,十年已经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了,夸张的表述中,已经出去两三代了,今天的卡通一代能涵盖多大的人群?今天的卡通之意味所在还能与10年前相比吗?这些最表面的变化都需更细心的观察。
10年中,“卡通一代”参加了各种各样的展览,但更多的人认识他们是通过他们邮寄到各方的招贴,不管他们是否认识你,你都可能在某个时候收到他们的邮件,如果对这个艺术群体完全不了解,收到邮件时基本上会对那些拼贴了五花八门图像的招贴略感莫名其妙,这些图像都来自商业文化,其视觉效果与街头广告、时尚小报插图是如此地统一,与他们所针对的所谓卡通文化现象一一对应,所以,收到他们的招贴,观者实在难以区分它到底是商业文化的宣传品,还是“卡通一代”的所谓作品。
艺术从商业文化中寻找灵感的努力并不始于他们,60年代的美国波普艺术早已经开始了,“卡通一代”延续的方式还是波普的方式,不同的是美国波普以安迪沃霍为代表对商业文化不冷不热浸身其中,其区分于商业文化也就是这份不冷不热的漠然,而“卡通一代”总给人以满怀热情的印象,至于这种热情来自什么动机,它针对的目的是什么,一般观者不大容易辨认。
有批评家评论说,他们工作是对卡通文化的追问,并且揭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这需要怎么样的专业能力才能对此有所感悟,如果它的这种追问只有批评家能够解读得出,那怎么能又说它是融入大众文化的呢。而对于正在发生的变化,扑面而来的商业文化制品显然已经提供了足够铺张的渲染,再麻木的人也不会对这种迅猛的变化无所知觉,何需美术馆里展览来以这样的方式“揭示”,难道真像维特根斯坦讽刺的,同一份报纸买两份,我们才能知道报纸所说的事?所以,对批评家所说的这种“揭示”不免心生疑惑、继而对所谓“追问”也警觉起来。
或许“卡通一代”的艺术家们并不是这么想的,他们也许就是要抹杀艺术与商业文化之间的种种区分,那么,既然已经有了无论在制作能力还是传播能力上都比他们更为强大的卡通文化,卡通一代艺术的独立性在什么地方?如果没有独立性,那么它的合理性只能是以他们的制作超越商业文化制造的图像,但是这种“以夷制夷”的招数能有几分胜算?
因为有对现代主义发展观的预防针,所以在涉及到“卡通一代”的时候,批评家们在文章里表现出的怯懦使他们的文字大多语焉不详,很少有人愿意对此做出有价值的肯定判断,但也并不作出否定的判断——闹不好,它哪天会波及世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