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艺谋的女性美学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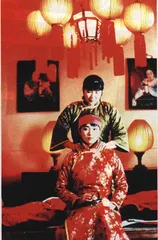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剧照

电影《秋菊打官司》剧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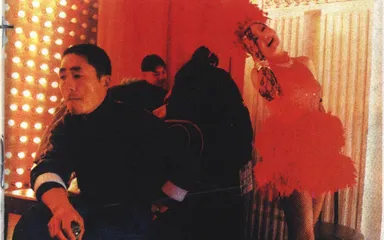
张艺谋执导影片《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幸福时光》工作照
在《十面埋伏》的宣传过程中,张艺谋始终在强调,这是一个关于男人与女人之间的爱恨情仇故事。这是一个相当有诱惑力的说法,众所周知,“情仇荷尔蒙”式的电影是他的长项。张艺谋自己也说:“没有一男一女的故事就好像欠点儿什么。”尽管张艺谋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曾声明:“我从未拍过一部只有男人或只有女人的电影”,但在张艺谋最重要的电影作品中,女性角色总占据着重要地位,在美国,很多学者和学生以他的作品为文本分析当代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演变。20世纪90年代,张艺谋曾一度被欧洲影评家认为是中国的“女性导演”,尽管这一评价并未得到他本人和中国影评家的认可,但已被公认的事实是,在其电影生涯的前半段,他从巩俐身上获得的灵感和创作激情,是他作品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其后,他也曾试图在章子怡和董洁身上延续这种感觉,这构成了他本人的局限性。有趣的是,当他在局限之中努力的时候,他是个真正的大师;而当他试图突破自己的局限时,却总显得笨拙。
一根筋的性感
张艺谋并不像其他导演一样强调女演员的漂亮,无论是巩俐、章子怡还是董洁,都是经张艺谋塑造后成为的美女,但观看过《红高粱》、《菊豆》、《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的人都会承认,张艺谋电影里的女性,有一种别样的性感。
《英雄》、《十面埋伏》的编剧王斌介绍说,张艺谋在想到一个电影的时候,最先想到的不是故事,而是一个性格,以及这种性格的人可能会呈现出来的画面。通常,这个性格会是我们俗话说的“一根筋”、“倔强”、“反叛性”。“张艺谋是喜欢这种性格的,对他来说,具有这种性格的人物的重要性甚至超过故事。”为了表现这种性格,张艺谋经常会改变主人公在原作中的形象,甚至改变故事。比如,在《秋菊打官司》中的原著《万家灯火》中,女主人公并非一个孕妇。但张艺谋将秋菊设置成一个最具乡村农妇特征的孕妇,因为孕妇的行动会比别人慢半拍,动作的缓慢正好可以更好地表现出那种倔强和刚强。一个孕妇的倔强和刚强显现在胶片上的时候,将非常有张力和戏剧化。对于这个改动,直到现在,张艺谋都很得意。
《冬至》的导演谢东自1994年《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开始担任张艺谋的副导演,到2000年《幸福时光》拍摄时,他已经成为张艺谋电影的第一副导演,从《摇啊摇》中的儿童演员水生、阿娇,到《我的父亲母亲》中的章子怡,再到《幸福时光》中的董洁,他见证了许多张艺谋挑演员的场景。他也认为,张艺谋挑演员重视演员的性格气质超过了外貌。比如《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中的两个小演员,是从14万个孩子中挑选出来。最终选中这两个孩子,是因为他们身上的两种气质:“一个就是倔,一个就是灵。倔,是执著,是有爆发力;灵,是聪明,眼睛里有股灵气儿。”《我的父亲母亲》最初挑选演员时,还是中戏学生的章子怡无论在演出经验还是外形上并不占太多优势,但在试戏中,谢东和章子怡演了一场对手戏,他发现,章子怡的领悟力相当好,导演说一种感觉,章子怡能一下子用几种不同的方式表演,而且有一种强烈的爆发力,以至配戏的他觉得有些承受不住。
对爆发力的强调始终是张艺谋对演员的要求。《幸福时光》的一位副导演在回忆拍摄现场时说,有时候董洁会闷在场上出不了情绪,如果别的导演可能会等待她慢慢酝酿情绪,但张艺谋会说,停,我要爆发力。
对女性角色的倔强和爆发力的追求使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始终呈现出一种有别于其他女性形象的魅力。张艺谋电影是一种荷尔蒙味道极浓的电影,几乎每一部电影都要强调一种不受束缚的野性和急待发泄的欲望。在他的很多作品里,都选择女性来作为他野性和欲望的出口,所以,我们会看到大量从开始的平静压抑到后来岩浆进发不可收拾的女性欲望想象,从九儿到菊豆,从招娣到小妹。
清华大学传播系教授尹鸿在总结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中认为:“张艺谋电影中的女性形象具有主动性、感性和张力,他偏好塑造‘冷美人’,她们在影片开始总是不苟言笑,但具备极强的行动力,而冷美人的突然爆发,是非常有魅力的。”
男性在看,看得并不明亮;女性在被看,被看得充满狎昵;这是男权社会主流语境下永远的表现方式
徘徊在秩序边缘的暴力对象
在谈到为什么大部分电影都以女性为出口的时候,编剧王斌说:“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男人是社会的中心,女人处在社会边缘,其呈现出的下意识反叛,以及在意识到自己的边缘性之后所采取的反抗是相当戏剧性的,而女性天生的感性、主体道德感的缺失也将会使电影里的戏剧冲突更为人性。”
可见,对女性的观赏,依然是张艺谋的男权视角以女性为重要角色的原始考虑。在视觉上,女性一次又一次被强迫式地置放在一个被观赏的境地:《红高粱》一开始,在男性声音的讲述中,九儿的特写逐渐浮现,九儿的脸被框定在银幕画框之内,形成一个典型的讲述与被讲述,看与被看的关系。在角色选择中,张艺谋首先考虑的是角色胸的魅力,那种对胸的颠荡的强调是被看的典型表现。在《我的父亲母亲》中,同样的场景再次出现,当叙事性极强的音乐响起,招娣的脸在花丛中一次又一次微笑着出现。摄影师侯咏在回忆当时的拍摄场景时说,张艺谋当时制定的摄影宗旨就是“美景加美人”,“张艺谋说:我们用的是宽银幕摄影机,要敢于拍摄人的大特写。演员都是十七八岁,正当年,不需要去掩饰什么,要展示他们的青春,包括皮肤的质感”。
男性在看,看得并不明亮;女性在被看,被看得充满狎昵;这是男权社会主流语境下永远的表现方式。从《菊豆》中天青在菊豆洗澡时的偷窥到《十面埋伏》中金城武对小妹洗澡的偷窥,张艺谋的女主角或多或少都承担着随时作为欲望对象被强暴的紧张。
耐人寻味的是,不同于好莱坞式的结局,除去《一个也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这些欲望对象都是以悲剧收尾,那些一根筋而又性感的女主角,不是像九儿、菊豆、小金宝一样被某种力量毁灭,就是像秋菊一样落入一种茫然彷徨的境地,而这些,对曾经那样奋力抗争过的她们来说,都极为荒谬。但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这是一种必然的结局。
电影理论批评家戴锦华认为,不同于17年电影中对女性特点的回避,用男性的规范来要求女性;也不同于第四代电影中对欲望对象的剥夺,第五代电影重新提出并表现了女性的欲望和挣扎。但在这里,男性的责任更多地通过视觉手段转嫁到女性身上,并通过女性的牺牲来确立男性在社会秩序和社会地位上的支配地位,达到主体逻辑和秩序的稳定。
尹鸿认为,张艺谋电影里继承了传统文化对女性的符号化:浪漫、感性;一方面,张艺谋电影通过对性别特征的视觉突出和“偷窥”等场景的安排将女性设置在男性的欲望场景中。另一方面,女性在张艺谋电影里远远不是看与被看这么简单,而是被安排为固定秩序的主要挑战者,同时接受挑战所带来的惩罚。这样,观看的男性就完成了一次“安全的冒险”:既达到了心理满足,又由于性别的不同而不必承担被惩罚的焦虑。”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这些一根筋又性感的女主角,总是被安排在大量的暴力场景中。《红高粱》中九儿一出现,就被置放在一群粗犷野性的汉子们当中,而九儿和我爷爷的第一场激情戏,是以九儿被粗暴地拦腰抱起开始,被以献祭的姿态放倒在高粱地里为结束。对此,戴锦华将之描述为:“倒在男性欲望的祭坛上,成为男性个体成人式辉煌的一幕。”
而在《十面埋伏》中,这种暴力场景来得尤为集中和猛烈:金捕头和小妹在牡丹坊第一次见面,镜头先展示小妹的一个大特写,接下来反打金捕头,完成一个欲望的观看与被观看关系。然后金捕头剑挑小妹外衣纽扣,完成了一个颇具亵渎意味的暴力场景。几分钟后,金捕头迅猛将小妹扑倒在身下,让人不得不想起《菊豆》中,菊豆和天青在染坊中偷情,以及《英雄》中梁朝伟将章子怡扑在身下的场景。
死,疯,茫然无措,远走他乡是张艺谋电影中女性最常见的结局。对这样的结局,编剧王斌的解释是:“女性的毁灭更能唤起人们对美的惋惜,使悲剧的结局更有力量。”而戴锦华则认为,无论是死、疯还是茫然无措,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在女人代替男人承担了罪恶,完成对秩序的挑战之后,彻底将女人排除在新秩序之外,成为“他者”——无关的人,或者祭品。所以,《摇啊摇》中,小金宝的死无法阻拦老大将新的小金宝带入秩序之中;《英雄》中,如月和飞雪也无法阻止李连杰和秦始皇达成和解。
作为女性的男性

电影《十面埋伏》剧照
在《英雄》之前,张艺谋的电影里的男性或女性总有一方处在缺席状态,女主角总是处在一种事先存在的关系中,这种关系是合法的,但又是相当古怪的。比如九儿的合法丈夫李大头是一个麻风病人、菊豆的合法丈夫是一个性无能,颂莲的合法丈夫连正脸都看不见,只是一个影子。这些人并不能像主流电影中的男性一样担负起重要的责任,他们更多是一种现存社会秩序的象征,这样,女性欲望的挣扎和描述实际上成为张艺谋的自我比喻。而在更深层次,在这样的一个中国故事中,由于强有力的男性角色缺失,这些电影的目标观众:西方观众,将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到这个缺失的地位,完成另一种层面上的看与被看。正如某影评人所说:“张艺谋的前期作品在西方的观众是这么一批人: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着星巴克咖啡,希望用观赏不同于好莱坞制造的电影方式来体现自己的品位。然后,他们看到了张艺谋的电影,希望有一天自己也能到那片未开化的土地上,遇到那些清纯而又充满野性的女子。”
而在《活着》和《幸福时光》里,葛优和赵本山饰演的角色实际上承担了其他电影中女性角色的功能:承担历史的命运并想办法活下去,直接成为西方目光的观看主体,完成第二重的看与被看关系。在这里,巩俐和董洁一样,是男性的陪衬,是视觉的调味剂,她们是外来人。张艺谋将她们的戏份从原作中的几乎没有安排成现在的平分秋色,纯粹是像莫言说的那样:“电影里没有漂亮女人还能看么?”
《英雄》之后的女性蜕变
如果说在《英雄》之前,张艺谋还在努力地进行着艺术个性和创作领域上上的探索,《英雄》之后,在商业逻辑覆盖下,张艺谋的艺术价值和个性开始变得含混不清。《英雄》不但使他开拓了国内票房,更使他的电影第一次能进入美国主流院线放映。《英雄》继承了他一贯的对女性的审美和对女性的态度,依然潜藏着他喜爱的那些元素:敢爱敢恨的红衣女子,对秩序的挑战,对命运的承担,对极致的浪漫主义的渴望。可是在商业电影规律下,他无法像在之前的作品中对人物的疼痛和欲望作深入描摹,对人物的关系作精心设置;人物让位给了场面,那些他曾用以自比的泼辣女子,退让成为单薄的符号和剧情需要的棋子。她们的活未曾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状态,她们的死也不再具备令人失望、压抑、愤慨的悲剧力量。而刺客无名和秦始皇则携手完成了一次对中国政治的权力想象。
《十面埋伏》作为张艺谋弥补缺憾的影片,在努力重新表现那种压抑中的反抗,矛盾中的激情;可是缺少了被压抑的寓言式的环境。在牡丹坊华丽而空洞的场景与绿竹林和白桦林铺陈出的美景中,在小妹心甘情愿而不是被迫为飞刀门复仇的前提下,反抗已经没有必要,甚至也无从反抗;爆发的激情显得突兀、粗莽而不合时宜;两个男人的争斗也就变成了一场心胸狭隘的闹剧。狂野没有了对象,刚烈没有了意义,性感也不复性感,观看的人也失去了想象和快感。显然,在《十面埋伏》中,张艺谋彻底丧失了对女性情感、心理,甚至欲望的把握,或许,真的如尹鸿所说:“商业化后的张艺谋已经丧失了艺术个性,有的只是艺术制作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