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墉:“娱己”,还是“娱人”?
作者:马戎戎(文 / 马戎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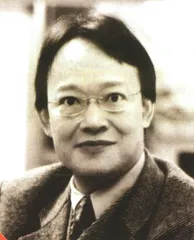
从传统眼光看,刘墉很难被称为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作家会像他一样,用12本书来教导你怎样“做人”。但从商业眼光看,刘墉则不折不扣是一个成功的畅销书作家:不算台湾地区,10年来,他在内地出版了60余种图书,销售量已突破300万册。今年3月,刘墉的最新作品《爱不厌诈》由接力出版社在内地推出,第一版印数即达6万册。像任何“特色产品”一样,刘墉和他的作品招致了很多争议,喜欢他的人认为他“深入浅出”,不喜欢他的人认为他的作品就是棒棒糖,小孩子一旦长大就不会再喜欢。在《爱不厌诈》一书的后记中,刘墉也第一次吐露了他的困惑:“写作这条路是艰辛的,一方面为了娱己,一方面希望娱人。于是求宠广大群众,或呼应少数知音,这两个目标就总在作家的心里拔河。”
三联生活周刊:《爱不厌诈》是你处世系列中最新的一本,你对自己的新书如何评价?
刘墉:在《爱不厌诈》之前,我写过很多书都是讲处世技巧,但侧重不同。《爱不厌诈》,讲的是在今天这个世界如何和所爱的人沟通、交流,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我身边的真事,故事里人的作为都有不诚实的成分,但都有自己的道理,我希望大家都能在从谅解的角度来看人性。
三联生活周刊:“诈”这个字眼在你的书里频繁出现,你似乎把它当成了为人处世的重要手段,你怎样看待“诚”与“诈”的关系?
刘墉:“诈”也是人性,小孩子从刚生下来,就会用高八度哭喊,要父母抱抱;再大一点会装头疼、肚子疼,要大人关心;你能说这种“诈”不对么?
在台湾,有人把我的书称为“刘墉厚黑学”。我其实一向主张以诚待人,但是我也主张,处世需要一定的技巧,如果你缺乏技巧,将不知如何自处,也会让他人尴尬。很多情况下,你要达到目标,不是暴跳如雷就可以的,要迂回前进。只要你到最后迂回的目的还是诚恳的,是鼓励大家向上的。
我儿子很小的时候,我带他出去玩。街边好多小贩会用各种手段诱使你买他们的东西,绝大多数时候,货物和承诺不符,但这是他们生存的需要。为了使我儿子用谅解的心来看这一切,我开始写处世系列:《看破人生的真相》、《把话说到心窝里》、《我不是教你诈》,都是写给他的,我希望他能辨别事物的本质,明白什么才是人生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也一直在强调:“诈”只能用于减少双方的尴尬,创造双赢的局面。
三联生活周刊:你的作品在商业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也有人认为你的作品不过是小孩子的“棒棒糖”,甚至是在迎合读者。
刘墉:我是不是在迎合读者,请看我的纯文学作品和专业的文艺理论书籍。有人有“棒棒糖”的印象,是因为我那些不是棒棒糖的文章没有在内地出版。
另一方面,我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纯文学的读者很少,少到不足以养家糊口。因此,我必须交错着保证我的读者群。我近几年每年出一本写情书,比如《爱又何必如此矜持》;再出一本处世书,比如《把话说到心窝里》;出一本纯文学,再出一本励志书。下个月我要推出我的另一本新书《爱原来可以如此豁达》。其实我所希望的是把我的思想理念,或是纯文学的理念通过“糖衣药片”传达给观众,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帮观众一步步带上来。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在作品里写你小时候是个性格冲动的人,但现在你好像把一切都做得很有技巧甚至到了“随心所欲”的地步。
刘墉:其实我到现在还是性格冲动。我对儿子生气时会把枕头往墙上扔,但不同的是我现在会很快平静下来。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我基本上也是这个发展脉络。四十几岁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五十知道了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接下去就是六十而耳顺,别人说什么都说好好好。
三联生活周刊:今年你55岁了,55岁的你认为对于一部作品,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对一个作家来说,理想的和作者的关系是什么?
刘墉:作品,最重要的是感动人,要能“直指人心”,而不是掉书袋。掉书袋只有在知识不普及的时候才会被认为是有文化。做人,要有散文的灵动,小说的变化,论文的沉厚,不能固守在同一种状态里,要做到不负我心,不负我生。作者和读者的关系,应该是若即若离,太不在乎,会失去成就感和价值,太在乎会迎合、媚俗。作家还是应该保持一种边缘的状态,即可以观察生活,又不能沉溺其中。 娱人刘墉娱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