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240)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杨不过 杨葵 罗世鸿 包包)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杨不过 图 谢峰
无聊时做职业生涯测试,我的结果永远是跟娱乐有关的职业,虽然现实中完全不搭界。从小到大我为自己设想过的职业无数,最离谱的是像美国的赖斯那样的政府高官。当然最好是在年轻漂亮的年纪,可以每天穿着不同的职业装搭配各式高跟鞋,将一干人指挥得团团转。这个梦想的后遗症就是狂爱《白宫风云》这类不够女性化的电视剧。最崇高的是做研究古生物的女科学家,在青春逝去的时候还会被年轻英俊的后来者崇拜。最省力的则是做办公室文员,每天打打字,回家带孩子,也很愉快。
但是,从来没有过任何与娱乐有关的设想,我从小就竭力把自己塑造成所谓脱俗的人,尽管20年来收效甚微,但仍然寄希望于特立独行的姿态可以弥补天分的不足。我不会想到,在成年之后居然会有成为明星的梦想。
是在看香港金像奖颁奖礼时的忽发奇想。现在的艺人越来越让人不敢小看,最佳男配角黄秋生一上台便引用狄更斯《双城记》开头的话说:“这是最好的时候,也是最坏的时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我们一直走向天堂,我们一直走向地狱。”
我钟情于他,只因为在万恶的娱乐圈里他可以说:“你看给你颁奖的那些人,都是一堆无厘头的人。从他们手上拿奖,就像你去精神病院,精神病人说你最漂亮一样,因为你是他看过最漂亮的,而他旁边都是些恶心的猪脸。这有什么意义?”
还有一次曾经看到一个从马来西亚来的小影后在电视节目里大谈独自去尼泊尔爬山差点死掉的故事,体验之丰富不亚于一些言必称流浪啦痛苦啦的另类女青年,并且,比她们漂亮好几百倍。
看明星们在领奖时作秀或大哭,我忽然希望有生之年能有一场演唱会,可以坐在小舞台的中央,只有一束微蓝的灯光打下来,有机会对很多人说多谢,感谢父母兄弟姐妹以及爱过或爱自己的那些人,然后唱一首动人心魄的歌。因为,这样肉麻的话在平时说出来是会被打死的。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我几乎可以打赌,那个我暗恋多年不能忘情的人会马上爱上我。他对我的印象,还停留在唱苏慧伦的阶段,他在一个只能看到CCTV4的地方说:今天我看“中国文艺”,有苏慧伦在唱歌,于是便想起你,那时在KTV,你总是会点很多她的歌来唱,但总是很快被别人不耐烦地掐掉……
如果有一天,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我该怎么告诉他,我已经唱不来那么轻松诙谐的歌了,而苏慧伦也早已被人遗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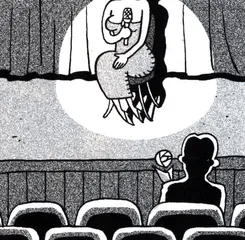
一日长于百年
杨葵
过生日,各送礼物,能看出关系的远近,更能看出用了多少心。那种逢男领带皮带,逢女香水化妆品的,一般说来,都是在敷衍塞责。
看到最别致的礼物,是一张《人民日报》,又黄又脆,但是干净熨帖,静躺在一个书卷气很浓的锦盒里。乍一见,不明所以,仔细看报头的日期,正是过生日那朋友出生那一天,通栏大标题正在“反帝反修”。时光突然倒流几十年,心里咯噔一下。想出这点子的人,生意不做大才怪。
我一向念旧,对这类含有过去成份的琐事儿兴趣浓厚。好比吧,一直坚持记一两行字的流水账日记,去哪儿了,干吗了,见了什么人,往来什么信件,等等,虽简约,还清晰。表面波澜不惊,可是自己能通过那些蛛丝马迹,回忆当年每一次心跳的振频。
每天辛勤做这功课,原是为了老来有得念叨。可是没等攒到老,就忍不住时时去翻看。一念之想,就拿出来对照对照,去年今天、前年今天、五年前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我都是怎么混过去的呢。
有一阵儿,耽迷于这种对照,好像看到自己的成长,自己的奋进,自己的成功;有时胸怀放大,还能放眼世界,看出风云突变、社会进步这种事儿。最过分的时候,爱屋及乌,还殃及他人——爸有一个系列的一寸免冠照片,小学、中学、大学、工作、右派……横跨70年,贴满一张相册页,我偶尔会拿出来对照,爸在我这个年纪正干嘛?
渐渐地,不爱看了。因为再看那些成长奋进成功,突然真的都成了过去。或者,简直就是“逝去”。这倒也没什么,关键是,对照现在,看到了个甚?颓丧消极倦怠,还有老去——真该回忆了吗?回忆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过早的回忆原来竟如此不堪!
再到如今,该写写,看得虽然少了,但也还看,就是再不含什么情绪了,不感慨,不兴叹,更别说什么放眼世界了。就是过日子,内心静好,雁过留痕。再看到有人送那样的报纸,还会兴趣浓厚凑过去瞧,但已是十万八千里外的事儿,再无心动。
不过,万籁俱寂,心如止水,那是牛逼呢,甭信!树欲静而风不止、“这几日心里颇不宁静”,这才是现实种种。每遇烦恼的日子,会在大脑里抻出把尺子,全长五千年,每年占一刻度。这尺子一摆,登时心里就服了,就您那一天?连带去年今天、前年今天、五年前的今天、十年前的今天,一起上吧,算个屁呀!树想不静都不成,因为风停了。
说归这么说,其实明眼人还是看得出,恰是因为正在经历欲静不止、天人交战的煎熬,才会写出上边这些字。事到临头,终究还是一日长于百年。
和丁丁一起去冒险
罗世鸿
那次过拉龙拉山口时,漫天大雪,天地一片混沌。到了尼泊尔后从报纸上得知,在我经过山口时,离那里不远的希夏邦玛峰上,Alex Lowe遇上雪崩,一个传奇终结了。我是看着录像带学爬山的,Lowe兄弟在电视里一招一式地教我在雪山上如何上升如何下降如何保护……Lowe还是个登山装备的品牌,我穿它的衣服,背它的包。
加德满都是全世界的背包客在亚洲的主要集散地,闲人们到了亚热带全都穿着亚麻裤子、T恤衫。入境随俗,我脱了Lowe,买了一件绘着“丁丁”的T恤套上,然后拿着一块蜡染和一包好茶去找朋友。
朋友叫拉迪,我们是在珠峰北坡认识的,当年他23岁,却已是夏尔巴向导中的翘楚,三次登顶过珠峰。当年若不是他的帮助,我的第一次登山大概会以悲剧收场。我在加德满都蛛网般的街道中找到了拉迪工作的地方,接待的小姐却搞不清拉迪是谁,叫经理出来,他阴着脸沉默了一会儿,说:“拉迪死了。去年10月,和韩国人在安拉普尔娜峰,雪崩。”说完转身走了,扔下我呆立一旁,不知所措。胸前的丁丁一如既往,瞪着一双好奇的圆眼睛。
有一集《丁丁在西藏》:丁丁的中国朋友张仲仁乘坐的飞机坠毁在尼泊尔,所有人都认为他死了,只有丁丁相信他活着。在历尽艰难险阻后终于找到了张仲仁。原来是传说中的雪人救了张。
穿着那件丁丁T恤,我去围着吞噬了拉迪的世界第十高峰徒步了好几天。当然没有奇迹出现,也没看见雪人。拉迪是我第一个死于山难的朋友,当时暗自祈祷,但愿也是最后一个。但岂知“上帝不关心人类,上帝只掷骰子”。才过了大半年,青海玉珠峰传来噩耗,五名登山者因天气骤变葬身雪山。其中惟一的一个姑娘,是广州的小旷。
小旷是在走川藏线时认识的。她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便选择了川藏线,穿着一件丁丁式的风衣,故意让人难辨性别。印象深刻的是她带了满满一包摄影器材,掏出个镜头来,似乎有小腿粗,如小臂长。万万没想到23岁的她第一次去爬山,就永远留在了5700米。
一年之后,又有凶信自新疆来,朋友老董不见了。老董曾登顶博格达,老董是新疆玩冬泳人中的顶尖高手,老董还能歌善舞……但在“知天命”的岁数,老董被托木尔峰脚下的一条冰河卷走了。我始终记得他一边载歌载舞,一边变魔术般捧出大盘新疆美食的样子。
想起说这些事是因为前几天我买了一整套《丁丁历险记》的DVD。看着碟子,温习儿时梦想的光荣和挑战,突然想起这些逝去的朋友。我发现丁丁的故事里永远不会死人,好人、坏人都不会死,没人死去,当然也就不会变老,等我未来的孩子那辈人长大了,他们八成还会看永葆青春的丁丁。而我现在不管听到哪里死人,都觉得心惊肉跳。
中产江翎
包包 图 谢峰
江翎刚刚而立,已经是杭州一家大型私营企业的行政总监,她老公是香港一家上市公司的财务经理。以他俩的收入,一年下来就足够在杭州市区买一套房子。另外,江翎上下班出租车的报销额度是一个月1000块。如果驾照到手,公司就配一辆车子给她。
但是,江翎仍偏爱她刚毕业时买的那辆“坐骑”——安琪儿自行车,哪怕隔一两个月就得光顾一次她家楼下的修车店。江翎从来没有跟修车店的老板说过自己的职业,那个善良的老板看着她的眼神总是带着点怜悯,配个小零件什么的经常不收钱。江翎顺水推舟地笑纳。去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她从钱包里随随便便地掏了张超市购物券送给那个老板,那个老板看到面值“500元”,老半天都没回过神来。
江翎住的房子是租的,60平方米,没有装修。她在深圳有过一套房子,自己从来没住过,房东做了好几年,租金一分没收。房客是她的好朋友,借用久了,后来就干脆买下。她在杭州买了一套商品房,正摩拳擦掌准备好好装修一番,她的小叔子跑到杭州开公司,没钱租写字楼,就用了她的房子。后来小叔子的资金周转不灵,需要帮助。偏巧她的股票统统套牢,于是她二话没说,让他拿房契办了抵押在银行贷了一笔款。现在,房子在银行的手里,江翎无可奈何在替生意失败的小叔子还贷,期待着心爱的房子早日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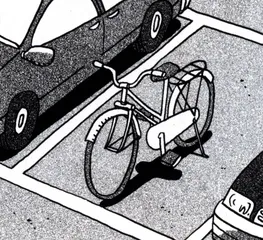
和江翎住在一起的是她的婆婆和她的儿子。婆婆是个文盲,从乡下过来,在杭州惟一的生活目的就是照顾他们娘俩的起居。她婆婆做的饭菜我领教过一次,吃进嘴就发誓再也不会有第二次。江翎如果不加班,没有饭局,不用带儿子上兴趣课,她一定会骑着她那辆破安琪儿到农贸市场去采购未来一星期的物品。
前不久,她又到农贸市场大宗采购,在自行车前自行车后放了满满当当的蔬菜、肉类、海鲜和水果。在快到家的十字路口一个急刹车,自行车的后座轰然倒塌,苹果和桔子滚了一地。江翎狼狈地蹲在地上捡水果,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她大学时代的男友刚好坐出租车经过,中途下了车,帮她捡了几个水果。临别时,那个在网络公司做项目经理的男人带着与修车店老板同样的怜悯,说,需要我帮忙的话,说一声。目送那个男人拎着重重的电脑包匆匆钻进出租车绝尘而去,江翎心安理得地骑着那辆后座散架、挂满农副产品的破安琪儿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