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是世界和平的途径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郝利琼)
2月6日,中国籍法官史久镛在连任国际法院法官后上班的第一天,被选为国际法院院长。记者在采访我国最著名的国际法学家、新中国首任联合国国际法院法官、96岁高龄的倪征(日奥)时,他评价说:“史久镛能当上院长非常不容易,这不仅是对法官本人地位和能力的承认,也和我们国家强大、国家地位提高有关。”2月10日,记者通过越洋电话对在荷兰海牙的史久镛院长进行了专访。
三联生活周刊:去年11月当选连任国际法院法官,今年又当选为院长,您觉得它对您本人有什么样的意义?您的当选和中国国际影响力提高这样的事实之间有什么样的联系?
史久镛:我能连任国际法院法官并当选为院长,能继续为国际社会的和平和国际正义做出贡献,是我生命中最愉快的事情。在去年11月的法官选举中,我在安理会得了满票,在联合国大会选举中获得了167票的高票数。大会的有效选票一共是187张,但在联合国会员国中有20多个国家并没有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能争取到他们的投票是非常费力的。当然,我的选举成功,更是和中国国际影响力分不开,也是我国的国际威望提高的表现。国际法院的法官能在超越一切政治利益的情况下选我当院长,我感到尤其光荣。因为我是1946年国际法院成立以来第一个中国籍院长,它是对我本人能力的承认。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院长和作为一个法官,在职权和责任上有什么样的变化?
史久镛:当上院长,我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更多的责任感。比如,国际法院审判案件都要由院长来领导,下周我们就要正式开庭审理伊朗指控美国的一个案子。案子很重大,由全体法官一道审理,主持开庭的当然是我,开庭以后的事情,比如内部讨论、起草文件、写判决书等等的事务,都要由院长领导。另外,院长还要负责院内的行政管理、监督行政事务、处理法院与各国关系,接待国家领导人等等。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法院和国内的法院有什么不同,它的功能和任务是什么?
史久镛: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构,是联合国六大主要机关之一。它的地位和安理会是对等的,国际法院院长和联合国秘书长的地位也是对等的,所以国际法院并不是一些媒体报道的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
它和国内的法院有很大的差别。首先,它没有强制执法权。国内法院具有强制执法权,国际法院的判决对当事国是有约束力的,却没有强制力。但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对拒不执行判决的一方,国际法院将提交安理会进行强制执行。其次,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的双方都必须征得对方同意,并愿意接受国际法院管辖,只有在双方都自愿的基础上才可能立案。
再次,由于争端双方都是主权国家,法院对他们必须同等对待,比如写书面报告,给这方6个月,必须也要给那方6个月;法庭辩论时,给这方3个小时,也必须给那方3个小时。另外,在国际法院打官司是不收诉讼费的,当事国只需负担律师费即可。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法院在维护国际和平、伸张国际正义方面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史久镛:国际法院在解决国际争端上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国际法院的判决书是有法律约束力的,这么多年来,我们对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做了很多事情。此外,国际法院的判决书及它对法律条款的解说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国际上经常引用这样的解说作为经典解说。在解决国际争端方面,国际法院和安理会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我们侧重于从法律的角度去解决问题,而安理会侧重于从政治方面去解决。比如最近非洲的喀麦隆和尼日利亚关于领土纠纷的案子,双方为此不断发生武力冲突,引起安理会的关注。我们也审理了这个案件,去年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判决,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现在正在督促双方要不折不扣地执行这一判决。在去年12月国际法院在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关于海洋上的两个小岛的主权争议判决中,我们把岛屿判给了马来西亚,印尼虽然也不那么痛快,但还是承认我们的判决是公正和合理的,他们愿意在新的基础上继续进行合作。
三联生活周刊:由国际法院判决的案子的执行情况怎样,大多数决定都能得到执行吗?
史久镛:在国际法院50多年的历史上,大多数的判决都得到了执行,只有个别的没有执行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国际关系复杂而多变,涉及到各种利益的平衡,作为法官,在处理国际问题时的难度在哪里?
史久镛:从专业角度讲,管辖权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没有管辖权,法院就无法插手任何一个案件。但对管辖权的界定很困难,法院一般都要专门对管辖权进行审理。在国际法院诉讼的案件一般都要分成两个案件,先是审理管辖权,然后对案子的是非进行审理。涉及国际争端的案件一般都非常复杂,要涉及到诉讼双方材料的送达、管辖权的界定、审理、讨论、起草文件、下判决书,这都是非常繁琐的事情。法官需要对一个案子进行长时间讨论,有些案子拖了十来年才审判。如上面讲的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案,卡塔尔和巴林关于领土和海洋划界的纠纷也拖了10年之久。一般来说,国际法院审理的案件平均要两年左右的事件,最快的也要几个月。
三联生活周刊:一个国际法官是超越于国家的,他必须具最公正的立场,但一个人总是带着他的民族情感的,他怎么能做到客观和公正,特别是在有关他的国家利益的事件上?
史久镛:这就要求法官道德品质高尚,一切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看问题时要保持客观公正,不应有私心杂念、偏见或成见。在一桩墨西哥诉美国违反领事公约的案件中,来自美国的法官坚决站在墨西哥一边,体现出了他公正的立场。当然,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又不是活在真空里,法官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这时候,也不能绝对化。一些法官投了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票,他们或者是真的相信自己国家是正确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观。国际法院之所以设了15个法官,来自15个国家,代表了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和法律体系,就是为了确保其尽可能的公正性。因为不可能15个人都有偏见。这样,我们就在制度上尽量保证了公正性。
三联生活周刊:您年轻时候选择国际法作为您的专业是抱着什么样的理想?经过这么漫长的岁月,这个世界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如今您怎么看自己当初的选择?
史久镛:我出生在动乱的年代,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如果世界上全部国家都能遵守法律,国与国之间有行为准则并且能够切实遵守的话,世界和平就有保证了。而国际法就是解决世界和平的一个途径。我为我能实现自己年轻时候的愿望,为世界的和平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到非常自豪。
史久镛小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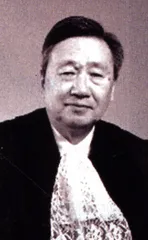
1926年10月出生于浙江宁波,童年迁住上海。1948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1951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硕士学位,之后在美国和中国从事国际法的研究和教学工作。1980年~1993年期间,作为中国外交部法律顾问,参加了同英国进行的关于香港回归问题的谈判,并担任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法律顾问。1993年11月,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官,任期9年。2000年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任期3年。2002年10月再次当选连任国际法院法官。2003年2月,当选国际法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