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信(21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吕明 辛快 朱启禧 任树 艾君 余不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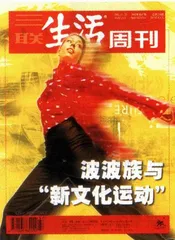
“看看波波们的生活让人觉得特别有压力。怎么人家都混成那样了自己还是这样?一拨一拨的名词全都没赶上就快三十了。网站上单挑出的那段话告诉我们说这东西“提供了一个用于对比的参照框架”。我没看出来。就觉得自己又被一场运动漏过了。”
北京 吕明
毕业流水线上花枝招展的副主席
有报道说:近日,应届高校毕业生开始填写“就业推荐表”。记者调查发现,一所高校居然冒出了近百名学生会副主席,数百名应届毕业生在填表时,“在校期间担任的主要职务情况”一栏中,竟都填写着诸如“学生会副主席”、“某某部副部长”、“班长”,“学习委员”等,个个身居要职,人人权倾校园。
你不能不感叹当今大学生眼界阔、智商高、能力强,在世事洞明的前提下精心包装自己,在激烈竞争的态势中竭力推销自我。似乎有必要成立一个“大学毕业生包装学会”,来好好地研究这个事,最终弄出一个“毕业生包装产业”来也说不准。有很现实的一些事例可资研究,比如不少大学生在毕业前去做了整容手术,小的割个双眼皮,中的隆一下鼻梁骨,大的就不好说了,反正是伤筋动骨的。这些是有形的“包装美学”,至于无形的,这“人人都是副主席”,该算是典型了吧?报道还说,该高校附近一家复印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很多毕业生为求职纷纷来此制作假奖状,从“某某地区作文大赛一等奖”到“某某发明科技奖”,还有的毕业生甚至连“某娱乐场所卡拉OK一等奖”的奖状也制作得很精美。
据说大学教育是培养一个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格健全的公民,不是生产或出售商品,我看这个老观念要改一改了,因为现实就是在培养一个个产品卖给社会。现在生产大学生的批量越来越大,谁能保证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的全是优等品一等品?最近有报道表明,已经出现了大学生听课雇“枪手”的事。在武汉一些高校,继花钱请“枪手”代考之后,眼下又流行一种新现象,大四学生花钱请低年级学生代听课,而且还有“中介”。如此这般,教育流水线上产品没有大的变化和质的提升,而卖给社会的“就业市场”又不容乐观,那么在外包装上下工夫,不就是无本万利、一蹴而就的事吗?就像过去的绣花枕头和现今的许多营养品,哪一个不是包装得花枝招展的?
浙江 辛快
狱内成材与民工培训
前两天《大众日报》登载了一则消息:山东省监狱成立了服刑人员刑满释放就业培训指导中心,并与社会中介机构、知名企业联合成立了全国首家狱内劳动力市场。市场开业当日,即有12名服刑人员当场被企业提前“预定”。报道还说,山东省监狱注重培养服刑人员的生存能力,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双手生活,并且先后有150名服刑人员拿到了初级、中级技术资格证书。看到这则新闻,我想起发生在老家的一件事: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我们那儿还比较贫穷,邻里之间经常为一些小事、小利益发生纠纷。有一次,我邻居的小儿子因他家与别人的小纠纷,便在夜里一把火将人家的麦秸垛烧了。年轻人头脑简单,一时冲动却不想触犯了刑法,被判入狱。当时在村民们看来,这小伙子一辈子完了,他家又穷,现在又坐牢;谁家的闺女会嫁给他?岂料,这小伙子在监狱内一边劳动改造,一边学习人工菌栽植技术。等他释放回家后,自己搞起了人造菌生产,把以往农民焚烧的秸秆用来培植蘑菇。如此以来,不但率先摘了穷帽子;还娶上了漂亮媳妇。简直是“因祸得福”。
而今,我通过升学离开了农村。可每每在城市街头看到无一技之长的民工兄弟为了一份零工而在烈日寒风中煎熬时总有一种难言的酸楚。按例他们生在城市,就会有劳动保障部门提供就业培训,可他们没有这一纸户口享受不到这个待遇。每年一到春运高峰也即“民工高峰”时,总有部门呼吁打工者不要盲目外出,要有一技之长。可实际上,许多地方政府部门并没有把农民纳入就业培训范围。农民即使想掌握一门技能,也惟有选择各种以赢利为目的的专业技校或培训班,而学一门简单技术,通常需要一家人全年的劳作收入。监狱成材与民工培训两个看似毫不搭界的问题,要联系在一起就值得社会关注了。
济南 朱启禧
违约就是违约,不值得鼓励提倡
有个案例:魏志宏是原中国人民银行职员,在央行7年,先在西南财大拿了硕士学位,1998年被派到英国大学学习银行专业,2000年刚到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读博士,2001年就跳槽到德勤国际。这样上完学或落下北京户口就与单位“拜拜”的事太多了,身边就有。人才流动实现最佳配置,是市场经济大趋势,谁也不能阻止。现在的问题是社会、媒体有种不太公平、片面的看法,只讲人才流动的半边理,即:凡是人才跳槽就应该受到鼓励,就是人力资源最佳配置。反对违约跳槽、对违约加重处罚的往往被视为保守、僵化。简单地说,这种看法是拿着“不是”(违约)当理儿说。
人才也要讲信用,违约不是荣耀。当然,国企制度肯定有问题,要加快改革留住人才。媒体对国企管理落后批评甚多,只是对违约者谴责声基本没有,所以我才想说出另一半理儿,为国企说句公道话。
北京 任树
谁抢救了刘海若?
因为英国的某个专家在刘海若受伤后把她“确定”为脑死亡,而后来中国的医学专家凌锋等人又“奇迹般地”使她“死而复生”,导致现在有不少人开始怀疑英国的医学水平,进而觉得中国的医学是多么的了不起。我当时有个疑问:海若是在英国伦敦北部的一个叫赫德福德郡的小镇出的事,伤情又那么严重,而中国专家是在事后几日才千里迢迢赶到英国的,远水难救近火,那么当时是谁抢救了她?
这个疑问现在有了答案。为海若治伤的另一个专家、北京宣武医院普外科主任孙家邦大夫说:“海若出事的小镇医院对病人大出血时采取的措施是很先进的。在肝破裂情况下找出血点止血很困难,往往会贻误病人生命。而在英国一个基层医院,能够在破裂的肝周围塞紧压住,用一个网兜住,先保住了生命。”孙大夫还说,这样的急救方法在大医院开放的医生中是被广泛接受的,而这方法在中国的教科书上没有。所以英国基层医院的腹部外科医生的知识水平比较高,三天后在伦敦打开腹部,肝脏已经长好,不用修补了。
记得前些天,为海若治疗的凌锋教授拒绝别人把她称为“神医”,现在孙大夫又把英国基层医院的医术大大褒扬了一番。中国医学专家对外国同行的中肯评价,不是谦虚之词,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令人起敬。由此我们也知道,即使英国某个专家说过海若“脑死亡”的话,也并不意味着英国整个医术就比中国差,也不值得我们为此沾沾自喜。
郑州 艾君
救助请勿讲等级
武汉市前不久出台一项规定,该市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也可领取《再就业优惠证》,享受各项再就业优惠政策。过去,该市只有国有企业下岗失业人员可领取,而集体企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却不能,因而在再就业时面临的困难更大。
这是进步,但进步过后又禁不住要问:那些曾在私营企业打工过的失业者呢?那些一直靠打零工度日甚至长期无业的人员呢?他们可不可以同样享受这些优惠政策?难道他们的日子比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过得好吗?
事实显然不是这样。虽然不少国企的下岗职工过得很艰难,但长期一直有“组织”(单位和政府)照应着,有下岗津沾、低保等各种补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了一位有“武汉市再就业明星”之称的熊姓下岗女工,她在一家宾馆就业3年后,还按期到厂里领取每月200多元的下岗生活费。而另一方面,那些所谓“体制外”的人员长期处于“孤军作战”,成为被社会遗忘的城市赤贫族,以致不少人靠“黄赌毒”等违法行为维生。他们与“体制内”人员的区别仅仅在于,由于长期“自力更生”,心理适应性更强,但决不等于不需要社会的扶持和关怀。面对不同的弱势人群,政府和社会应以公平为出发点,不能厚此薄彼亲疏有别,有意无意地忽略某一群体,而对某一群体过于“偏心”。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即使不能照顾周全,也应该按照合理的“差别原则”,从最困难的群体开始,让他们同样感受到社会大家庭的温暖。否则,这部分人很容易与社会产生对立情绪,成为真正的“不安定因素”。
武汉 余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