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公社”,姿势正确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之余)

Soho现代城的大堂是一种街道式的设计,很开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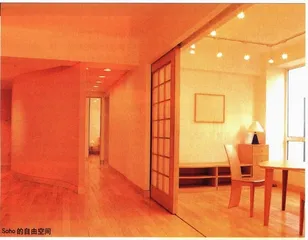
Soho的自由空间
“狄德罗的新睡袍”
从机场高速路进入北京,走上东三环或东四环,“soho现代城”的楼顶会一直在你的视线中,除了这个巨大的实体,Soho的住宅概念也因为红石公司的soho现代城和“建外Soho”而成为时尚界关注的焦点,一直在各种媒体和购房者视线中。
北京聚集了最保守的文化人和最前卫的另类,也许是前卫的另类们认同了Soho这个品牌,但是再保守的人也没法否认这是一个消费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一个商品总是在所谓的狄德罗效应中才成为必需而获得成功。狄德罗因为友人送给他一件新睡袍,为了与它相配,他一件件更换了他屋里的所有东西。即使是哲学家,狄德罗可以事后写文章后悔接受了那件新睡袍,却没法否认物品代表着的文化象征意义。其实所谓“狄德罗效应”的起点并不在于那件新睡袍的风格样式,而在于被它所象征的某种生活方式,后面的一切都是为了这种生活方式的完整构成。
Soho认定的“狄德罗新睡袍”是什么呢?潘石屹一直在说,多元是未来生活的趋势,谁也不能规定一种标准的生活样式。作为发展商,怎么能让房子在未来的时间里受到重用,就得能给人提供符合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因此,最好的设计模型就是把无限的灵活性和可能性留出来。这个判断来自1999年潘石屹和张欣到哈佛参加一个会议的气氛,张欣说,那次会议上来了很多IT界的人,他们当中有很多华尔街精英,这些人在以前都是住着豪宅,出门在外时也是非六星宾馆不住。这些人突然之间都撸起袖子做起了网站,那种气氛强烈地让他们感到,世界发生变化了——网络技术一定会深入地影响人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直接服务于生活的房子不能不考虑这种变化,最直接的变化就是有很多工种不再依赖于办公室,会导致一批人可以改在家里办公。但究竟什么人在家里办公,他的工作是什么类型,都不好设定,灵活使用的空间就变成了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启发和落实。但是灵活也总得有个限度,不然没法进行设计,限度也就是建房子的依据。潘石屹为此花钱找设计师来专门讨论“人在哪个点上有最基本共同之处”这种看似不着边际、玄而又玄的问题,而户型立面风格,在他看来已经是肤浅的问题。
风格实在太多了,哪怕是翻开一本最简易的建筑读本,从现代主义以来,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简约主义、乡土风格、高科技派、新理性主义、新陈代谢主义,已经让人看得眼花缭乱;更不用说我们又笼统地引来了欧陆式、中国古典式、地中海式、夏威夷式。你要不去读一个建筑学硕士,永远也弄不清楚。其中有一个变化是很明显的——现代主义的信条之一是,建筑师或设计师对消费者负有道义上的责任,必须从自己确认的高雅品位出发,对消费人群进行教化。而后现代的设计转变了方向,80年代以后,全世界的设计都在转向。在法国,人类学家执掌蓬皮杜中心的设计部门,日本制造商把大笔钱花在调研“生活方式”上。在美国,电脑巨头招募心理学家的劲头不亚于招募工程师。谁还去管物品的风格,最终的选择取决于生活方式,甚至只是不同的生活态度。
Soho的概念以及对新生活方式的憧憬和现在中国的创业文化态度相呼应,借助于电脑,到处都处于可能性的期待气氛里。利用生活方式进行市场销售,这种想法的直接来源是文化的一致性。它和亚文化群体的自我定位有关,亚文化群体有一种对既定规则的抵制态度,他们的方法是利用消费世界的某些部分进行创造性选择,形成一个可以表现其个性的产品群。所以在这样的消费需求下,一个物品向消费者体现出的意义会变得和单纯的功能元素一样重要。成功的品牌正因为这种意义而具有了图腾般的力量,消费者在物品中定义自己的个性。
当现代化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很多由城市发展带来的问题都成为需要反省的主题。比如,城市密度造就的城市魅力之一是逛街和在逛街中发现小的铺面,这些都渐渐被大的购物中心和塞满汽车的马路所减弱;城市道路的流畅被一个个社区的围墙所打断;闲散的交流被封闭的单元住宅所阻隔。建外soho向中外建筑师招标后,红石公司会提醒它的建筑师面对这些问题,最后中选的是日本建筑师山本理显。他的设计符合了混合使用空间,边界模糊化的soho概念。此外,也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那些社会性的问题,至少是回应了那些问题。在这个楼群中,山本理显设计了14条步行小街,宽的地方有6米,窄的有4米,加起来5000米长,而且相互错落,不规则地设有停步的小花园。这个社区没有围墙,14条小街向城市开放,其间有店铺、餐厅,有办公室。“城市密度”造成的魅力,于是会在这个区域得以恢复,这个社区也就融合在城市里成为一个部分。社区内居民也不会因此而被打扰,因为在街道建筑的三层屋顶设计为另一个区域的开始,三层的屋顶和每栋搂的大堂相连,形成了住户区域的街道,有一部分是架空的过街桥也是住户街道。为了避免楼与楼之间窗户对视的干扰,同时也可以增加每一户的采光时间,建筑师把整个楼体向南偏东倾斜30度,每层三户各居东、西、南三角,向北的角留给电梯和一个公共起居室,这个公共起居室被要求一年四季保持和住宅内一样的舒适环境。山本理显相信,“人类一旦置身于新的空间时,其行为会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可以想象这个公共起居室会引导出相应的人际交往。
革命浪漫主义的劲头
而在长城脚下开发的别墅群则来源于一个更有雄心的社会语境。
改革开放之初,未来是一个以遥远的欧美生活为样本的蓝图,20年过去,未来终于降临的时候,简单复制那些图纸上画好的东西已经成为对创造力的压抑。民族自信心在经济发展的背景下支撑起更深刻的欲望。一方面,不再做诸如“中国自己的IBM”之类的名目成为有觉悟的创业者的共识,“永远跟着人后边学,就永远矮人半截”。对于红石公司,创造一个有文化根据的品牌不仅关乎企业的成长,也关平信念。另一方面,对外企代理人、证券市场的经纪人这样一批得益于这个亢奋时代的人群,不再是像一幅有名的照片说的那样,“我买,故我在”,独特的风格和优雅的奢侈、城市与自然之间的调节、忙碌与精致生活协调成为进一步的身份定义。
红石公司开发的这个“建筑师走廊”现在更名为“长城脚下的公社”,这也是它原来的英文名字。如果说“走廊”的字面意思更温和一些,“公社”就显得更有挑战性。因为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建筑量非常大,但大多是在重复一些没有个性的东西”。投资2400万美元,给建筑师最大自由地设计这样一个项目,除了难以预期的销售前景,张欣说:“让中国与建筑有关的人,从发展商到建筑师以及购买房子的人,都看到建筑的更多可能性,激发人们追求浪漫生活的意识与想象。”“比如张永和的夯土墙,也不是说弄个榜样让人都做这样的建筑,但那也是一种关于建筑的精神和对生活的理解。”真有点革命浪漫主义的劲头。
“公社”入口处是负责景观设计的艾未未设计的一段赤裸裸的水泥墙,它其实应该是一扇门,是敞开的门,只是对来者起引路作用。同时巨大的体量立在路边,与长城相呼应,两种时代关于墙的不同材料,不同使用,不同看法,使这个地方从一开始就有了想象的凭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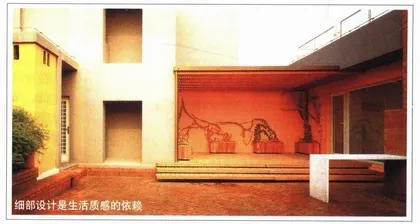
细部设计是生活质感的依赖
像设计师的时装一样,建筑师的房子,有出处的物品自然会提高身价。早在这个计划立项的时候,红石公司就广泛介绍了参与设计的建筑师以及他们各自的设计理念。这些建筑师在不同场合和地域都不断发表实验建筑作品,设计公共俱乐部的承孝相在韩国有一个独立式住宅被评为韩国20世纪十佳建筑。最奇怪的“箱宅”设计者张智强在香港因为他在一个30平方米的房间里设计的丰富空间而得奖,参加过2000年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日本建筑师坂茂的设计遍布世界,三宅一生的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都有他的设计。比如坂茂的哲学就是用人家认为不能盖房子的材料建房子,所以他的纸建筑成为世界建筑界众所周知的事件,并且在2000年德国汉诺威建筑展上获奖。张永和几乎是中国最知名的有实验精神的建筑师。
这些房子的独特性确实具备了诱惑力,长城也是一个价值极高的文化借用,这些建筑中,距离长城最近的只有200米,这是文物局的规定距离。后来一期的12栋别墅改为酒店式服务,现在不仅对外开放,而且他们也请人到其中的三栋房子试住,为开业后的服务提供更为细致的参考。
隈研吾设计的竹子屋是试住的其中之一,他说:“一般来说,修造基地的目的在于使用地和建筑物形成对比,而这一次,我想来个反其道而行之。长城周边风景的那种粗犷(低精度)非常有魅力,我想以它的精度为基准,将建筑粗犷化。在近代建筑中源于自然物与人工物之间的精度差的不协调感曾被看作是建筑家的一个个性特征。然而在现代,在这种精度上大做文章的建筑已被视为陈腐。现在能让人心旷神怡的是这样一种空间——其周边环境的精度延续不断地变化,直至建筑的精度,竹子这种素材使这一境界得以实现。”竹子屋在玻璃墙的外面用大面积的竹子墙围起,门、窗处有可以推拉的竹墙,屋子里,排列得疏密程度不同的竹墙把空间分割得空旷而层次丰富,是不同空间,又有通透感。竹子又是百叶窗,透进的阳光被竹子分割成幻梦般的光线。房子的温暖感得自于玻璃墙47厘米厚的中空填满了鹅绒,所以玻璃墙看起来也是鹅绒墙,和竹子相互弥补。这种设计中的想象力正是“公社”的期望。
泰国建筑师堪尼卡的白房子表面不起眼,但内部设计充满细节。她为到山里度假度周末的人建房子,不仅要给主人的生活提供变化,揭示一些在城市里丢失的东西,同时也不能完全要带人离开城市生活,不会因为在山里而丢了现代化享受。
这样兼顾两种心理和物质的需要,才能使人的生活更加平衡。现代化城市里讨厌的东西——噪音、污染、忙碌没有了,缺稀的东西全方位提供,山、树木、凉风、安静、星空,这就叫“奢侈”。奢侈还将体现在服务上,张欣正在考虑请一位来自瑞士的酒店服务学校的校长来培训这里的服务员,让每一个细节都超出想象。她说:“什么是满意?就是得超出想象。”
而超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策展人想象的是在中国有这样一个聚集了12个前卫设计的建筑项目。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是创办于1895年的威尼斯双年展在1975年加进的一个部分。今年的是第8届。策展人发给红石公司的邀请函说:本届双年展的主题是next,即未来。我们正在世界各地寻找能为未来十年的建筑业树立一个里程碑的重点项目。你们的项目从许多方面讲正是这样一个在建筑创意中结合了美学理念和浓厚的亚洲个性的完美建筑。在考察了走廊的项目后觉得,这个项目理所当然非常适合参加今年9月开幕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展览。以一组建筑组成的项目参加展览,“公社”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质疑的声音
建筑上强调想象力的一般是公共性建筑,而居住建筑是设计生活方式的,所以生活细节的设计是否合理,空间利用率的高低,才是衡量其价值的标准。高层建筑的空间利用率应该是75%,市面上的房子都不到70%,这些东西没有做到,就谈不上什么想象力。Soho现代城的所有理念都有补漏的嫌疑。
长城脚下的公社不是由业主委托建造的别墅,所以建筑师在没有居住者要求的设计中只有理念,但没有居住的舒适度,并且理念又不够新鲜,那它是什么?我们看到“公社”别墅的多样性并不是由地段产生的,而是建筑师风格的不同,这是对特定环境的一种浪费。
以张永和的夯土墙为例。什么样的材料决定了它承重量等指标,决定了它的建筑形态。比如南欧、阿拉伯的建筑,墙很厚,拱形很多,墙的厚度和门窗开洞的对比造成了它的审美对照,材料本身达到了美。而这个设计中,材料与相应的形态毫无关系。
怎么激发人的想象?那房子必须是自己的。现在变成酒店,一个过客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