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东说:我老是拿建筑比人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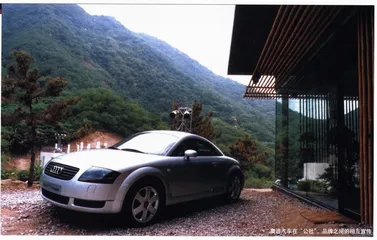
奥迪汽车在“公社”,品牌之间的相互宣传
我以前做的建筑80%是住宅,这是我最拿手的,张欣看过我装修的一所房子和一个办公室,他可能觉得我比一些设计单位的设计好一些,就请我来设计。我到这里来设计的第一个项目是soho现代城。Soho是比较难的一件事,又是办公又是住宅。她让我来设计,我是从一个房子开始设计,然后扩大到整个建筑。但是本来那4个楼已经有了设计,一开始是办公室,那个设计已经得到政府部门的批准,绝对不能改。所以我不是从零设计,因为原来的房子是设计为办公室的,现在要改为soho就要做很大的改变。但是已经经过批准的东西又不能随便改,受很多限制,这就要动很多想象,找办法。在这样的地方除了生活还要办公,应该有一个给这些不出门的人一个交流的空间,正好那个原来做办公室的空间,我们就把它改成空中四合院。中国一般好像是建筑师管外面,室内设计管里面,所以室内设计跟外面没有关系,外面可能是现代的,里面就可能是欧洲100年以前的样子。我们的房子是从里到外都是一个感觉。
好建筑坏建筑的区别不是因为材料,而是想法。坏建筑不是因为便宜的材料,是因为便宜的想法。所以越是受限制,才越需要聪明,每一个空间都要聪明。不好的空间人住在里面就不舒服,就不高兴,所以建筑不是让人看着高兴,是住着高兴。漂亮不漂亮不是最重要的,首先是人的精神与建筑的空间、环境有一个好的关系、好的交流。漂亮也不是不重要,建筑就像人一样,这个女人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因为她外表怎么怎么样,是因为她的精神。很多那种标准的漂亮,你不一定喜欢,因为你一跟她说话马上觉得她很无趣,没脑子,也就不觉得漂亮了。房子也是这样,如果一所房子外面特别漂亮,但是进去以后你觉得这个空间没意思,你也就不看了。如果有一所房子你从外面看,没觉得什么,进去以后你发现很舒服,空间很好,你出来以后再看就觉得它漂亮了。我老是拿建筑比人。
在“公社”设计的这个房子,知道是在山里边,所以要有一个坡度,它在什么位置都可以用,你会注意到它可以有两个门口,如果路在建筑的上边,上面可以是门口,走下来进入大厅。如果路比我的建筑低,那它的下边可以做门口。从上边进是直接看到一个花园,从下边进,可以上到屋顶花园。所以这个建筑放在哪里都可以,只要是山坡,可以朝南,可以朝东,窗户也合适任何方向。
每一个建筑是有5个立面的,楼顶也是一个立面,所以我老是要设计屋顶。因为现在你建一个楼,比你高的楼看着你的楼顶的确是一个面,你不能不设计,不能让上面乱七八糟。本来这是一片地,有草有花园,你在这里盖了房子,地没有了,我们要让本来的地还在,上面还要有一个像样的花园。当然你可以把它设计成圆的,三角的,但如果是平的,我的想法是把它用起来,尽量增加城市的好看。
设计公寓和别墅不一样,公寓得尽量让多数人能觉得合适。别墅要看业主的需要,要了解他的生活,他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喜欢什么艺术,建筑师会试着和他建立一种关系,如果没有这种可以沟通的关系,就不做了。一般别墅的业主找建筑师也是有针对性的。而“公社”的别墅是这样一种特殊的工程,它没有甲方,不知道谁将来在这里住,所以我设计的时候就设计给我自己,就完全自由,从颜色到空间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张欣给我们的限制只是很有限的一些,比如,用当地的材料,要有佣人的房间,很少。设计出来之后,有一些讨论,修改。没有那么多不要这样,不要那样。这是建筑师最自由的一个项目。

隈研吾“竹屋”的内部
方振宁:建筑评论家
方振宁答“长城脚下的公社”是否前卫?
有人认为“长城脚下的公社”的实验建筑非常前卫,然而也有人认为在建筑理念上不够前卫。
说实话,当初记者在网上看到“长城下的公社”最早提出“收藏建筑艺术”这一口号时就吓了一跳,佩服这一概念的提出,然而也对它是否会成为实验建筑的博物馆持怀疑态度。这种怀疑是基于中国那时还缺少我们所期待的文化建筑出现的环境。这些混合亚洲建筑军团到底能够做出什么样的建筑,我想,许多人会像我一样持观望态度。然而又像世界上所有的事物不可预料一样,“公社”的建设和最终结果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亚洲建筑非常另类的存在。
首先我们要讨论他究竟前卫在什么地方?当然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能只局限在建筑的造型方面,也不能以单项身份去和欧美数字化建筑以及虚拟建筑相比。首先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建筑项目,虽然中国有着世界第一的建造量,但有哪些文化建筑或者说纯粹建筑受到世界注目?自从包豪斯诞生以来,建筑就被称为是综合艺术的象征,而不只是解决居住的功能问题,纯粹建筑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美学意识和人对精神的渴望。“公社”的诞生就是对那些商气横行的建设现状的反叛,是新生建筑资助人,以亚洲独特的建筑样式抗衡欧美现代主义流行样式的尝试。
就像我们认识“文革”一样,虽然它为中国带来许多灾难,但是“文革”的一个重要概念无法否认——那就是企图在文化观念上进行革命。这场革命所焕发出来的能量似乎没有结束,我以为“公社”是中国建筑长征的开始,这就是所谓建筑理念上的前卫。
这次阪茂开发了完全是竹子结构的房子,并且把这种新的竹制合板技术在全世界申请了专利。同样,我们也从来没有见过香港建筑家张智强“手提箱”的住宅概念,他的设计对现在那种典型的住宅形象提出全面怀疑,建成的效果超出人们的想象。
韩国建筑家承孝相将已经感觉非常酷的钢筋混凝土盒子,整个用铁板做外装,其手法有些跟人家学的,然而那不是直接照搬,而是把瑞士建筑家赫佐格和德穆龙(Herzog&deMeuron)发明的建造语汇中最强的部分加以光大,让人着实佩服承孝相的锐眼和大胆。在20世纪的1927年,德国工作联盟曾经在德国策划了“现代实验住宅展”,共有16位建筑家受到邀请参赛,每人设计了一栋住宅,但风格基本上一致,以后对在世界上推广现代主义住宅有很大影响。然而“公社”让我们看到相当复杂的亚洲当代建筑文化背景,来自七个国家和地区的建筑家,虽然都受过本国建筑教育,其中相当一部分有在欧美受优秀教育的经历,然而这种文化出身的多元性背景,恰恰给“公社”建筑带来意外的丰富性。这也是这些建筑价值的原因所在。
在20世纪巨匠建筑家勒•柯布西埃生涯中有一个经典故事,就是早在20世纪20年代,柯布受到一位木材工厂的老板邀请,在法国西部盛产葡萄酒的PESSA C设计集合住宅,这位年轻的老板是位文化人,他看了年轻的勒•柯布西埃写的“新精神”的文章很感动,于是让柯布到
PESSA C试手,结果柯布的前卫住宅盖好之后许多年卖不出去,这家公司倒闭了。可是现在去看那些住宅仍然闪闪发光,是20世纪建筑的经典,这个故事让人非常感慨。勒•柯布西埃这些集合住宅为什么今天仍然被人们所敬佩?那是我们敬佩在那个时代柯布所具有的前卫精神,即使在建造上不那么精致,我们更注重建造的行为是否与那个时代保持精致的关系。所以精神也不是一句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