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报道:跨进中国门槛的纽约人寿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张峰 田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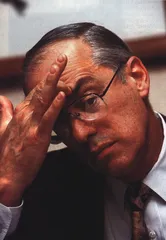
白嘉礼(陶子 摄)
代表美国保险业的建议书
白嘉礼说:“中国的确是一个潜力巨大的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美国和欧洲的保险公司就可以立即在中国赚钱。因为中国的事情非常复杂,在中国市场站稳脚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并且要有长远打算。”
三联生活周刊:请问您这是第几次到中国?您能透露一下您的建议书的具体内容吗?
白嘉礼:在过去的17年里我一直不断地到中国,不管哪一次我发现中国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首先是中国人现在越来越关注如何提高经济的发展水平,其次是对任何来源的思想都开放吸纳,以推动这个有巨大人口国家实现经济的不断增长。
我的建议书认为服务业的壮大会促进更高效的经济发展,会创造大量派生活动,带给制造商和消费者新的利益,所以中国应该培育一个高效运营的健全而又可以吸引外资的金融行业,放开管理,透明公开。中国在入世谈判时已经承诺将在几年内撤消很多外部及内部的限制,过渡期当然有助于满足中国国内调整的需要,而放开服务业所带来的长期经济增长效益将弥补中国经济的短期失衡。
中国在加入WTO后,各领域内将面临来自外国生产商、服务提供商带来的更多、更凶猛的竞争。来自外国的竞争使中国公司将来会被扫地出门是一种带有侮辱性的提法,因为竞争将迫使中国人学会竞争,而且你们一定会学会,这在很多领域都已得到了证明。
三联生活周刊: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有什么意见?
白嘉礼:我并不对每一个中国条款都很精通。但最重要的是条例要透明、完整。这个条例已经积极迈出了走向透明、完整的一步,但并不是最后结局。中国保监会已经成为一个现代保监机构,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出一些修改和调整。我想变化没有关系,但总的原则是一定要引进竞争,而且要在外国保险公司和中国保险公司之间创造一种平等的机会。
三联生活周刊:您希望中国保险作出哪些改变?
白嘉礼:首先,监管条例透明、清晰、完整,我们就不用去猜测它的意思了。其次,保持保险公司在财务上的清偿能力,且给予足够的自由来设计险种和定价。再次,对所有的消费者合理对待。最后,希望市场的行为准则一定是公平的。
与海尔合作的中国方略
白嘉礼评估中国大陆的市场说:“中国保费收入仅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1%,较美国约4%~5%比较,发展空间极大。预估中国寿险市场在未来10年,至少有六倍的增长空间,并可容纳超过100家寿险公司。中国总有一天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市场,尽管这需要20或30年。”据说,白嘉礼曾经在一个记者会上问过在场的近百名中国记者,其中只有4个人买了保险。他随即笑着说:“这里就会有我们96位新客户。”
三联生活周刊:合资公司申请开业的地点选择在什么地方?开业后打算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哪些产品?
白嘉礼:开业地点在上海。但是我们和海尔公司订了一个协议,希望尽快在全国都能够开展业务。我们的产品设计还没最后完成,而且没有得到中国保监会的正式批准。我们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是一系列的险种,首先会推出储蓄型的,再会是投连型的。因为只有当用户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储蓄型保障性的险种之后,投资连险对他们才有真正意义。中国投资连险名声不好是因为消费者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些产品的性质,他们在买这样的产品有什么潜在风险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稀里糊涂买了。对那些需要投资连险的客户,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真正理解保单的价值会有很大程度的上升和下降。
三联生活周刊:您现在怎么评价中国这个市场?
白嘉礼:我坚信中国市场的巨大扩展空间,上海的保险公司在过去几年里就发展得非常迅速,在上海保险市场上运营的那些中国保险公司绝对没有因为外国公司的竞争而被赶了出去。根据中国保监会统计资料,2001年整个上海的保费收入达到21亿美元,比2000年整整提高了42%。在上海的保险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一共有22家中国本地公司、14家外国公司。所以我坚信,随着中国的保险市场向外国的不断开放,这种成功的范例会在中国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地实施下去。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选择海尔作为合作伙伴?
白嘉礼:好的合作伙伴,应该一方是保险业行家,另一方是市场方面行家。如果两家都是做保险的,各有不同的经营方式,一定会发生冲突。而我们现在这种方式,需要提供如何开发保险产品、建立保险产品的支持系统及如何推销保险产品的专业化建议。
三联生活周刊:纽约人寿选择海尔,是长久的合作伙伴还是跳板?
白嘉礼:合资企业是一种永久性关系,而且建立这种强劲的合资合伙会给双方不断提供巨大的价值。婚姻是我在描述合作伙伴时常举的例子,选择婚姻时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而且概念是将和你过一辈子。我坚信和海尔也是。
三联生活周刊:这种合作会不会因为现在政府在起一定作用?在由市场来决定而不是政府决定一切的时候,你们会不会有所改变?做生意肯定是为了赚钱,这个时候和海尔合作会不会没有纽约人寿自己来做更好呢?
白嘉礼:首先,不管在世界上哪个国家,政府对保险业起的作用都不会小。其次,我们相信海尔的目标和我们的目标完全一致。所以从长远看我们都会和他们合作。产生利润是我们这个合资企业多重目标中的一个,但不是惟一目标。我根本就不相信再过5年或者再过10年,海尔的目标就会和我们变得不同。海尔也知道合资公司不会马上获得利润,那是长远的利润获得。
三联生活周刊:和其他外资保险公司相比,在进入方式和理念方面,纽约人寿和其他保险公司的区别是什么?
白嘉礼:我想区别就在于我们给客户提供多种专为其设计的保险服务以及公平合理的价格。如果你是指有没有什么诀窍,没有,保险业是一个没有诀窍可言的行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你应该做什么,而是脚踏实地去做。
三联生活周刊:花旗银行等也在全球经营,他们的业务涵盖了商业银行、保险,这对纽约人寿有何启发?
白嘉礼:这种一站式购齐的模式在2001年是谈得很多的。但我们公司的销售额去年比前一年上升了41%。在美国这个市场上开展寿险竞争的有2000多家保险公司,所以再多一家两家我们也毫不担心。4年前就有人说:你们公司到2001年肯定垮台,因为那时所有的人在网上就能买寿险,没你们什么事儿了。但现在那个人的公司已烟消云散了,他很穷很穷。
白嘉礼
纽约人寿国际公司董事长兼CEO。纽约人寿国际公司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的国际分公司,在亚洲和拉丁美洲均有业务。白嘉礼同是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执行副总裁。
纽约人寿国际公司在阿根廷、中国香港、印度、印尼、墨西哥、菲律宾、韩国、中国台湾及泰国设有分公司或子公司。在中国北京、上海、广州及成都,以及越南河内设有办事处。
白嘉礼现任经理风险公司(Executive Risk Inc.)及邦斯集团(Barnes Group)董事,同时担任太平洋盆地理事会(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U.S.)美国代表团主席。
白嘉礼是美国投资顾问学院的创办成员、总裁和理事,亦曾是美国寿险联合会及联邦破产立法支委会的成员。他还担任过前纽约州长凯瑞的纽约执行顾问委员会委员,即“海曼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保险业的监管改革。
另外,白嘉礼亦曾是Capitol Housing Corporation和Capitol Housing Finance Corporation这两家公司的董事及副董事长,美国保险协会的副董事长,及赫佛大地区商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上海一直是各家保险公司争夺的重点城市之一(吉国强 摄/Fotoe)
偏执的行业老大
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成立于1845年,总部设在纽约,是美国最大的相互型人寿保险公司,是排行《财富》杂志全球500强第187位的专精人寿保险的美国百年老字号。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提供传统寿险、年金险、健康保险、伤害保险、共同基金、机构资产资产管理、信托服务等401(k)款金融产品。
据国际寿险营销研究协会(LIMRA International)统计美国84家主要的保险公司的市场数据显示,2001纽约人寿在美国寿险市场年销售增长了41%,新增保费收入的市场份额为第一名。尽管2001年全行业年金销售滑坡,但纽约人寿的年金业务却增长了2.5亿美元。2001年的海外市场销售增长了31%,投资管理销售在业内不稳定的情况下增长了20%。
纽约人寿2001年包括保费和服务费在内的营业收入增长了11%,达130亿美元,而前一年度为117亿美元。用于金融投资和保护保单持有人利益的盈余和投资准备金增加到87.41亿美元,为业界最具资金实力的公司之一。负责投资管理的公司——纽约人寿投资管理公司(NYLIM)所管理的资产2001年达1529亿美元,比2000年增长32%。
纽约人寿与众多保险公司最大的不同是至今不是上市公司,而且是偏执坚持决不上市的行业老大(全美五大保险公司之一)。史端博说:“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大致分成股份制或相互型保险公司。股份制公司的基本成员就是购买了股票并拥有享受分红和表决权的股东。相互型保险公司则直接对保单持有人负责,保单持有者具有表决权和分享红利。由于相互型的着眼点是保单持有人,因而他们的利益最能得到保障。
“从历史上看,相互型保险公司曾在美国寿险市场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在近十年中,金融服务业和保险业之间的界限已越来越模糊。结果,一些相互型寿险公司为了筹集扩大业务和提供多元化的产品及服务,相继转成股份制寿险公司。而这种变化偏离了相互保险公司的初衷:优先保障保单持有人的利益。
“纽约人寿则不是,在过去的150余年里,相互结构一直是我们的基石。我们拥有足够的财力并通过收购等来扩大业务。而且相互型模式完全适合我们的核心产品和对客户所承担的义务。我们的反向操作策略最初招致一些人的不满,但是现在已证明是最明智的举措。我们的寿险销售增长速度继续大幅度超过业界的平均值。衡量我们业务的标准不应该是某一天内股票市场的行情,而应该是在十年甚至是半个世纪内所取得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