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雪冰事件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金焱 甄芳洁)

(腾科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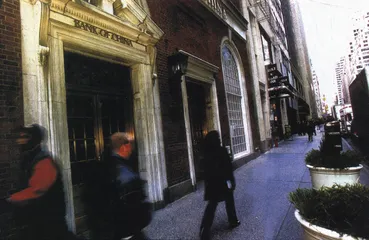
麦迪逊大街上的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优雅的沦落
42岁,王雪冰当上了中国的银行行长。对年龄的强调,并非完全来自记者,而是来自被采访对象。多数人都向记者叙述过王雪冰那句著名的话:“我42岁时就当了行长,你们呢?”在现在这样一个时刻,对这句话的解读,不同的对象则有不同的结论。不过,如果追寻这句话的“出处”,大家比较一致的判断是,更多时候,王雪冰是在与他的外国同行相处时说这句话的。很显然,国内的同行也会辗转得知并最终传播它。
从履历表看,王雪冰是1976年大学毕业,随后进入中国银行。按年代推算,他应当是工农兵大学生,但这并不影响业内人士对他能力的评价。一些外国同行甚至认为王雪冰是他们认识的最出色的中国银行官员:“在中国和国外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用流利的英语发表颇有见地的讲话,他非常专业,非常聪明,一直强调效率和盈利性。”王雪冰曾著书《欧元实务》,被采访对象也向记者屡屡提及这本书,“看一下你就会发现,他对欧元是非常有研究的”。
给业内人士的印象,王雪冰并非仅止于演讲与著书。在“实务”方面,他同样有很多不凡的记录。有采访对象指着北京阜城门中国银行原来的那栋大楼告诉记者,当时中国银行盖这栋楼很不容易,国家不给拨钱。中国银行自己也很难拿出这笔钱,结果大楼还是盖了起来——王雪冰成功地做了一笔黄金交易,一笔交易换来了一座大厦。确认这种说法是困难的,能证实的是,王雪冰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trader(交易员)。也算是他的同行评价说:他是一个被西方银行界认可的专业人士,“他做黄金交易,是一个世界范围内都排得上名的交易员”。
王雪冰的“传奇”,还有一个说法是,他亲自参与操作的“业务”,一年能赚到的钱,相当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全年的利润。“他炒澳元,能在货币市场上把澳元砸了下去,从而在出口大宗货物方面赚了很多钱”。
比较而言,境外媒体更注意中国金融业的这位人物。《远东经济评论》认为,“王雪冰曾经享有盛誉,1993年起,王雪冰在中国银行做了7年行长,在这期间完成了把中国银行从一个政策性银行变成一个商业银行的初期艰巨工作,同时在这7年期间,把中国银行变成最赚钱的国有银行。”
所以,相当多数境外媒体概括王雪冰,比较一致的判断是:技术官僚。
当然,王雪冰被注意到的,还有诸如“从不穿聚酯衣服、白色短袜,喜欢法国餐馆、karaoke,还有波尔多葡萄酒”,《时代周刊》亚洲版写道。反映他格调的还有他爱抽烟斗,打高尔夫。他被形容成“优雅的银行家”。更复杂的王雪冰,不是没有被发现,一位欧洲银行家描述说:“(王雪冰)是非常有能力的银行家,但同时有着坏脾气,极其傲慢”。
王雪冰的原部下们说起他的日常喜好,前面都用“嗜”字修饰:王雪冰嗜酒。故事与他的司机有关。司机到他家里送一个急件,结果看到的王雪冰正坐在云集的文艺界大牌人士之间,喝得满脸通红,他从不掩饰自己对风雅的追求。
王雪冰的沉没,似乎应该从2000年2月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一点点算起。他遭到了从业以来领导权威第一次被严重质疑的境地,光荣开始被打碎。
中国银行的一些员工回忆说,王雪冰到建行任职后,他们与建行同行交流经常会听到很多隐晦的用语:用语之一是“退货”——“我们要退货,把货退给中国银行”,之后他们才明白,“货”是指王雪冰。另外是在一个特定时间出现在建行下面支行、分行的员工电脑上,4个字:您高升了。有讽刺王雪冰能力不济的意味。这种情绪的积聚,据说最直接是因工资问题。中国银行的一位中层告诉记者,他也曾听说王雪冰到了建行后,建行人的工资就减了,但至于减工资的依据是什么,他并不清楚。
从“最优秀”的中国银行官员,到遭遇被“退货”的境地,领导能力的下降是很难解释的,勉强可以联系起来的事件是,美国货币监理署(OCC)从1999年开始调查中国银行纽约分行的事件。
“优雅的沦落”,西方报刊用类似词语描述王雪冰的结局。他们的报道解释说,在过去监管不严、体制不清的中国银行业里,许多银行家做了违规的事情甚至意识不到自己在犯法。也许这就是王雪冰悲剧的原因之一,但显然不是全部。
在王雪冰被解职时,作为王雪冰事件的一个重要成员,香港《下周刊》评价为一个“穿着优雅,纤细、柔声细语的女人”王雪冰的妻子宗路路还在纽约,不知道她近期会不会回来。
王雪冰震荡
王雪冰事件确实是一个足以引起震荡的消息,尤其是在网上,还有国外。在新浪网的相关论坛上,许多人纷纷口诛笔伐:王雪冰是“中国最大的不良资产”,“极度的官僚”。
美联社声称:王雪冰事件,揭开了中国银行业冰山的一角。对中国银行业来说,这是一块正逐渐愈合的伤疤,但又被人揭开了。作为国际化程度最高的中国商业银行,美国严格的银行监管制度直接造成了这件事情的爆发。
王雪冰被拘,是在美国货币监管署结束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两年的调查,宣布结果的前几天。知情者说,从1999年起,这个案子一直在查,但纽约分行的一切工作都正常运行,外观看不出任何异样。这是一场针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1991~1999年违规行为的调查,而王雪冰在1988年时被派到纽约,从1990年起担任分行的总经理,曾为期3年。
1月11日,不是王雪冰第一次被查。业内人士透露,以前就曾经被查了半年,相比较而言,无论从规模还是引发的震荡,这两次都不能相提并论。
1月16日,中国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在中国审计工作会议上称,此前审计中国银行,查出的主要问题是违规放贷、账外经营以及违规开立信用证和签发银行承兑汇票等。这一次审计查出的问题“主要是27亿元违规操作”。知情者说,这里面大部分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出的事,而且王雪冰难逃干系。
美国货币监理署(OCC)的最后处罚办法是:对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实行1000万美元的罚款、中国银行总行1000万美元的罚款。OCC声称,这些行为包括:“一个欺骗性的信用证问题,一桩欺骗性贷款,未经授权的授信及刻意隐瞒和其他可疑行为”。
复杂的交易及其问题
备受关注的问题贷款,其细节始终是缺失部分,OCC没有给出,只是在他们给中国银行美国分行方面的通知单里,列出了34个人和公司,同时禁止中国银行在纽约、中国城和洛杉矶的分行同他们交易。发言人罗伯特举的一个例子,是用来表明这次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事情的严重违规性:中国银行给一家暴发户性质的金属交易公司100万美元的贷款。在数月内贷款提高到700万美元,最终增至1800万美元,结果不得不作为一笔坏账勾销。
即使相关的法庭材料,除了证明事情的复杂性之外,仍然只能勾描出其间的局部与大概。
《远东经济评论》研究了有关的法庭材料后描述说:“(牵联的人与公司)是一个单独的、非常复杂的网络。”
2001年2月1日曼哈顿联邦法庭的材料表明,这个网络的中心是一对夫妻,他们是:周约翰和刘莎丽。在起诉立案时,他们住在新泽西Alpine的一个价值300万美元的家里,OCC的通知单里列出了周约翰的6个化名和他妻子的3个化名。名单上还有他的岳父刘道忠(也叫刘托尼)、岳母王淑敏、妻弟刘辉。
周氏夫妇和他们的亲威,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组成了一个“theNBM团体”。起诉书中指认:“他们设计引诱中国银行贷款给NBM团体数千万美元,盗用贷款基金3400万美元,不偿还债务,给银行造成严重损失。”
更曲折的事实在于,周氏夫妇从中国银行拿到贷款,然后转移过无数其他银行,存放在两个香港银行、广东省行和PoSang的账户上,其后又欺骗性地使用这些账户的基金作为商业税收,从中获得更多中国银行的贷款。
一个姓杨(PatrickYoung)的中国银行前职员也被起诉书指与周氏夫妇合谋。他发出了一个借贷担保,使周氏夫妇能够从另外一家银行借来200万美元。曾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工作的人介绍说,杨1992~1999年在该行的信用和商业发展部工作,1999年在风险管理部,2000年被开除。
法庭材料表明,起诉时间最早的借贷,发生在1992年2月,他们在没有还债的情况下,银行还是按常规给他们增加贷款。1992年2月给NBM团体的贷款是600万美元;两年以后,银行把这笔贷款增加到1000万美元;又过了6个月,贷款额外增加了500万美元,同时把借期延长到1999年7月。不过,法庭材料没有解释的就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去追究这两人的信誉欺骗问题。
这是一个显得相对详细,又极其专业与琐碎的情况说明,其间所涉及的人与事,并不那么容易就能看得清楚明确。一般中国银行业业内人士的解释更直接与概括:中国银行纽约分行涉嫌洗黑钱和违规贷款。
后来,问题指向越来越具体化:一是违规开立信用证。知情人解释说,美国当局起先查了一家公司,由这家公司追到中国银行那里。有趣的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总共开了27个公司,不过27个公司只有一间办公室,而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就是给这家公司开立信用证做担保的。另一件事是,该行提前释放抵押品;还有一个是违规拆借美元进行汇率炒作。
由于这次事件,中国银行处理了分行的11个人。
“中国特色”
中国银行的员工说,客观地看,中行的海外部是同国际银行业接轨最好的部分。
曾经去过纽约分行的张先生对纽约那栋坐落在麦迪逊大街上的小洋楼印象很深,“它在百老汇旁边,是非常古朴的建筑”。在比较繁华的麦迪逊大街上,纽约分行的业务量也很大。刚统计的数字表明,去年该行的清算交易量已经从前年的第13位,排到第11位,这是相当不错的成绩。
纽约分行1981年11月的开业仪式成为一个值得自豪的事情:在纽约、伦敦、中国香港、新加坡、卢森堡这些世界贸易金融中心,中国银行都设下分支机构。不过现在中国银行的自豪更理直气壮:中国银行成为中国第一家在亚、欧、澳、非、南美、北美六大洲均设有机构的银行。
有数据表明,中国银行拥有12967个国内机构和559个海外机构,建立起了全球布局的金融服务网络。在香港和澳门,中国银行还是当地的发钞行。海外机构的总资产达600多个亿。纽约分行的业务这些年来逐步扩展:1985年9月26日和1988年10月6日分别在纽约唐人街和洛杉矶开设了支行。服务范围涉及到个人储蓄/借贷、商业贷款、信用证服务,以及外汇和资金转账等。
即使国外媒体,也非常重视中行海外分行的优良业务。但曾经深入观察并研究中行的有关人士说:“当然,中行海外分行也有不可忽视的东西,比如说,呆坏账比例。”从某种层面看,最直接与国际接轨的海外中国银行,要抹去“中国特色”,也需要时间。
1月18日,中国银行周五公布的新闻稿称,截至去年底全行境内外机构实现账面利润108.05亿元人民币。新闻稿指出,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及香港中银集团重组费用支出增加等原因,境外机构实现税前利润折合人民币85.57亿元,同比减少9.41亿元,降低9.85%。
有专业人士分析说:中行海外的85.57亿元税前利润主要来自华人、华侨和一些中资机构,这也是中国银行海外分支机构的服务定位。这是一个颇有“特色”的定位。张先生发现,他进到纽约分行时,看到的都是华人的熟悉面孔——即使不是中国银行总行派过去的,也是在当地招的华人。
张先生从那些熟悉的黑头发黄面孔所发现的问题是:没有当地化。
与OCC等一些国际规则的要求存在的差距,张先生解释说,从中国银行总行派出去的人,对当地法律法规不熟悉,头脑中毕竟都是国内的标准,操作差不多也接近国内这一套。但是,你的银行毕竟在国外,这其间的危险在于,延用国内的管理模式,受到的却完全是国际化的监督。
中国银行所做的改革是“先从国外改起,毕竟在外国的地盘上要遵守外国的游戏规则,改起来也要比国内相对容易,”张先生说。原来纽约分行这类海外分支机构的定位是为当地华人华侨及中资机构服务,业务不敢做大,这样就形成了封闭的体系,不能参与到当地的主流中去,这带来了中国管理与国际监督的冲突外,更直接问题是利润来源。
洛杉矶是金融诈骗案的高发区,去年,中国银行洛杉机分行发生了两起支票诈骗案。诈骗案带来的惊吓让中国银行从上到下都意识到了防范风险的整套措施方面的脆弱,而这恰恰是国有银行的通病。该行一位资深人士说:“我们的整改工作已经持续进行一年半时间了,成果也有一些,但要彻底解决近十年累积的管理问题,我觉得时间还很长,路也很长。”
国外媒体对中国银行的称誉,相比而言,是最多也最充分的。但是,“接轨”之路并不那么容易。专业人士称:如果剔除个人在银行业务的问题(这需要有关方面查实),更全面地看,海外分支机构所累积的问题只是中国银行业累积问题的缩影。

银行的服务对很多中国人来说依旧谈不上舒适(路透/Reuters)
国有银行的不良资本
谢平(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
国有银行运作的结果为什么不良资产比较高?有几个要点:
地区之间不良资产的趋同性。这是一个数理统计分析的结果。工农中建四家银行的上海分行都盈利,他们的某省分行不良资产都是30%。也就是说,工农中建的盈利行都在上海、北京、深圳、浙江、福建。不良资产高的地方,各行都高。这是统计上连续几年的统计结果。它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银行不良资产跟银行管理无关,地方政府、地方金融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比如,工商银行的某市分支行,它如果在这个市创造的不良资产越多,那么它实际上对这个市的经济贡献越大。这个问题在国外没有,中国独有。地方政府很希望你在本地创造很多不良资产,这就跟财政拨款一样。因为负债你不用担心,是总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商业银行自愿的不良资产。仔细分析案例,有很多贷款,银行在贷这笔款时就知道这笔款收不回来。2000年工农中建有一万多亿不良贷款转移给资产管理公司。转移中发现一些贷款合同要素根本不全,有些贷款就是凭一张纸条,有些贷款合同上只有一个署名,贷款用途、期限都不清楚。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贷款要素这么不清楚?理论上叫做很不完全的合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很不完全的合约会贷款呢?这就是地方行为。分行行长、支行行长,共有四级行长,贷款时就不想收回来,反正无所谓。你查不出我有任何腐败行为,我这贷款就是收不回来,又怎么样?
自愿的不良贷款,对地方行长肯定有好处,好处在哪儿呢?跟地方政府的某种交换,跟国有企业的某种交换。你给我安排一个子女;或者说我现在对地方作出这么大贡献,我有可能转到地方去当副市长。我们有统计显示,工农中建的行长在地方提级的概率远远大于他在本行提级的概率。如果某家国有商业银行有50万人,只有一个行长。当行长的概率是五十万分之一。但是你要想在地方当个科长、副处长,就太容易了。我们的统计显示,工农中建的地方分行行长,最后转地方当官的很多。某行有一个分行长,当了8年,不良资产比率达到80%,完全就是一个制造不良资产的行长,最后退休,地方安排他做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地方政府心里很明白,这些人对地方工作肯定是做出了很大贡献。
不良贷款和行政干预。这样的结果是各方都有利。我们有很多这样的报告:工农中建说,唉呀,这笔贷款是省长开办公会定的。如果不给,我们在地方怎么活?给,我们知道这贷款风险很大。这样总行也没办法。实际上,这种行政干预的不良贷款对大家都有好处,对地方有好处,贷款留在当地了;对企业有好处,款子不用还了,有多少我用多少;对工农中建的行长来讲,我有个理由,对上头好交待,贷款是省长办公会定的;对存款人来讲,一点也没有损失,他不怕存款取不出来,他知道存在工农中建,国家有责任要保证存款安全。所以,这种合同、交易,对各方都具有帕累托效应。最后受损失的是谁呢?国家。
不良贷款与计划经济无关。计划经济下是没有不良贷款的。我们发现,工农中建的不良贷款,实际上1993年以前产生的不到1/3,2/3是1993年以后的。很明显,1980年时,我们这个国家,全国贷款只有几百亿,现在全国贷款是10万亿,就算1980年不良资产100%,也只有现在的不到1%。这几年的贷款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的。
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要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良贷款跟我们常规的、教科书上的、货币银行学上所分析的不良贷款是不同的。中国的不良贷款有很多制度性因素,而且这种制度性因素,跟我们的政治体制,跟银行的产权制度,跟我们的银行机制,跟我们的国有企业制度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