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的哲学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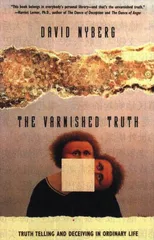
大卫·尼伯格《消失的真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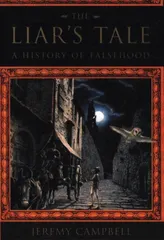
杰里米·坎贝尔《谎言的历史》
还有什么比讨论说谎更无聊的?——既然人人都是这方面的专家,整天都在撒谎,动机也五花八门:自大、贪婪、自我保护、政治野心、还有性……基于人类说谎的必要性,许多职业应运而生:从间谍到纳斯达克上市公司的账目审计员……
公众谎言比比皆是:最近,里根的传记作家爱德蒙·莫里森出于对文学更高的真实性的追求而谎称自己如何介入里根的个人生活;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里戈博塔·门图出于政治真实性原则编造自己在危地马拉的政治生活;美国历史教授约瑟夫.伊利斯出于自我理想杜撰在越战中的英雄事迹;小说家诺曼·梅勒为了促销小说而夸大情妇数量;纳斯达克一些公司为谋求上市泡制虚账;美国众议员加里·康帝步克林顿后尘,同样出于自我保护隐瞒与白宫失踪女实习生钱德拉·莱维的私情……
谎言如命中注定的车祸一样不可避免,不可不说。新近出版的两本西方畅销书更探讨了人类谎言的起源及发展,并为谎言的合法性张目。
杰里米·坎贝尔所著《谎言的历史》站在哲学高度,详细考察了人类观念进步史,其视野从前苏格拉底时代一直延伸到法国解构主义运动。坎贝尔一方面扼腕于当代哲学中“真实性”这一观念的衰颓,而另一方面则高度评价了谎言的智慧。
与此同时,伊芙林·苏利文的新作《谎言简史》摘引大量来电影、畅销小说、政治新闻中的说谎片段,并模仿17世纪英国作家罗伯特·伯顿在《犹豫的解剖学》中的口吻对谎言进行分类和“谎言的真话成本”分析,她与坎贝尔一样,推崇真话,但也尊重谎言的必要性。
这两本新书都力求超越1978年出版的那本《谎言: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道德选择》。本书中始终认为撒谎只是生活的选择之一,说谎并非必然,书的结尾说道:“诚信乃宝贵的东西,容易丧失,却难以恢复。”
事实上,有关人类说谎行为的争论由来已久。
一些哲学家坚信说谎是绝对的恶。康德认为谎言是“对自我的犯罪”,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虽然托尔斯泰自己说过不少谎话,但他在小说里则警告说:谎言是说谎者的地狱。
而另一些人则对谎言持姑息的暧昧态度,他们认为,说谎在一定条件下不可避免,所以,人类最好学会怎样撒谎——怎样在正确的时候正确地撒谎。而最近这两本书则宣称:说谎是社会生活丛林法则中的必要求生手段之一。
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早有深厚的说谎传统。
雅典娜把俄底修斯比作“谎言的无底洞”;《圣经》记述的历史是通过谎言推动的;尼采说,“谎言是存在的病态本性”;歌德断言真话“有悖人类的本性”,真话将人禁锢在“有限”里,谎言将人“解放到无限的可能中”;维吉尼亚·伍尔芙也认为,不顾他人感情一味追逐真实是“对人类尊严的损害”。
当我们以审美眼光看待说谎,它是一种艺术,是创造的产物。蒙田认为,真话只有“一张面孔”,而“真话的反面”则八面玲珑——虚构、诡辩、变形、掩藏……这里是艺术和文学的乐土——毕加索说:“艺术是帮助我们认识真理的谎言。”
可最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当我们需要认识真理的时候,如何正确判断一个人是否在说谎。
有一则寓言,说的是一个岛上生活着两个部落。其中一个总撒谎,另一个总说真话。一个旅行者在十字路口不知方向,路旁分别站着来自两个部落的向导,旅行者不能简单只问一句“前方是否是正确的路”,因为他并不知道谁说谎,谁说真话。
正确的方法是——旅行者问其中一个向导,“如果我问另一个向导前方是否是正确的路,他会怎么说?”如果前方的路是对的,而被问的向导恰好说真话,他就会回答“不”,同样,如果前方道路正确,而被问的向导撒谎,由于他知道另一个向导会说“是”,其回答也将是“不”——因此,如果两人都说“不”,则前方道路就一定正确。
通过智慧的追问,我们在想象中的未知世界里获得真理与知识——说谎这一“存在的病态本性”在追问下不得不说真话。可惟一剩下一个不可预期的问题:现实世界并不存在品格如此清晰稳定的部落、民族、国家、团体、个人——我们多半是两个部落的混血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