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社会服务”第一号令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三联生活周刊)

在香港的“社会服务令”中有更多的公益色彩(Getty Images/Imaginechina)

儿童救助需要一种更为人道的理念(丝路/SIPA 供图)
17岁的黎明(化名)和犯事时刚满18岁的亚丽,先后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某社区的居委会做社区服务。他们在这家居委会的对外身份被统一为志愿人员,他们有自己的办公桌,跟其他工作人员关系平等。惟一不同的是,他们有一位辅导员,当时选定在这家社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辅导员前地雷专家鲍景文,鲍在一次地雷爆破实验中失去了双臂和双眼,之后成为热心帮助转化不良少年的民间志愿者。
他们是河北省石家庄市长安区检察院发布的国内第一号社会服务令的两位实施对象。黎明的犯罪是因为在一家网吧拿了人家放在电脑桌上的一个价值1200元的手机。而亚丽的情况比较特殊,这位高二女生犯有很难治疗的皮肌炎,每月家人要为她付出约3300元的医疗费。她因为内心的压力,一次在美容院从一位顾客皮包里取走了1600元。尽管她出事时刚刚过完18岁生日,也得到了更为宽容的惩治。
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属于初犯,犯罪意图都是一念之差。根据以往的法律,他们可能在长达半年的诉讼期后,得到拘役或者缓刑的处罚,而且这将成为终生伴随他们个人档案的不良记录。
黎明的社会服务开始于5月26日结束于7月26日,他总共为该社区服务了100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检察院和他服务的居委会兑现了对他的所有承诺,没人让他剃成犯人必须的光头,没人因为他正在“服刑”就呵斥或者随意指责他。所有知情人一贯给他以尊严,对他的个人情况实行严格的保密措施,仅限于居委会的5名成员和包括鲍景文在内的两名支援辅导员知道。因此小区居民唠嗑中并没有把他当谈资,也没人发现他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他每天服务之余,都能回家,他父母也十分满意。检察院和居委会在每个阶段都征求家长的意见,由家长配合增强效果。
亚丽则是7月5日开始进行社区服务的,由于她的病情比较严重,皮肤上不时要起红斑,她的服务时间少于100个小时。她完成服务后,将继续回学校参加明年的高考,一切如常。
他们的这一记录也许也将记录到个人档案中,但根据具体实施“社会服务令”的长安区检察院起诉处副科长王晓丽的说法:“即使写到档案中,我认为也不会有什么不利的影响,因为哪怕单从‘社会服务’这样的措辞中,一般用人单位也不会有什么敏感反应。”
“社会服务令”是欧美国家比较通行的惩治轻微犯罪的办法,英国早在1973年的《刑事法庭权力法》就创立了“社会服务”的刑种。这属于“自由刑”的一种,法官判处被告人进行无偿的社区工作,以弥补其罪行给社会和其他个人带来的损失。这有点像我们以前常在美国肥皂剧中看到的情节,一个馋嘴的小男孩在一家杂货店偷了点糖果吃,被店主逮住后罚他去粉刷房子。当然,在法官或其他执法人员那里,事情不会显得那么简单而轻率。
把“社会服务令”带入中国的是该区检察院主管起诉的副检察长裴维奇,他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顾了这次移植历程:“今年4月5日我到澳门参加了‘全国少年刑事研讨会’,第一次听说了香港早在1987年就开始实施的‘社会服务令’,当然,他们是面对社会全体公民的。我们在移植这一新型的惩治手法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用在未成年人身上,使那些犯下轻微罪行的孩子们能够免受起诉之苦,另外,必须强调的是,这是我们工作之外的工作,有公益色彩。”
王晓丽说:“以往我们对犯了罪的未成年人思想转化缺乏一个载体,而社会服务令的出现正好充当了这个载体,当然,处罚不是目的,通过处罚也能够让他们帮助社区做一些服务。”王晓丽对此项法规的前景十分乐观。
对首例“社会服务令”在检察院实施,外界还是有疑问的,因为按照惯例,对犯罪嫌疑人的最终裁决权落实到法院手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法律专家冯锐就说:“我国已经取消了检察院的‘免诉权’,也就是说,检察院不可以做最后决定,如果都从检察院或者公安局做处罚决定,一开始就乱了。所以,必须赶紧立法,法律不可以随意创新,必须有立法上的确认。”不同的意见来自英国儿童救助会中国项目司法项目官员李萍那里,她在接受本刊记者一次非正式的采访中认为:“可以参照的例子是上海的‘少年法庭’,他们也是在1985年的时候,自己先搞起来的,之后高院推广了这一模式,对未成年人的立法国内目前还有很多空白,难免有时候立法相对滞后,而实践显得更为大胆而有实效。”
王晓丽解释道:“尽管国家废除了检察院的‘免诉权’,但我们仍拥有‘未诉权’,它也是‘不诉权’中的一种,包括了绝对不起诉、相对不起诉和可以不起诉。对轻微犯罪或者查不清楚的案件检察院拥有最终决定权。”当然,冯锐的担忧并不是没有理由,她至少有两个理由可以构成反对意见,首先在立法不完备的情况下,实施宽免犯罪的法规可能被某些徇私枉法者利用来开脱罪名,其次可能“社会服务令”向非良性发展,演化成“变相劳改”。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实施机构都受过系统的司法训练,这两极的发展都有可能。
为了说明长安区检察院对这一新规矩的慎重态度,王晓丽向记者说明了实施“社会服务令”的程序,案子由公安部门进入检察院后,具体的办案人员给出自己的意见(她强调,每个人的意见仅仅代表他个人,为此,他必须为这个意见负最终责任)。如果他们认为该少年的实情可以实施“社会服务”,就上报给主管起诉的副检察长,再由他传达给区检察委员会,该委员会作出决定书后宣布,同意不起诉,启动社会服务令。因为检察院对任何一个案件都拥有五个半月的审理期,他们在两个月做出社会服务的决定并实施后,一旦发现对该少年的惩治不足以让他纠正罪责,哪怕在实施过程中,都可以撤消服务令,重新向法院提起诉讼,进入下一个司法程序。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注意到,原本从事教育工作,有丰富的青少年工作经验的英国儿童救助会项目官员李萍表达出了一个更为人道的理念:“我们希望根据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让针对未成年人的诉讼‘分流’,公安局不送交检察机关,检察院不诉,法院给予免刑或者缓刑,最终的理想是不要把他们送进监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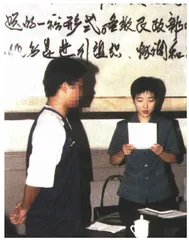
未成年人犯罪多了一种惩治办法(丁文亚 摄) 王晓丽法律法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