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研究院是不是“梦工厂”?
作者:李伟(文 / 李伟 张春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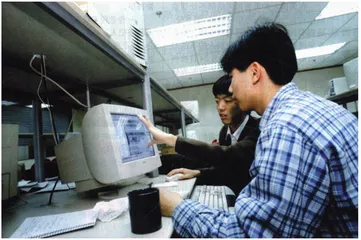
北京微软中国研究院为吸引人才,开辟工作室提供在校大学生免费使用(文津生 摄/BizFoto)
特殊待遇
“现在朗讯贝尔实验室在北京有500多人,在上海有50多人,这一两年应该还是快速增长期,会有大的发展,”朗讯贝尔实验室(中国)公关总监杨伯宁说。但在上月初朗讯刚刚关闭了在硅谷的一个18人的研究中心。虽然没有统计资料,但朗讯贝尔实验室一定是目前跨国公司在中国最大的研发机构,自1997年5月落户中国,已经成为朗讯贝尔在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研发机构,积攒了一大批顶尖的年轻的中国研发人员。看上去比贝尔更野心勃勃的是松下,2月7日,松下电器研究开发有限公司在中关村成立,作为后来者,会长森下洋一明确表示,“5年之内要达到1500人的研发规模”。
至此,跨国公司的“建院”运动已近高潮,据不完全统计已有美国、日本、德国、澳大利亚、俄罗斯、韩国等14个国家的公司、科研机构和大学与中国内地科研机构和高等学校合办研究开发机构:贝尔英特尔、IBM、诺基亚、爱立信、微软、摩托罗拉……该来的都来了。而所组建的中国研究院大都有特殊待遇:一方面是备受重视,地位显赫,中国成为海外建院的首选地,就连日本也难望其项背,微软在海外也只有两家研究院,一家为剑桥,另一家就在北京。另一方面,却是投入的不平等,以英特尔为例,2000年英特尔的研发经费为38亿美元,按惯例10%用于基础研究,也就是说这一年有3.8亿美元被分配于加州、俄勒冈、以色列和北京的四个实验室,而北京5年总共只得到5000万美元,远远低于平均水平。微软也只是计划6年投入8000万美元,这与一个年利润达到90亿美元的巨无霸不相称。
那么,中国研究院究竟在为跨国公司做什么?
侦察——站在市场的前哨
英特尔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颜永红带记者参观了他位于北京嘉里中心7层的实验室,两年前他和另外一名创始人容志诚在一间10平方米左右的小房子开始了工作——颜是语音识别的专家,而容是微处理器的专家。颜向记者演示了两项成果:语音PC控制系统和语音网络服务系统,前者可以用语音指挥电脑操作,比如动动嘴就可以完成一篇文章的输入和编辑;后者可以用语音指挥网络信息的查找,比如你可以直接向电脑打听天气预报或者股票走势。“这是两项很有市场前景的成果”,颜永红说,“但我们并不打算去做产品,我们以后会把它做成Free软件放在网上。”颜的真正目的是开发芯片,而且是做适合中国人用的芯片,“我们站在应用的层面上对芯片的设计提出要求,具体地说现在就是看看怎样的芯片能够处理中文语音。”
颜永红每两周会向总裁写份报告,“我们是英特尔的侦察兵,在科学与市场间寻找各种可能。”颜永红说,“从物理上讲,在网络时代把研究院建在哪里无所谓,但研究院终究是公司的研究机构,要替总裁考虑5年以后的事情,它应该存在于最接近市场的地方,站得越近看得越清”。
本土化——不让盖茨头痛
与颜永红不同,前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李开复则委婉得多——“我们和市场无关,我们做的是基础研究”,他曾在不同场合强调,实际上对这句话的正确理解是:“我们和眼前的市场无关,我们考虑的是5至10年后的市场。”他在建院之初就将研究方向定位于3个新一代,“新一代的多媒体——把计算机视觉、图形学与数字视频相结合,以实现‘互动式多媒体’;新一代的用户界面——让人们能够用更自然、更多元的方式和计算机‘交谈’;新一代信息处理技术——尤其是中文处理技术。”李开复所从事的研究正是盖茨最头痛的困惑——如何让最多的中国人接收西方人发明的电脑。盖茨最终还是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中国人——李开复对盖茨作了回应,他在《科研方向》的最后写道:“我更期望上述创新能够对解决中国人所面临的计算机难题有所帮助,进而造福12亿中国人。”
经过两年的运作,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做得风生水起小有成就,前后搞过两次成果展示,最近的一次是去年12月12日,微软推出了实用性很强的“中文语音识别系统”,他们会把此项技术和新微软拼音植入今年推出的新的中文OFFICE中去。
人才——更长远的准备
李开复面对记者时一再强调科学家的身份而回避对“抢夺市场”的诘难。事实上所有研究院面临的主要非议不是市场争夺而是“人才掠夺”,毕竟市场的冲击要5年、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后才会显现,而人才的“流失”则是刻下的困境。
盖茨曾经数次说:“我敢打赌你们都不知道,在微软中国研究院,我们拥有许多位世界一流的多媒体专家。”李开复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拉起了拥有43名博士的研究队伍,其中60%以上都曾在国外顶尖学校拿过学位,“生活无忧、经费充足、思想自由”是三大法宝。颜永红也承认招兵买马并不困难,他50人的团队平均年龄只有29岁,但问题是:“中国的信息技术人才存在严重断层,精英几乎都集中在25~50岁之间,由此而引起的人才流动肯定会让媒体受不了。”放宽视野看,IT人才在全球仍是稀缺资源。据IDC最近一项联合调查,欧洲IT专业人才的缺口在三年后将达到170万人,在此间,因专业人才缺乏而无法完成的工程项目损失达3800亿欧元;美国今年的IT人才需求量为160多万人,在未来10年内,至少还需要100万名高科技人才,其中IT人才占85%以上;日本今后10年的科技人才缺口为160万人至445万人,其中主要为IT人才。只不过中国的人才问题更尖锐也更敏感。
大公司在人才竞争上也更加白热化,在这种情况下,研究院在选才上作了更长远的打算,“与其说我来找专家不如说来找潜力”,李开复说。李在面试时经常会问一些古怪的问题,“为什么下水道的盖子是圆的?”“请估计北京共有多少加油站?”——“由此我来推测一个人的思维和独立思想的方式”。研究院不仅在寻“潜力”,也在寻找更小的苗。每年假期微软研究院总是挤满了来实习的学生,英特尔公司将目标放得更低,赞助中学生赴美角逐“英特尔科学天才奖”。美国摩托罗拉也启动了“希望之星奖学金”,将人才救助转向人才培养。
三年后的梦想?
侦察市场、本土应用、积累人才是今天研究院的主要工作,它们大多是沉默的,尽管母公司每天都要爆出几条猛料新闻。采访过程中,颜永红反复向记者说明:“研究院的真正作用三年后才能看清楚,那时可能会有更多强力产品,可能研究院的规模还要翻倍。”
而北京社科院经济所副所长赵弘认为这一时期可能还会更长,现在跨国公司正处于小心翼翼地试验阶段,“也许十年后反过来看研究院的建立,会发现它巨大的能量,这是中国经济也是全球经济发展的一个节点,国际资本的目光从生产线、廉价劳动力转移到高增值的科技研发,中国将从制造中心转化为研发中心。”在经济一体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不断优化其价值链,不可避免地把研发中心转移到最具活力的市场,从而控制产业上游,取得竞争优势。
“对大公司来说,从投资人力到投资人脑,从投资下游到投资上游,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想象空间,还意味着巨大的风险。”赵弘说,“大的馅饼有可能变成大的陷阱。”最尖锐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的科技品位低,据统计,在我国经济增长中只有20%靠科技进步推动,而美国则超过了90%,这意味着中国市场的拉力滞后于跨国公司的科技推力,市场难以承担高昂的研发费用。更严重的是市场与消费可能会拖垮科技发展,实验室里的新玩意无法商业化。这也是盖茨、贝瑞特们的顾虑,科研一不小心就可能成科普。中国从一个不完全的工业国转向信息国家时,单靠科技的生拉硬拽是不行的。
研究院是跨国公司的“梦工厂”,资本家与科学家依靠它实现了理想与梦想:贝尔实验室1925年成立后使AT&T及朗讯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电信公司,70年代初100多名科学家来到了施乐帕洛阿托研究中心,这些一流电脑专家躺在铺着麻袋的地板上,四周放满了黑板,幻想着电脑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个人电脑尚未出生的时候,他们“孵化”了风靡今日的一系列概念——鼠标、菜单、图表和视窗等等,在他们身后诞生了微软、3COM、Adobe和苹果。(图片均为本刊资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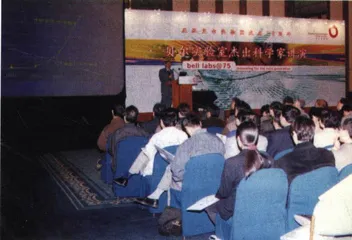
2000年是朗讯贝尔实验室成立75周年。在中国,贝尔实验室以又一次举办“贝尔实验室杰出科学家讲演”作为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