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德伯格正传
作者:钟和晏(文 / 钟和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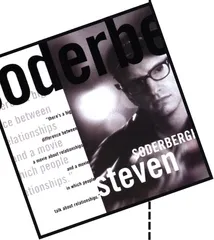
史蒂文·索德伯格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他的电影作品的书,在书名中称自己是“the Luckiest Bastard You Ever Saw”(你所见过的最幸运的家伙)。1989年,索德伯格的第一部作品《性、谎言和录像带》获得金棕榈奖,那年他26岁,也是戛纳历史上赢得这项令人垂涎大奖的最年轻导演。这部电影的片名后来成了各种报纸头条新闻爱引用的标题,尤其在漫长的克林顿-莱温斯基情节剧期间备受青睐。
可能《性、谎言和录像带》当时赢得的声誉和商业上的极大成功与本身实力相比多少名不符实,但是在好莱坞巨片一统天下的整个80年代,这部朴素节制、成本仅为120万美元的独立制作影片构成了对好莱坞的虚华浮夸最有力的反叛姿态。对观众来说,《性》提醒他们也有不是好莱坞制造的好电影;对好莱坞来说,他们突然意识到这样的小成本电影也能赚大钱。索德伯格因此成了艺术电影通向商业市场可能性的最佳象征,也为后来类似《低俗小说》到《美国美人》这样具独立意识的电影进入主流院线开设了道路。
索德伯格本人的艺术道路并没有从此一帆风顺,电影之神再次向他微笑已经是11年以后。90年代索德伯格一共拍摄了7部电影,从《卡夫卡》的深思到《丘陵之王》的温柔;从《在底层》的幽暗到《战略高手》的低调,这些影片题材风格上的变化多端让人吃惊,当然没有一部影片的影响力能超过《性》。索德伯格本人的解释是:“那时我还年轻,还想试图找出我的强项和弱点。”
同时代的昆丁·塔伦蒂诺等人引来大批模仿者并不由自主地滑向自我模仿的陷阱时,索德伯格拒绝自我重复的坚持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在不断探索中他的个人风格日渐明显。其实从《性》开始,索德伯格已经呈现出冷静自信、不带矫饰的电影品质,这些年来他尤其发展了建立在本能直觉基础上的叙述能力和影像风格。他将技术的精确和对表演的尊重揉合在一起,不仅相信自己的直觉,也深信演员的表演能力和观众的智力。从对电影语言的审慎运用来看,他更像是现代主义者而非后现代。他从不追求震惊的效果,而是更满足于微微地出人意料。
虽然从索德伯格的影片中可以明显看出奥逊·威尔或者戈达尔的影响,而且他也不止一次表示出对阿伦·雷乃影片的偏好,虽然他在90年代的大部分影片都是几十万美元的小制作,常靠给人写剧本的钱来维持,事实上他已经渐渐失去对作者电影的兴趣。在他出版的那本电影编年史中,1996年到1997年间的日记尤其充满了挫败感和自我怀疑。后来他说:“我开始意识到我越来越使自己边缘化,如果我想要在这个行业中有个自己的位置,我必须打破自我界限。”1998年的《战略高手》就是这样一个转折点,这部影片同时捧红了乔治·克鲁尼和詹妮弗·洛佩兹。到了2000年,《阿莲正传》是那年第一部票房超过1亿的影片,全世界的票房总数达到2.5亿美元。他的最近一部作品是根据英国BBC电视连续剧改编的《贩毒网》,气势恢宏地描述了美国令人绝望的反毒品战,一上映就赢得了大量赞誉,甚至引发了有关的政治辩论。这两部影片使他同时获得今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的提名。
如今,自然有好事者开始质疑索德伯格的电影究竟是受欢迎的艺术电影还是装作艺术气派的主流电影,索德伯格本人究竟是渗透进好莱坞的电影作者还是披着独立外衣的主流导演?这样的问题显然找不出什么标准答案。索德伯格说:“美国缺少的不是艺术电影作者,而是由聪明的电影人拍摄、能在4000家影院上映的电影。我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把钱给那些聪明有趣的人,为什么他们只能做些不到100万的玩艺呢?”
说到奥斯卡颁奖晚会,他说:“他们请我,我就去呗,否则我宁可去打棒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