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圆桌(129)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巫狐 陆离 朱伟一 愚妹 快雪亭 kivo 顾汶)
阴险的摄像机
文 巫狐 漫画 谢峰
不久以前,我看到一个漂亮女艺术家做的纪录片,内容是娱乐场所女洗手间里的风起云落,小姐们在那里垫胸、涂脸、净身和数钱。这部用针孔摄像机拍的东西万分动人,在展览上吸引了很多人,大家看着一群非法佳丽在厕所里给男人打撒娇或者生气的电话,一边肆无忌惮地换内衣,无比兴奋。
电视里有些设套的节目也开始这么干,记者们诱使人给他们买个身份证什么的,买的人秀得真诚,卖的人狡猾得像个地道的狐狸,但狐狸多半还是上当了。他们约了个地方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买方的眼神像克格勃,冷静得像没带摄像机。
终于,电视节目越来越像真正的犯罪现场直播了,电视被绑在一根名叫地下生活的柱子上表演高收视率的游戏,观众挺着脖子流着哈喇子跟着上下起伏。有时候,比A片还过瘾呀,因为那些演员都不知情,不知情这三个字好值钱。
从前有相机的时候,相机是把手枪,现在有摄像机的时候,摄像机是挺机关枪,它连续扫射,一个也没法放过,它弄点小阴谋真是方便极了,“你爱张国荣吗?”话筒伸过去问某新秀:“喜欢到要发疯,我想把他放在我床上。”其实这是剪辑的小伎俩,人家在说的是个绒毛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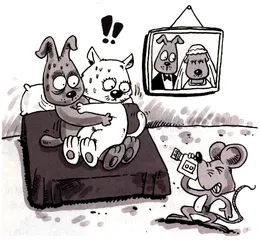
摄像机把很多人不小心弄成了受虐狂或者自虐狂,当正常生活已经不刺激,就来点咖啡加点咖哩,在娱乐节目里拷问一下那些名人淑女,问他们的初夜问他们对目前的性伴侣满意与否,如果他们唧唧呜呜就把镜头伸得更近些,再近些,细看他们额头的汗满脸的尴尬笑容,要多搞笑有多搞笑,没得噱头怎得看头。
飞来飞去的女人
陆离
小R是我认识的一个女人。我认识她时她还是个学生,但是我能从她口中听到一般学生说不出的颇有见识的话题,她提起英国、法国、瑞士、丹麦、德国、荷兰、比利时如数家珍,一边说一边用手大幅度地划过空气,好象在挥舞着一面欧共体的旗帜。那时她常常混迹于留学生中间,我在语言学院看见她的次数胜过在她就读的学校,她热心地教留学生们汉语,把粉色的舌头吐出来,咻咻地呼着气,告诉留学生们(均为男性)汉语发音和舌头的密切关系。可以想见她的舌头是怎么跟男留学生们的舌头搅在一处的。她不仅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渊博的汉语知识,鉴于她的专业是世界性语言——英语,她也虚心求教,吸收兼具各国特色的英语发音,力图使自己的发音不那么中国味。她还深入浅出了学习了不少粗俗的俚语,用娇嗔的口吻说出来,以达到和男留学生们打成一片的目的。
小R大学毕业后的行踪一度是个迷。后来据一些时常流窜于北京各个饭店酒吧西餐厅音乐厅画廓古玩市场的人说,有时会在云鬓香车的群体中惊鸿一瞥小R的倩影。小R今非昔比,不再秉承留学生们休闲嬉皮的服装风格而是向雍容贵妇型迈进了:她的头发高高地挽成一个髻,露出凝脂一般的脖子和钻石项圈,貂皮大衣遮过麂皮靴子,据推测里面是一条范思哲弹力超短裙和一条CK内裤。曾有她的大学同学自以为和她很熟上去打声招呼,但一律被毫不留情地羞臊回来,因为小R声称非常讨厌男人(中国男人)轻浮,见姑娘就上去搭话,而她对于其他的女人,一向都是轻蔑的。
两年前北京的外国人好像退潮一样呼啦走了一批,据说她也被大西洋的海水带走了。
小R毕竟与众不同,让人牵肠挂肚。对于她的去向众说纷纭。像她这样不凡的女人自然不会出去吃苦,留学打工上班养家。关于她的故事可以讲上一千零一夜:有人说她接受了某年逾花甲的阿拉伯王子的价值连城的大钻戒,去天方夜谭的国家充当后宫佳丽去了;有人说她粘上了美国的某个“大王”——“石油大王”或者“钢铁大王”或者“传媒大王”,有望成为富可敌国的女继承人并夸海口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捐献几千万美金;有人说某个非洲部落的一手遮天的酋长摄取了她的芳心,平日她英姿飒爽地驰骋在非洲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周末则到欧洲参加王室举行的派对;有人说南亚的某个贪污国家巨款的政治家对她一见倾心,在法庭上又臭又硬像茅坑里的石头的政治家在枕边柔情蜜意,把瑞士银行的账号和密码一并向她娓娓道来有人说……总之,小R是一个我们生活之外的女人。她从一个人身边飞到另一个人身边,她的故事遍及世界各地。
小R的事情之所以要由我来写是因为上天赋予了我这个使命,让我在天涯海角遇到她。其时小R在委内瑞拉某中国城某超市当收银员,她干起活来心不在焉魂不守舍多算了我钱,待我正要和她理论时,她惊恐的眼光中闪烁出熟悉的倔强的内容,我没说什么她先辩解起来。小R说,我来这儿散心的,闷得无聊才来体验生活。明天的机票,头等舱,去英国。心早就飞过去了。谁稀罕这个工作?!姿态比卡特琳娜女皇更不可一世。说完,她不顾我呆若木鸡跨过一摊污水甩手而去。三十多岁的小R的身影依然迷人,穿着隆重的套装,好像在高尚写字楼上班的温文淑女。天知道,明天她要飞到哪里去呢?
(本栏编辑:苗炜)
“劳工神圣”?
文 朱伟一 漫画 谢峰
小时候想当工人啊!还记得于洋同志吧?就是电影《火红的年代》里的那位炼钢工人赵四海,抓革命,促生产,真正的国家主人。还有很浪漫的一面,“我站在金色的炉台上,这里是毛主席到过的地方。亲切的教导……”——一首小提琴曲《我站在金色的炉台上》让人“浮想联翩,夜不能寐”。
中学毕业后终于当上了工人,可感觉并不那么好。不像赵四海,脖子上围条雪白的围巾,风风火火闯九洲。数九寒天,风雪交加,我们在露天中洗轴承,双手浸泡在汽油中,先洗轴承,再上油。一墙之隔的南京大学却是另一番天地,红砖绿瓦,“南风轻轻吹又起,吹动了绿草地”。我这才真正体会到高玉宝同志在《我要读书》中的心声。
我混进了大学。因为是学生,暂时不是工会会员。不过,大学毕业重新工作后,又成了当然的工会会员。但这些工会也就是发发电影票和补助金什么的,更像是联谊会,不像大型革命现代歌舞剧《东方红》中的场面,波澜壮阔,激动人心。
我到了美国寻找革命战斗的机会。这里曾经有过遍地的产业工人,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最理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土壤,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好去处。美国的一位早期社会主义领导人维克多·伯尔格说过:“每一位社会主义同志都应该备有一枝精良的步枪,另加50发子弹。”这是要搞红色暴动。
1960年代,《劳工法》在美国曾经火过。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一任院长就曾经是哈佛大学的劳工法专家,现在改行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任校长也曾经是劳工法专家,现在也改行了。国内来的同学大多亲近《公司法》,远离《劳工法》。
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公司法》是个热门。教《公司法》的有好几位教授,济济一堂,是个朝气蓬勃的战斗集体。但教《劳工法》的只有一位教授,犹太人,留一把大胡子,年轻时思想很可能左倾过。劳工法教授是真正的形单影孤。
劳工法教授也有风光的时候,那就是在海外讲学。暑期他去阿姆斯特丹举办《劳工法》讲座,授课处是河上的游船。河上泛舟,浅斟低唱,趣谈国际工运大事,好不风雅!这与我心目中的劳工律师相去甚远。
《劳工法》我学到了什么?我知道美国工会的活动天地越来越小。在美国,专业人士不得参加工会。这样一来,知识分子就不能与劳动者相结合。
工会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商定劳动合同和工资待遇,其他许多问题则是通过别的法律下的诉讼来解决。1967年美国通过了《男女同酬法》,后来又推出来一个《就业年龄歧视法》,禁止因为年龄原因而雇用、解雇或提供补偿。美国同志经常是告性骚扰,告性别歧视,所以领导通常不敢随便解雇人,都盼着经济萧条,企业普遍裁人,他们好趁火打劫,你也搞不清他们裁人到底是经济需要还是公报私仇。
看电影也能学习美国工运史。故事片《豪法》的片名就是主人公杰米·豪法(Jimmy Hoffa)的名字。该片由奥斯卡影帝尼克逊主演。豪法是美国工运史上的一位传奇人物,曾经领导过美国最强大的卡车司机工会。
豪法得罪了权贵,尤其是肯尼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用了7年时间,终于把豪法投进大狱。1964年,陪审团定豪法有罪,说他盗用了工会的退休基金,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
豪法曾经支持过尼克松。美国不搞一元化,工会有许许多多的山门,其中大部分支持民主党。所以尼克松十分珍惜豪法的这份友情,一上台就特赦豪法。豪法出狱后还想夺回卡车工会主席的位置,因此得罪了不少人。1975年7月30日,豪法失踪,据称是被好莱坞黑帮杀手所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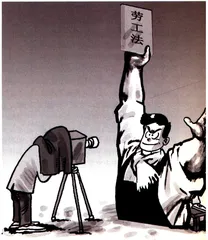
邂逅老狼的那一天
文 愚妹 漫画 谢峰
那一天,在一个卖虎头鞋和红棉袄的小集贸市场百无聊赖地闲逛,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在歌唱,有一点沙哑,但充满磁性。在一个这样的声音面前,我一点防御能力也没有,一下子变得不知所措。
是老狼的声音,不知道是哪一个摊主开着收音机,让我觉得温暖。
那天,也和她见了一面。于是和她又聊起老狼。她已经不喜欢老狼了,并喜形于色地说着苏永康。我说我还是那么死性不改地喜欢老狼高晓松朴树这三大丑男。
想着想着我就笑了。真是这样子的,还有像窦唯张楚何勇他们,她也是肯定不会喜欢了,但我又是多么地爱啊!一句“避开大家无聊之中勉勉强强的热闹,开发自己能够得到孤独中的欢笑……只想能够努力做到我认为的好。”让我得到在孤独的日子中怎样的共鸣!即使窦唯别的什么也不写,就凭着这一句,就足够让我喜欢他下去——瞧!这个多么可爱的男人,年近三十还在成长,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惟一和她共同喜欢的人是郑钧,但她之所以爱和我之所以爱似乎不一样。她说:“很多人喜欢郑钧,他好帅!”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从不觉得有很多人喜欢郑钧是好事情。
在麦当劳一个小时的冷气之后,我们礼貌地分手。这时候,我看到她的背影,我们穿的衣服是多么的不一样!她穿的是我永远也不可能穿的粉红粉蓝粉绿,而我穿的一身黑和球鞋。
我走在路上。我想,我谁都可以拒绝,可谁又能够拒绝时间呢?
以上便是我在邂逅老狼的那一天所做的,所想的。在我就要结束这篇文章时我惊觉,这就是我喜欢老狼的原因——让我暂时性失忆,并假装可以拒绝时间。
时光之书
快雪亭
想当年(老人们喜欢用的字眼),我上高中时,有次作文课的题目是写一封信,可以写给任何人。答卷五花八门,真有寄给火星人的信。而我的信独具一格:写给30岁的自己。
这篇作文收在家里一个旧书架底层,前天我整理杂物时,又把它找到了。
我毛骨悚然地站了一会儿,才翻开作文纸页。这种感觉不可思说我收到了寄自13年前的自己的信。它从一间宁静的平房式小教室里寄出,由一个热情男孩的憧憬的双手投给了时间;恍惚间就飞送到钢筋混凝土大厦里这个平凡忧郁的我的手上。
“你好!收到这封信时,你已经30岁了……”
啊,是的,我收到了它,我30岁了!
“你一定成功而又快乐,不像我,有这么多的苦恼。”
我成功吗?不知道;我快乐吗?
“昨天,因为作业的事,还被我爸(也就是你爸)臭骂了一顿。这家伙很危险,动不动就骂人,有时还动手,你也要小心。人为什么要有个坏脾气的爸呀!你说?”
爸爸……爸爸已经病逝十年了!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向他表达我的爱?我为什么没有回报他深沉的爱与关怀?这种遗憾又如何才能弥补?
“前两天,B又为一点小事和我闹得很不愉快,到今天还不理我。人是怎么回事呀?”
不用担心,再等两天,郊游时她会借机跟你和好的。唉,可毕业后你们就要天各一方,十年不通音讯。人就是这么回事,小伙子。
“不说烦心的事了。我对你的世界很感兴趣,它是什么样子的?可惜你不能回信告诉我。也许以后的科技有了发展,你可以给我回信?那就快回吧,我想看看明天,想得要死。有时候,我不知道自己以后该怎么样,我懂得太少。甚至害怕将来。你一定比我聪明得多,如果你能教我就好了……”
教你?是呀。你走了多少不必走的弯路,但你又多么幸运……和今天的世界比起来,你想象中的世界更加美好。
“因为咱们俩是一个人,所以我请你别改变我的一切。有几点要记住:一是对朋友要好;二是不该说谎的事就不说慌;三是要勇敢……”
你的话我记住了,我会尽力而为。
“虽然这样教你,可我感觉你是我的哥哥似的。这很奇怪,你比我大,而我们又是同一个人……”
读着读着,我热泪盈眶。这是个晴暖的冬日下午,旧书架散发着古老的漆、木香气,阳光使屋内空气中的灰尘也变得耀眼辉煌。我却闭起眼睛,看见了13年前的那间小教室。在那个浓绿的夏天上午,我坐在靠窗的桌前咬着笔杆,搜索枯肠。外面一片葱郁像渲染开来的水彩;窗角有一幅小小的洁净的蜘蛛网挂着水珠——一切都如同雨后的早晨一样清新。
我不敢相信自己曾经这样年轻。
我看《东京日和》
文 kivo
在一个类似于水彩画的阳台全景镜头中,影片缓缓地开始,不疾不慢,预示着整部片子的节奏与未来。中山美穗所饰演的女主角阳子在白色的床单前摆出各式样子,在爱人岛津(竹中直人饰演)的镜头下,自然的甜蜜悄然滑落。
影片如流水一样,绕过千山万壑后,依旧不改从容的本性。导演竹中直人似乎沉溺于他那略显冗缓的节奏中,而身为局外人的我,则是看着平静的画面,内心却莫名的烦躁,就如阳子一样,突然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狂。阳子是因为内分泌失调,而我,则是不耐于生命的平凡。
一连串的琐碎镜头,是导演刻意安排的吧!岛津对阳子时好时坏:有时两人可以高兴地聊天,有时却会气得砸掉饭碗。时间的推移中,磨损的是什么?是我的耐心,还是他们的爱情?
直到那个镜头的出现,整个人徒地清爽。
那是快要下雨的时间中,一起跑步的夫妻俩在路边突然发现一块很像钢琴的大石头,然后,两个人就像孩子一样地奔跑下去,然后欢乐地弹奏着《土耳其进行曲》,和着雨滴滴落的声音,还有他们的欢笑,一瞬间仿佛万籁澄清。
猛地明白,原来岛津对阳子的爱意,是藏在生命的每一刻钟上,随着时间的推移,爱情并没有消亡,反而历久弥新。
以后的镜头中,时不时地会出现向日葵的镜头,摇曳着两朵金黄的笑脸,迎着湛蓝湛蓝的天,用完美的色调展示了一种明朗。记得D.H.劳伦斯在他给露依·勃罗斯的情书中形容那个女子“像向日葵那么坦率”,起先我不懂,现在却懂了。阳子与岛津的爱,何尝不像这两朵向日葵,坦率地活在世间。而岛津为阳子拍下的照片里,哪一张不倾注了他对阳子深深的眷恋!
影片最后有这么一场戏:理完发的岛津突然发现阳子失踪了。他慌乱地穿过树林,四处寻找,终于,他发现在一条船上睡熟的阳子。
照我一贯看的电影,此时的男主角应该大声叫喊女主角的名字,以求达到煽情的气氛,可在这里,一切归于宁静。岛津看着阳子,脸上满是安慰,激动只留在眼睛里。
这是一种内敛的感情,日本的作品好像大多这样,恋爱双方都不将感情挂在嘴边,因而使得电影中弥散的是安详的气氛,不刻意煽情,甚至,避免煽情。取悦观众的,则是一种安静与平和的人生。
音乐是一部影片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整部电影中,背景音乐大多是钢琴和小提琴演奏的。钢琴是一切乐器中最温柔的音乐,而小提琴,则是温情与萧瑟的组合体,有了这两种乐器的铺陈,剧情才越发完整。
在影片结束后,我想到徐志摩的一句诗:“希望在每一秒钟上允许开花。”
别了,MBA!
文 顾汶
“方总走了”,早晨一进办公室Kevin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每个人,失踪三天的方先生终于有了下落。
“还MBA呢,一点风度都没有,走了连个招呼也不打”,公关部于芳一副不屑的神情。
听说MBA的优秀不仅表现在超凡的管理才能上,更表现在行为规范和生活态度上,也许方总是个例外。
回想起方先生刚从加拿大回来时很是振奋人心,刚下飞机就直奔公司,与其他一些海外空降兵一样,一着陆便点火烧钱,一出手两个月250万出去了,眼见火势不对,又急忙扛起大旗走人了。
说是说做是做,这不,周一上午的例会大家又要“指点江山”了。“指点江山”是公司里各位总监之间的戏言,因为各部门的工作方向均由自己掌握,主持工作的COO是刚从美国回来的MBA,实际经验少得可怜,根本无法把握各部门业务的走向,任由各部门主管“指点江山”,指到哪里打到哪里,自由自在好不痛快!
不过,约束还是有的,要求每周甚至每天将各自的工作写在公告板上,以便掌握每个人的工作动向,跟着COO工作好像陪幼儿园阿姨做游戏,当然是做管理游戏,轻松、愉快也很有意义但不实用。也许一来就把这位美国MBA放在COO位置上反而害了他,而且害的不仅是他一个,近来遇见几家网站带“C”字头的MBA,大都是从校办工厂里生产出来的“课堂总经理”,他们的名片上公司地址不断变化,公司名称也不断变换,也许他们还有一段变化的路要走。
下午,又要开始新一轮的面试,需要招一位部门经理。人力资源部送来7份简历,有5个MBA,其中3个是在读,今年才考上的MBA,简历上却早早地明显地传达了“我是MBA”这个信息。难怪国外的老同学一再催我:必需去读MBA,如果能去国外拿个MBA,再回来做事,那更是前程似锦。MBA可谓职场中的VIP,因此下午的面试我一点也不敢怠慢(读MBA都是付出了很高代价的)。
方总的工作由我来代管,由于没有交接手续,晚上一个人静静地清理他的办公桌,精美的笔记本,考究的文件夹,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方先生的名片,“方××”后面紧跟着是大大的“MBA”,“市场总监”四个字很小地压在下面,这醒目的“MBA”令我想起了《围城》中的方鸿渐博士。
唉,轻轻地把方先生的名片盒放进纸篓。
别了,MBA! 老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