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大战略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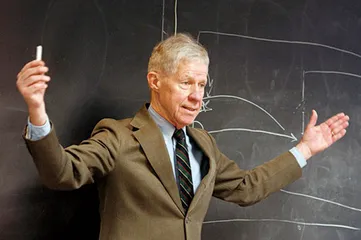 ( 希尔和他的《大战略:文学、治国之术和世界秩序》 )
( 希尔和他的《大战略:文学、治国之术和世界秩序》 )
查尔斯·希尔也是耶鲁大学这门课程的老师。日前他出版了《大战略:文学、治国之术和世界秩序》一书。他在书中提出,应该重新把文学用做传授治国之术的工具。“文学探索无限的、微妙的细节,描绘虚构人物的思想,以复杂的情节把宏大主题戏剧化,它最接近世界运作的真相。没有文学的洞见,就无法练习治国之术。文学处于宏大战略所需要的领域,处于理性的算计之外、想象活动之中。”为此,他考察了从荷马到拉什迪等70位诗人、剧作家、小说家、散文家的著作。这本书某种程度上也是一部回忆录,在成为教授和学者之前,希尔是一位外交官,做过基辛格和乔治·舒尔茨的助理,以及前联合国秘书长加利的顾问。
美国评论家亚当·柯什对希尔这部著作的出发点提出了质疑,他说:“文学是政治领导才能十分可疑的基础,如英国散文家威廉·哈兹里特所说,诗歌的语言天生与权力的语言一致。直到近来诗人才被想当然地视作和平主义者。阅读《伊利亚特》或《亨利五世》等于观看帝国主义和征服者的辉煌,这些书让我们敬佩我们的理性所谴责的东西。”
希尔也承认:“本书中思考的著作回答了治国之术中的难题,这些解答既可以被掌权者用于行善,也可能会被用来为恶。”但该书的原创性不在于希尔提出重要的文学作品回答了重要的政治问题,而是提出这些作品真的已经因为影响了国王、王子、将军和政治家,从而影响了世界。文学和治国之术的关系是交织在一起的、交互的,因为文学告诉领袖们谁的行为将成为文学的材料,就像《伊利亚特》让伯里克利知道,谁的行为会被修昔底德记录下来,修昔底德的著作又影响了后世的政治家。
希尔在序言中说:“亚历山大大帝东征时随身带着《伊利亚特》,把它跟一把匕首一起放在枕头下,认为它是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宝藏,包含着所有的军队品德和知识。托马斯·莫尔在被封为圣人之前,阅读罗马的诗歌和戏剧。伊丽莎白一世从西塞罗的作品里学习修辞和司法战略。弗里德里希大帝把荷马的《奥德赛》当做王子们的典范。约翰·亚当斯读希腊文的修昔底德著作,从斯威夫特、莎士比亚和塞万提斯那里学习如何走出人性的迷宫。林肯精读惠特曼的《草叶集》并被它改变,阿拉伯的劳伦斯带着托马斯·马洛里的《亚瑟王之死》,不是把它装在骆驼身上的褡裢里,就是装在他头脑里。”
全书围绕三个有重大影响的历史时期:古希腊和罗马的古典时期,国家从家族和部落习俗中脱胎出来,开始形成第一个国际体系;新教改革时期,在16和17世纪的欧洲,现代独立国家的体系开始成为化解宗教战争的途径;现代时期,始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平等、自由的理想被用于抨击民族国家和国际体系。希尔强调,《伊利亚特》描述的原始的国际格局逐渐让位于修昔底德在《波罗奔尼撒战争》中描述的更加复杂的力量均衡,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平衡倾覆之后,这一体系遭到了破坏。之后,宗教战争又为国际体系创造了一场危机。新教和天主教如何和谐相处?作者描述了马基雅维里、莎士比亚、霍布斯、弥尔顿和斯威夫特等人对混乱和以共同同意为基础的统治合法性的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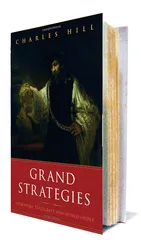
现代文学开始以意识形态和革命为武器挑战现代制度。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表达了这种挑战:“法国大革命威胁着世界秩序,英国的常识维护着文明的体系。在伦敦,私人生活可以存在,在巴黎一切都要在公众面前展开。”在《格列佛游记》中,在现代化国家的前景还不明朗的情况下,斯威夫特思考了政府的各种形式。“在更深的层面上,该书讨论的是秩序的脆弱和政治家们为了平衡、约束国家力量,使国家力量合法化所做的努力。”■ 读书文学希尔修昔底德文化战略伊利亚特